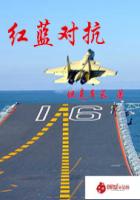第二日,用过早饭,平儿在跟齐夫子读书,贺君欢则在自己屋里筹划着下一步该如何做,却听见外面闹哄哄的。
没过一会,妗春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小,小姐,那个,那个凌王妃来了。”妗春气喘吁吁地说着。
“果然是个蠢的,她居然真的来了。”贺君欢冷笑一声,搁下了手中的笔,见妗春还在这傻愣着,笑着说道,“傻丫头,凌王妃大驾,还不快去接待?”
妗春眼珠转了转,也笑了,欢快地应道:“是。”
贺君欢知道这个鬼丫头肯定又要耍什么坏心思,也没拦着,反正她手下有分寸,不会出什么事。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对着镜子梳了个得宜的头发,也没上什么妆,化了下眉,戴了两三样素净的头饰,收拾好了才出了屋。
刚到外院,就见外厅里一个穿着富丽堂皇地年轻女子坐在主坐上,旁边是妗春给上的茶,她拿起来喝了一口,立时又全吐了回去。
“这什么茶?如此涩口,便是咱们府上下人怕是也不曾喝这么差的茶叶。”左茗薇用丝帕擦着嘴,带着嘲讽说道,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妗春正低着头偷笑。
刚走进来,正巧看见妗春在偷笑,应该是这丫头动了什么手脚,想到这,贺君欢无奈地笑了笑。
“民女见过凌王妃。”贺君欢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然后起身坐在了旁边。
“放肆!”凌王妃突然拿起桌上的杯子,摔到贺君欢脚边,“本妃让你坐了吗?”
茶水濡湿了贺君欢浅粉色的衣摆上,晕开了好大一摊茶渍。
贺君欢成心给她下马威,起来欠了欠身,说道:“王妃恕罪,民女这两日身体不好,听闻王妃是个贤淑的,想来不会同民女计较,如今看来,倒是民女误会了。”
“若是王妃觉得生气,民女这就给王妃赔个不是。”贺君欢说着,又是欠了欠身。
“你!”左茗薇用手指着贺君欢,眸子里满是愤怒。成亲这么多年来,因那事王爷同她一直相敬如宾,何时会那般不顾及她情面,硬要把一个野种带进府里,还要寄养在她名下。
左茗薇越想越气,还是旁边的婢女扯了扯她的袖子,让她想起了她来的目的,这才冷静下来,说道,“本妃不同你计较这些。”
“听王爷说,你弟弟是王爷在邳州时,与你姨母生的孩子,王爷想要把他带回凌王府抚养,还要过继在我名下?”左茗薇的语气里全是不屑和鄙夷。
“正是。”贺君欢回答道。
左茗薇一听到这话,先是冷哼一声,随即说道:“你好大的胆子,竟妄图混淆皇室血脉。来人,把她给本妃绑到大理寺去。”
当下,左茗薇带来的人便要上前来把贺君欢拿下。
妗春连忙挡在贺君欢跟前。
“慢着!”贺君欢不紧不慢地开口,对左茗薇说道,“王妃有何证据,说平儿不是王爷血脉?”
“本妃自然有,王爷他根本就不可能……”
“王妃,”贺君欢突然叫住她,一双杏眼盯着她,说话轻飘飘的带着蛊惑的意味,“慎言啊。”
左茗薇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差点说漏了嘴,竟然恼羞成怒,举起右手就要打贺君欢。
“你这个贱人。”
贺君欢拽着妗春往旁边一挪,左茗薇便扑了个空,险些趴到桌上。
“你在做什么?”一声震怒从门口传来,只见顾旌舟穿着朝服走了进来,一看便知是刚下朝,得了信儿就赶过来的。
“王爷。”左茗薇明显有些慌乱,呆愣地站在原地不敢动。
“来人,把王妃带回去。”顾旌舟脸色阴沉得吓人。
顾旌舟说完,身后的两个丫鬟便过去了,捉住左茗薇就要往外走。
“王爷,茗薇嫁给您多年,事事为王爷着想,如今这女人分明就是在诓骗王爷,王爷莫要上了她的当啊,王爷。”左茗薇哭的梨花带雨的,倒是真的说到了顾旌舟的心坎里。
贺君欢要做什么,他一直都不清楚。为了皇位?可是就算他认了平儿为长子,只要他不想,平儿永远也不可能登位,像贺君欢这样聪明的人,不可能没想到。可除了这个,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殿下息怒,王妃多年无子,这突然间多了个儿子,任谁也会难以接受的。”贺君欢走到顾旌舟身边,轻声说道,“平儿这些年跟着我生活得也很好,不如,就算了吧。”
顾旌舟低头看她,却见她那双眼睛正含笑看着他,却是在嘲笑。
顾旌舟感觉自己像是赤裸裸的被人盯着,心里既羞耻又恼怒,他甚至想要直接杀了贺君欢,但一想到贺君欢那日在玉清观说过的话,他还是强压下心中的杀意。
顾旌舟声音低沉地说道:“本王说了,平儿是本王的孩子,若王妃不愿意抚养,本王也不介意,给他换一个嫡母。”
这下,左茗薇彻底安静了,顺从地被人带了出去。
“半月后,本王会派人来接平儿。如此,你可还满意?”顾旌舟一双眼睛斜睨着贺君欢。
“民女自然是满意。”贺君欢说着,颔了颔首。
“那你最好,也不要叫本王失望。”顾旌舟话里有话地说,甩袖离开。
“恭送凌王。”
终于送走了那两尊大神,贺君欢松了口气,准备去找平儿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情。
“平儿?”贺君欢敲了敲门。
“姐姐怎么来了?”平儿立马当下书,跑去开门。
“姐姐是想来问你,那件事你想好了吗?若现在反悔,还是来得及。”贺君欢坐定后,开门见山地问平儿。
平儿想了一下,却没有回答,只是反问道:“那姐姐当初,为什么会想让平儿去坐那个位置?”
贺君欢想了一下,开口说道:“当初我只想活着,后来,几次三番的追杀,叫我心生怨恨,但那时我也没想让你去坐那个位置,只想着你变的强大一些,更好地活下去。直到,你五岁那年。”
那年,贺拂带他们两个去央州,途径梧州。梧州那年发了大水,死亡的百姓都快能将梧岭河填满了,但朝廷的救济粮,却迟迟没有来。后来,贺君欢从贺拂口中得知,当时大景正在和西南瓦剌打仗,且梧州是个小地方,皇上便只拨了七千石粮食,这层层克扣,到了梧州竟只剩了四千石,足足少了一半。
“君王无才德,百姓受苦。”贺君欢看着平儿,眼中含泪。
平儿拿起丝帕递给贺君欢,贺君欢摇了摇头,没有接。
“黎民苦,焉你我可逃?姐姐教平儿识字,知理明识,可不是为了让平儿做个书生的。”平儿的声音虽稚嫩,却透着坚毅,“平儿是傅家血脉。傅家,忠的是天下,爱的是百姓。如今国势渐微,百姓受苦,平儿又岂能独善其身。”
“平儿只是心疼姐姐。”平儿看着贺君欢说道,“姐姐原本应该像寻常女子一样,对镜拈花,与心爱之人琴瑟和鸣的。如今,却只能为了平儿,躲在这暗处,步步为营。”
“平儿。”贺君欢轻轻唤了一声,将他搂在怀里。若不是大景这代已呈危势,她也不愿让平儿去那个位置。只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哪怕居于陋室,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也一定要比现在要幸福自在得多。
“平儿,你要记得,不管以后什么样子,你永远都是姐姐一辈子的骄傲。”
“嗯,平儿省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