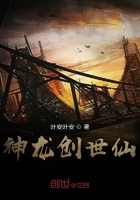“梁鹤鸣吾且一,于大朝无劈石以练剑!!”。”从屋里传来之言秦峦嘶吼。
虽百般不,而无可奈何,此为叱喝后,头如被震醒。言秦峦欲把头埋被,努力地闭上眼,尽可自好。然而,越赖在床上不动,头晕而愈。言秦峦忽悟一重者——竟不寐矣!天大乱兮,竟不寐矣!
言秦峦莫,以衣服之。先是亵衣,复为中衣,又为袍衣,然后是衣,后再披一帔。卒为善矣,盖又对外之风矣。
亦真是个鬼。言秦峦心,必选在此冷之时练剑,练何武功不好,则好瞎劈劈劈,俄顷又劈石劈木,是非须臾复山兮?是非言大劈孰?梁鹤是个鬼!
言秦峦至门前。顾此与王义忠府也精之雕木门,神情严肃。其复检了一遍身之行头。深衣?衣矣。衣?衣矣。帔?衣矣。裘?谓兮,吾之裘尚未穿?!
甫至门即复返,甚费力地又以裘与披上。然后,言秦峦又至矣门。
其深吸一口气。
“终当临者。”言秦峦谓己曰。
其决意,终,之推也?。是也,此风终是要临之。一生中,有无穷之,如是呼之风之挫。能逃乎?不能!唯对之,战胜之,人生能得令终。对寒!,言秦峦!
风啸一声,寒意袭人,凛然若锥骨。
“已矣。”
言秦峦之又把门关上了。
·
门者言秦峦,在院里俄腾旋,须臾步行,时回挥剑。
好一把青鞘剑,历百年犹锐。闪着寒光的茎干,在空中与梁鹤同旋跃。微青灰色的茎干,若在空留一道青之划痕。衣飘飘,长发起,秀英气。
跨步,下腰,挥斩。一鼓作气,起,从重发,之言前之石劈为两。
夙兴之不光是梁鹤,又有一群人也。自然,梁鸣鹤亦为之主。梁鹤鸣于庭中舞剑,无吩咐,自是无人敢于庭立而。只为着空之事,远远望见梁鹤舞之势,阴或服,或畏惧。
梁鹤瞑目,尽可于此剑与其直觉。闻之远处传来之风,其闻花落地之声,其可闻左右过也,有声之声。众多之声,无一定,天下四。异同之声,持异之问,异声诉而异之事。每惟瞑目,能得此一静凝,一湛之觉。譬如,此剑能言,梁鹤直然。每一把好剑都之有剑魂,而一以战国之遗奇剑,为甚如此。此上百年之剑魂,与死者以深厚之。。每一把都之有体,但多去感,必感之至,至期,以致一矣。
梁鹤立不动,持此青鞘剑,竖在面前,微行此是晨间之,混着香香之气。久之锻炼,使其身直在气。
梁鹤鸣觉有一足于向之近。此意甚是闲,若昨日遂感过,历历在目。渐近,然即此觉。若非昨日已经是觉,其必误以为己真之练能直触剑魂矣。
梁鹤一转,开目,释了青鞘剑,将其收鞘中,曰:“言秦峦你醒也。食欲何图?若其仆不祈州之菜式,我吃不惯。”
观其言秦峦似火冒三丈者。言秦峦披着两件衣,一披肩,拥裘衣,拥炉火,冠袍服,只是目恶狠狠地视梁鹤。言秦峦怒之曰:“大朝之东劈西劈之,胡为兮,造楼兮,不知我在寝兮?”
“然则,此眼视若将至辰之皆。”
“辰算个啥兮?想当初,余皆睡至午后皆为常事。”
“不食?”
“食连午饭共食之固!”
“果为我识之言秦峦。”梁鹤笑焉。
“识什?汝知寝谓予多重乎?”
“多大?”梁鸣鹤一面坐者,问之,曰。
言秦峦气得一旦皆语塞矣,一曰缓也:“一日累得死,眠不善则明日无精,则寿!谓,寿!汝是变而杀!”
“那我奈何?一教之人,总不能辰时复起乎?”
“此,今有辰乎?梁鸣鹤君视是,那日,惟寅而已!且,世间百般兵器,斧、钺、钩、叉、剑、戟、弩,你偏要练剑?练剑而已,你偏要习劈石!劈石则已,汝尚大早劈!”
“你说我练剑,君使之非剑?”梁鹤然地回答。
“此言。为甚我能择也。其不名者先忽而灭,便留了一封信,一室我看亦不知也,,然则以末花剑。汝为我愿兮?那玩意儿告百有余年矣,是传说中最后一把能斩出剑有剑气也,臣能直弃兮?”
“好好好,后不在早劈石头也。”
“劈他亦可!吾之重非石矣!”
“好好,知是也。”
“知,而固不改。该劈劈,当泄,梁鹤鸣子谓吾不知汝乎?”
“好好!今谨者总可乎,吾友言秦峦。”
“谁为汝友!我乃非也!”言秦峦犹怒。
“汝昨夕自言之。”
言秦峦似被浇了一盆冷也,忽然而静言矣。而实非原梁鹤矣,而于思昨日之言。
言秦峦心:我去,我几忘之也儿也都。昨日一讲吁矣,奈何异议皆言?欲不言何事要也?嗟乎,幸无恙,无事。
梁鹤见言秦峦忽而默矣,于是问:“何也?”
“然犹怒兮!我欲往食,以缓我之心。”言秦峦毕,乃步地向门迈出。言秦峦穿得里三层外三者,内地若一蠢萌之子,梁鹤看了忍不住也想笑。
“食,言秦峦,彼欲不往厨下之方也?”
“固非也,心情不好,我欲往旁里且狂食,以慰我心伤者!”
“别忘了下午还约了人。”梁大声曰鸣鹤。
“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