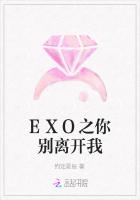白花花的世界,被打开了一个洞,里面渐渐流出黑色的水来,流淌在整个空间,最终化为泪的海洋。
我跟我久违的母亲继续生活在那空洞的家中,某一句话过:人需要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但存在有多个维度,或许我在那个最苦涩最阴暗最寂寞的维度里,不断地盘旋往复。
我觉得世界像是一棵树,上面的花朵映着光芒,艳红嫩绿,而大部分见不得人的根都被埋葬在黑色潮湿的泥土中;有一天,地裂开了一道缝,一缕光照进来。
我跟崔城几乎天天见面,坐在花园内的木质躺椅上,他经常说一句话:
“谁也没有多少朋友,仅仅是自己认为关系好罢了。”
我确实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总能给任何玩耍的孩童带来欢声笑语;我只是想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气氛,我害怕争吵,害怕玻璃碎在地上的声音。
南归的大雁排成了“人”字形,离开了我们的那片天空;我感觉他是个天生的哲学家,他唤醒了我内心深处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真的知道“人”是什么么?
我整天跟人打交道,大人,孩童,每一个人我都不陌生,每一个人我都不了解,我或许根本无法懂得“人”的概念。
我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人。
“为什么我不是人.......”
长期与世隔绝的他总是会问出这句话来,我最开始以为这个问题是抛给我的,但他却总是望向天空。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句尾存在的是一个省略号。
我妈妈跟我叔叔开了一个发廊,外面有两个旋转的荧光桶,我小时候仅仅是很喜欢看它在夜晚旋转所发出的光。
屋里白织灯的光从后面透出来,照亮了玻璃门外的台阶。我几乎不到门的一半,看见妈妈涂着红嘴唇,满脸堆笑地伺候着每一个来理发的客人,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
小时候我跟我她和爸爸一起去高档商业区逛奢侈品店的时候,那些店员一个个都是这种讨好人的表情。
以前我根本没看懂,现在我却看出了面具底下的痛楚,我一下子流下泪来,我妈朝我摆了摆手,示意我离开。
夜晚的街灯好似一个个打着灯笼来看热闹的人,围着我这个孤零零的孩子观望;我感觉有一个影子一直陪伴着我,它跟我说:离开吧,没有人总能陪着自己。
后来有一天律师找到我们家,告诉我妈说:“您好,韩夫人,我叫陈安,是韩长铭先生请来的律师,现在他的服装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他曾经将他的竞争对手鼎级服装告上法庭,理由是对方进行非法集资,并故意抬高价格扰乱市场,现在这场官司马上要开始了。请问他人在哪里?”
我妈妈当时流下泪来,捂着脸扶着墙痛苦到:“长铭,他.....他已经死了。”
律师一阵震惊,语无伦次地说:“什么?!韩先生他.......怎么会这样,两个月前他还嘱咐我说要打赢这场官司,打垮他们公司,这.......”
他夹着公文包转身要走,这个时候我妈妈马上叫住他,“陈律师,请您留下来,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打赢,我们不能就这么忍了。都赖那个溅人,没有她我们家也不会......”她又泣不成声地哭起来。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抬头仰视着那位身材高大的律师安慰着我妈,我看到我妈如此软弱痛苦,我的心仿佛也流出泪来,但我却忍住了哭,我不想让外人看到我们家破落狼狈的样子。
日落之后的月光总会带给迷路的人一缕希望,就像大风吹跑了淋漓的大雨,但也只是一时一刻罢了。
那天妈妈带着我如约地登上了法庭,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几乎花光了仅剩存款中的一半,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鼎级服装给我们的赔偿,虽然对于以前的我们家微不足道,但对现在来说却是一笔巨款,至少不用母亲在发廊里给每一个施恩光顾的客人陪笑脸。
场面几乎是一边倒,我们觉得自己有理有据,但咄咄逼人的却是他们,律师因为没有拿到丰厚的佣金,所以根本没有卖力,眼看着马上就要败诉了。
母亲在原告位上险些晕厥了过去,这时候铁面无私的法官像是呵斥般对着母亲大喊:
“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没有就结束了。”
最后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而母亲舍弃尊严赚来的钱却几乎付之一炬,我们彻底穷了。
我还记得对方坐在被告位上的老板板着个脸,凶狠的眼睛像是要撕裂一切他认为弱小的生物,他临走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妈说道:
“到底还是乡下人,穷命改不了。”
这句话一下子惹怒了我,我一拳就挥了上去,母亲一下子从后面拽住了我的手,把我扽了回来;从她那红眼圈中我看到了苍老与心酸,她仅仅是个三十中旬的女子。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对面高大的老板轻蔑地笑了笑,随手扔给我妈一个袋子,我接住随手打开,里面放着的是一打红纸,是我妈一个月都挣不来的人民币。
我把手缩了回去,这时候一双手一下子夺走了我手中的袋子,随后只听见母亲熟悉的声音沙哑地大喊了一声:
“滚!我们不需要你施舍可怜!”
红色的钞票散落在楼道里,像是一片片樱花飘落在风中,我依稀记得那会儿我敲响崔城家门的时候走出来的那个女人,这种味道是多么相似。
我妈一屁股坐在大理石的地砖上,双手捂着脸哭泣,以前趾高气昂,全身穿戴奢侈品的女人如今却是如此苍老憔悴;而她,却是我至亲至爱的母亲,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7岁的我像是哄小孩子似的哄着自己的亲妈。
看见前面中间那穿着黑色西服的老板,我心里狠狠地发誓一定要替父母狠狠地羞辱他,报复他,他是我一生的敌人。
然而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快点长大,照顾好体弱的母亲,让我们家重新恢复以前富有的生活。
也是那时候,我才懂得,那漫天飞舞的红纸意味着什么:财富、尊严、地位、势力,更多的是别人看你的目光。
我感觉我的世界在一点点地缩小,我经常跟崔城在小区内的躺椅上一坐坐一下午,看着天空一点点地变色。
“你知道么?我们家穷了。连基本的生活都费劲了。以后我可能得去帮我妈妈经常打扫发廊了,现在薪水越来越高,连个小时工都顾不起了。”我向他说着,他是除了我母亲以外第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仿佛都有着魔力,深深地都印在我心底;好像他总有治愈人的力量。
他好像不能理解我话里的沉重与心酸,依旧像往常那样对我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自己厉害了,别人才会高看你一眼,才会把你当成他们里的一员。”
这次我有些呆了,我以为他会说一些以后好好努力,生活会改善之类的话。我又继续说道:
“你以后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呀,或者说一个穷孩子。你们家应该很有钱对不对。”
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想了想说道:
“说实话,我一直特别羡慕你,总有人来找你玩,围着你转,你那么招人喜欢。我好像除了有很多用不完,玩不完的东西外,其他一无所有。”
说完他叹了口气,低下了头,看了看地砖上打架的两只蚂蚁。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便跟他在长凳上坐了很久,我跟他有一个约定:
永远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我变得像他们家那么有钱,他变得像我一样招人喜欢。
各自有各自的梦想,大小不一,方向不同,但渴望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日子像是水一般慢慢地流逝,我好似抓了一把沙子,丝毫没有感觉。每天我放学先到母亲开的那家发廊里去帮忙,看着母亲和雇佣的那个店员一起染了五颜六色的头发,招待一个又一个客人。
我很讨厌那里的气息,仿佛是油腻又刺鼻化妆品的味道,地上满是掉落的头发,有长有短,我点点把他们扫净,然后丢在门外的垃圾桶里;我习惯了听那里放着的流行音乐,无非是一些令人作呕的情感: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偷了我的心,爱你千千万万年。每一次听见那半死不活扁平沙哑的声音,我都像是吞食了一只活苍蝇。
每次帮完忙,母亲都会摸摸我的头,催促着我回家去写作业。我实际上对任何学科都不讨厌,至少我觉得没有比解决那两三行的数学问题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比如说鸡兔同笼,追击问题,数独等等,我还很喜欢玩魔方,那时候连劳技课老师都拼不出来的魔方我都能在最快的速度内把它恢复原状;每次我都得到满堂的喝彩。每一个人都对我投来了敬佩的目光,就连家长也一样,我小时候有一句话是最熟悉的:“韩鑫这孩子真聪明,干什么都行。”
每次听见这样的话,我都会一阵得意;有一天学校组织了奥数竞赛,对于大奖我势在必得;我们学校是参赛的两个最有竞争力的学校之一,而另一个则是崔城的学校。
不可否认,崔城在这方面也十分有才华,但他也时常夸奖我,说我是天才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真心的,要知道,他从不说假话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比喻,我们两个都像是高超的画家:每一种思维,每一个定理,每一个数字,都像是活灵活现的音符与色彩,被我们唯美华丽地涂在试卷上。
那是我们最完美的杰作;我们有着一样对于数学痴迷的心与灵光闪现如涌泉般的大脑。
那次奥数比赛之前,我们两个又像往常一样坐在小区花园里的长凳上;现在的我们仿佛都长大了很多,长凳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窄;我们很遗憾地想过,或许有一天这个长凳只能坐下一个人。
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打算参加这次奥数大赛么?据说这是小学生奥数最权威最大的奖项。”
他几乎是罕见地脱口而出:“我父亲一直跟我说让我报,拿了大奖以后升学用。”
“那你呢?”我继续问道,但我知道这几乎是句废话。
“当然也是参加啦。听从他老人家的安排,当然更多的,是想跟你比比,较量一番,说实话,我觉得你在数学这方面真是个天才。”
听了这段夸奖,我像是吃了一个甜杏,诚实是最好的赞美;对于夸奖我向来不吝啬,但只有对于他的夸奖,没有一句是场面话。
“崔城,你知道么?我认识这么多人,实际上能说真心话的只有你一个。”我说道,看着在半空中飞舞的黄蝴蝶,随着秋天的落叶一点点的飘着,“我总觉得跟你坐在一起很放松,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那是因为咱们两个本来就很像。”崔城打断了我的话,当我看向他是,他嘴角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像是在陈述一件在他脑海里深深记录下的数学定理,“你可能没有发现,实际上我只有你一个朋友,因为我很少下来玩。”
我实际上早就知道他朋友不多,经常关在屋子里学习,但他第一次跟我说出如此走心的话,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羞涩的孩子。
那天下午,我们约定好了,这次大赛我们见分晓,对于小学奥数,我们都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然而事情终究不能如我们两个人所愿。那天老师找到我向我说明了这次考试的情况:考题类型,知识点覆盖,大题分值,考试技巧等等,不断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计算,光有思路拿不了全分,别再犯老毛病。
这些话老生常谈,但她最后一句话,却像一把刀子似的深深地刺入了我的心:“明天就要交报名费了,一共980元整,让你家人准备一下,这次全学校都看好你,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老师的笑容消失冬日的阳光,在寒冷的空气中融化了一地白雪;但我面对着980元的报名费时,就像掉进了冰窖里,感受不到任何零度以上的气息。
那天放学后我按时回到了母亲开的那家发廊,这是个令我作呕的地方,那天母亲正在伺候一位中年男子。
屋里还是回响着有气无力的情歌,对于我一个小孩子来言,根本无法理解被爱情伤了心,虐了情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感情被别人肆意践踏的心情。
母亲每天仿佛几乎都会说一样的话,我习以为常:
“回来了,孩子,好好听讲了没有?今天事比较少,把地扫完就赶紧回去写作业,我今天尽量早点回去做饭。”
我点了点头,照例把书包仿佛皮椅上,今天这间屋子里只有母亲和这位客人,我有些纳闷,便问道:
“妈,那位小哥呢?今天没来上班?”
我看到她的眼神渐渐黯淡了下来,又勉强挤出了笑容,对我说:“他以后可能不来了,正好,也少发一份工资。”
对于母亲这种敷衍我每次一下子都能看穿,便明白那个人是因为微薄的薪水所以辞职了,以后店里就会剩我们两个人。
这对我妈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以后能理发伺候客人的就只有她一个了,我现在恨我自己没有任何手艺,只会徒徒给家里增加负担,比如我980元的奥数比赛报名费。
我拿着那把仿佛裹着黑色胶的塑料扫把扫起屋来,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剃发机的嗡嗡声;吵闹的世界里总有一个深沉的问题,把轻浮的一切衬托得卑微。
“妈.....我....”
我刚要开口,只听见坐在椅子上理发的中年男子一下子站了起来,像是一只咆哮着的熊,对着我妈大喊:
“你能不能看着点?!不会理发就别理!你看你把我的头发都理成什么样子了!我明天还有会,你知道不知道你会对我造成多大的损失?!”
母亲一下子吓傻了,赶紧弯腰连声道歉,像是要把心都掏给那位大叔看。那男的像是一只浑身刷满了鞋油的野兽,圆睁得双目像是要一口气吃掉陪笑道歉的母亲似的,下巴上短短的胡须像是钢针般在他的盛怒之下变得更加骇人。
“你们这些理发的,连基本的手艺都做不好,还来开店害人!”他越说越过分,我看着母亲这卑微的样子,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我一下子把扫把扔下地上,朝他大声喊道:
“你爱理不理!没有求着你!不想理就快滚!”
那人好像很惊讶似的,一脸嫌弃地说道:“瞧瞧,你们这家店真是可怜,你瞧瞧旁边那家,人家那小姐,人家那手艺,怪不得人家客人那么多,你们这家店呀,也就等着关张了!”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嘴里轻笑一声,一个钢蹦儿也没有留下。母亲仿佛被抽了魂,一下子跌坐在皮凳上呜呜地哭起来,嘴里不断地小声嘟囔着一句话:“怎么会这样?他这是今天唯一一个客人。”
窗外车来车往,行走在外的人们像是一群群无家可归的野狗般穿梭,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成长在的这个世界;它好似一个吃人的恶鬼,一点点吃掉我身边每一块可以称之为希望的蜜糖。
母亲继续捂着脸哭着,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是安慰的话,我觉得此刻已经太过无力:
“孩子,都怪妈妈没出息,把家里伺候成这个样子,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你父亲他也是.......”
一提到父亲我仿佛一下子走进了那个充斥着消毒水刺鼻气味的急救室里,看着躺着白色病床上被绷带裹遍全身如木乃伊的父亲;他是个无比软弱的人,散尽了所有能造福家庭的钱财。
她坐在椅子上抱住我的头,满脸泪痕,抽泣着说道:“以后我一定给你一个比以前还要美好的家庭,我会让你考上大学,让你高昂地走进社会。”
这话应该是她说给自己听的;在那一刻,我年幼的心灵早已经敲定了我的未来。
仿佛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的听见了奥数奖牌掉落在地上碎裂的声音,报名费那一把钞票像是被刚才那凶恶的男人的一双大手撕成了碎片。
那天我骗母亲自己的作业已经在学校写完了,一个人陪她在店里做了很久,一地的狼藉没有人来打扫,渐渐在屋里腐烂发臭了。
我做出了一件让所有老师同学都震惊的事情—我退出了这次比赛,原因我说的是我打算抓紧时间复习我的课内知识。为此学校不少老师甚至教导主任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谈话:
“韩鑫,我跟你说,这次奖项的份额你知道有多重么?那个这个奖,几乎就可以走入好中学的大门了。你怎么会能放弃这次机会呢。你还小,搞不懂,过去跟你妈妈好好聊聊。”
我只能敷衍的点点头,便关上了门从办公室离开了,隐隐约约地从门内传出了老师聊天的声音:
“哎呀,你说这孩子真是.......父母也不管管,孩子不懂,家长也不懂么?”
“是呀是呀,没错,这家里人也不管管?孩子还小,懂什么呀?”
如果有一面镜子能够如影随形让我看清楚我的每一缕头发每一丝表情,我或许此刻会看见我阴沉着的脸,像是要下起雨来。
我不懂么?我不想上好初中么?我不想以后考上好大学,成为数学家么?我不想此时跟崔城一分高下么?
或许学校所有人都只看到我如雏鹰般一试高下的眼神,每天都迎着风向着太阳飞去,在我身上沐浴的总是无尽的光芒,远处的人们甚至会把我想象成一只火凤凰。
然而摆在我面前的却很明晰;每一只雏鹰都要在山崖上磕碎自己嫩黄的嘴唇,早日飞向蓝天,这痛楚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那天崔城早早地就在四周落满黄叶的长凳上等着我过来,远远地向我招手。不知不觉,又是每一年的秋季,我跟他已经认识三年了,从一面之情到独一知己;这场面与第一次我俩见面的时候是如此相似,但却相互转了视角。
那天下午他说了很多关于他未来梦想的话:“你知道么,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数学家,真的,你知道么,我们家祖上曾经中过状元。”
我默然不语,这次他话很多,我话很少。
“这次考试咱俩都好好考,我觉得以后咱俩可以上一样的初中高中大学,最后一直到工作,咱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他的话仿佛有回声,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天空泛着一层鱼肚白,仿佛沉淀着迷茫的梦,此刻坐在长凳上的我感觉像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他难得今天说了这么多话,像是一个在四周充满压力的真空空间里的孩童发现了外面世界里的一朵红莲花,轻轻地敲打着透明的墙壁。
“我父亲经常说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努力的强者和懒惰的弱者。我觉得咱们两个都是绝对的强者,以后在一起做事情再好不过了。”他顿了顿说道,“我一直觉得上学和钱没那么重要,重点是自己努力了没有.......”
他看见我一句话也不说,意识到了自己的话不对劲:“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努力.....”
“没关系,我知道。”我抬起头来一下子松了口气,但地下传来的重力一下子翻了好几倍,“我这次不打算参加了。”
他听完这话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我,问道:“为什么啊......明明咱俩都是很有希望的。是不是你觉得你会输给我,所以胆小啦?哈哈哈。”
我知道他在开一个玩笑,因为他觉得我在耍他,毕竟980块人民币对于他和以前的我们家来说几乎就和零钱一样。
“我没开玩笑,这次我真的不去了。”他认真地说道,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耳边直传来沙沙的风声,落叶在地上盘旋。
他用他透亮的眼睛看着我不说话,我俩就这样坐了一会儿,他变回去了。如果我们两个调个个,或许我会转移话题找个他更感兴趣的事聊聊,但现在我却像是被一吨重重的铁块压在地上,无法呼吸。
我一个人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夜晚拉开了帷幕,我像是一个退场的演员在后台一个人反思。那有你大叔对着母亲嘲讽的模样历历在目,崔城仿佛没走,一直在我耳边说着关于他梦想的话,我以前或许会发自内心的祝贺他,但现在那声音却是如此的刺耳。
为什么他可以,而我不行?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任何人都知道:他们家有钱,而我们家没有。但我仿佛用自己幼小稚嫩温热的胸口贴在了南极冰天雪地里一块冒着冷气的寒冰之上,渐渐的,连流动着的血液都好似冰河里的水,全身的肌肉都变得僵硬。
后来结局就跟我预料的一样,他拿了金奖,被多所好初中点名要走,他很兴奋地跟我说,打到他家里的电话络绎不绝,几乎全都是祝贺和鼓励的声音。
他是个透明的孩子,只能在一个不被注意的地方看到所有人外表上的温和与冰冷,所以毫不遮掩自己得来的一切;那是他的成功,分享成功的喜悦对他来说估计是无与伦比乐事。
我想往常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最美好的话语祝福了他,以后前途无量,实现梦想这一类的话。
那天我挤在颁奖典礼上,看见他脖子上挂上了金灿灿的奖牌,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耀眼,映照出了他天才般的辉煌。
主持人继续用洪亮的声音说着:“现在请各位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颁奖。”
这次比赛的发起方很有心,这是个新加的特殊环节,让家长也有了炫耀的资本,让孩子体验到作为父母的骄傲,一举两得。
那天我看到崔城站在中间,透明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梦想如灯般被点亮的那一刻,紧接着家长走了上来。
他的父亲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当他转身的那一刻,我震惊了;看到他父亲的那张跟他一样棱角分明的脸,我的心里仿佛被缠上了毒蔓藤,所有的毒素都一点点渗进心里。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些在楼道内飘散的红纸与那个不可一世的高大背影;我永远也忘不掉那天瘫坐在地上痛哭的母亲;咄咄逼人的法官,软弱的律师,看热闹的观众,那天法庭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雕刻般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摧残着我的每一缕神经。
崔城的父亲,跟鼎级服装公司的老板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我希望这个才是真相;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他们两个是一个人。
他是逼死我父亲,搞垮我家庭的元凶,而崔城则是这个恶魔的儿子。
那一刻我不敢再直视这个世界,仿佛每一缕光线都伴随着嘲笑的声音从窗外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