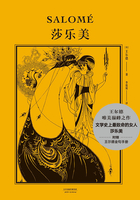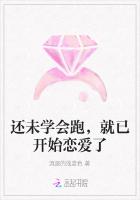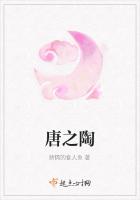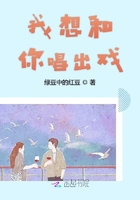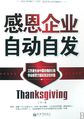一个朋友看过我的书房,问我为什么不捐点书出去。看我反应不积极,就笑我是小气鬼。“真是一毛不拔。”他说。
他说得不错。但我并不是没有过捐书的念头,特别是像他说的,书架已经塞满,有些书完全可以淘汰掉的。但是淘汰哪些书呢?虽不敢说架上的都是好书,但都是我精心选购的。有些书是我的至爱,那自然是不舍得捐出去的。有些似乎可以,比如说版本、装帧不满意的;内容不是很喜欢的。但等到真要捐出去时,却又像鸡肋一般有点舍不得了。毕竟版本虽然不好,但并无复本;内容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但至少还有资料的价值。如果实在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我也不好意思捐出去了。就像捐赠衣物,很多机构都要求至少七成新以上,而我自己有些穿了十几年的衣服还不舍得丢掉,又怎么好意思拿这些穿旧的衣服去献“爱心”呢?
其实除了以上原因,我还有听起来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书即便捐出去了,真的能发挥它的价值吗?虽说书不像钱、电脑、大米、食油,甚至七成新以上的衣物那么招人喜欢,在捐赠的过程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但对于它能不能发挥捐赠者预期的作用,我也总是心存怀疑。我的担心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孩子们的手中,他们会看吗?能看吗?学校会准许他们看吗?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可以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我的老家还不算贫困山区,虽然也称不上富裕,但学校里图书室还是有的。小学的图书室我没见过,之所以知道有,是因为一个要好的同学父亲就是我们那所村办小学的校长,我曾在他家里见到套装的《西游记》,问是哪里来的,才知道学校还有图书室。当然图书室我是没有眼福看到的,估计里面的图书,就像这套《西游记》一样,只能供校长和老师们专享了。我那时还小,民主、权利的意识还没有,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太对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我爸不是校长。
初中跟小学差不多,虽然也有图书室,但也从来没见过,更狠的是,学校不仅不开放图书室,见到我们读课外书还要没收。我自己就被校长没收过一本《陈真传》。当时是晚自习后准备睡觉前的那个空档,就连这个时刻校长都不肯给我们一点阅读的自由。我自然无话可说,唯有惊恐。要说我也当过帮凶,初中二年级,我因为学习成绩还好,被任命为班长,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课间操时和班主任一起搜同学们的书包,看到课外书就没收掉。大家似乎也都习惯了,或者自觉有愧,做完操回到教室,看到书没了也不敢吭声。记得一次搜出的是一本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名著《高山下的花环》,课本上就有节选,但那时不懂,交给班主任,仍旧没收掉了。现在想来都感到惭愧。试想,在那样的气氛之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学生们的手中又能怎样?
我还算是爱书的,但小学、初中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仅有的底子是小学时买过的几十本连环画。我上初中时,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入迷,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爱看武侠小说的同学手里捧着一本书,正是《射雕英雄传》,不由大为吃惊。我说不是电视剧吗?怎么还有书?孤陋寡闻可见。但那时也有对付老师的办法,我没有试过,都是看那位嗜武侠小说如命的同学在实地演练,刚开始是在课桌上挖个洞,小说放在桌兜里,一行行移动。后来被识破,就剑走偏锋,将书一页页撕开,一张张地看,即便被查收,损失的也仅是几页而已,不影响大局。我想很多老师肯定对他这一招十分懊恼,因为我知道有些老师,收书的积极性之所以那么高涨,除了迫于中考的压力,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也爱看。
高中时好一点,许是我读的是省重点高中,眼界和胸襟与普通高中有所不同。学校历史悠久,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木质图书楼,每周开放一天,供大家自由借书。虽非完全开放式,也已有开架的雏形,书脊顶着玻璃,站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书名,喜欢哪一本,用手指一指,管理员就可以帮你取下。高中时我因此读了不少书。但到高三,风声就紧了,图书馆虽然仍旧开放,但班主任却收紧了政策,记得有一次,我借完书正要出门,突然看到班主任进来了,心慌手乱,忙找个地方把书藏起来,班主任对我盘问半天,矢口否认,他看我两手空空,才放我过去。
也许真的是因为看课外书太多,第一年高考失利,复读的那个学校是个县重点,图书馆比省重点明显差了许多,首先没有单独的图书楼,只是一个小藏书室;其次偶尔才对学生开放,也只局限于低年级的学生。毕业班的学生自然应以高考为重,否则明显就是不务正业。所以就冲这一点,如果今天非有人说我是那个学校的校友,我是誓死不认的。
大学自然不用多讲,也不是我们捐书的对象。假如以上列举的情形没有变化,那么即便有书又能怎样?有书和没书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就别怪我对捐书持这么悲观的态度。
但也许现在比我那时候已经好了许多,学生们已经可以不用理会升学的压力,自由地阅读课外书了。毕竟我离开中学校园已经十几年了,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点进步。但不知怎的,我总是乐观不起来,因为我对我的乐观也悲观起来了。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或许我也会慷慨大方起来,即使只为不被朋友说成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