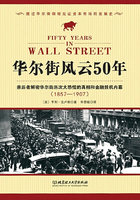法朗士是群星璀璨的法国文坛上一位博学的文学宗师,法兰西学院院士,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认为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和评论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斗争,被看作他所生活的时代法国最重要的良知之一。在他去世后,时任法国众议院院长的保罗·潘勒维闻讯感叹说:“昨夜,人类知识界的水平下降了。”法国在巴黎为他举行了国葬。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原名雅克-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波(Jacques-Anatole-Fran?ois Thibault),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其父曾入伍从军,1830年革命后离开军队,在巴黎经营书店。他的书店主要提供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著作和资料,经常有许多作家和博学之士光顾。在父亲的藏书中长大的法朗士从小就受到书籍的熏陶,在博览群书中积累了渊博的学识。法朗士尤其热爱人文科学,有着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了如指掌。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法朗士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创作,曾拜法国著名诗人、帕纳斯派首领勒孔特·德·李勒为师。1867年法朗士加入帕纳斯派。他的第一部诗作《金色诗篇》发表于1873年,之后又创作了以希腊人生活为题材的三幕诗剧《科林斯人的婚礼》(1876)。法朗士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晚,成名作是他三十七岁时发表的《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1881),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善良、亲切、敏感、富有正义感、宽厚又有点可笑的老学者形象,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并受到法兰西学院的嘉奖。
法朗士的作品体裁多样,涉及小说、戏剧、回忆录、历史等。历史和社会政治问题是法朗士偏爱的主题。如小说《苔依丝》(1890)反映的是四世纪的宗教斗争,长篇四部曲《现代史话》(1897—1901)的主题是教会和德雷福斯事件,同样影射德雷福斯事件的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小说《企鹅岛》(1908),《诸神渴了》(1912)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审视,而《圣女贞德传》(1908)用唯物主义观点和写实主义手法重写了传奇历史人物圣女贞德的一生。此外,法朗士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曾为《时报》《新杂志》等多家重要的报纸杂志撰写文学批评及其他评论文章。
法朗士的作品风格典雅,文笔优美。他的行文看似平如秋水,却含蓄隽永、韵味深长,字里行间经常透着幽默和讽刺,流露出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绪,同时不乏人道主义的关怀。法朗士的文学理念与当时法国盛行的追求科学客观性的自然主义文学截然不同。他推崇想象的力量,作品经常充满奇思妙想,带着梦幻的色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法朗士的创作深受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影响。他虽然酷爱书籍,但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作家,而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直很关注他所处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功成名就、具有一定影响力之后,法朗士越来越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法国历史上曾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态度,他坚定地站在曾经在文学创作观念上和他有分歧的左拉一边,支持德雷福斯。在左拉发表公开信《我控诉》之后不久,和左拉一起最早在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的第一份知识分子的请愿书上签名。在左拉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立场而被收回荣誉勋章后,他退还了自己的荣誉勋章以示同左拉共进退。二十世纪初,法朗士从德雷福斯派转向支持社会主义,反对教权主义,主张政教分离,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批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殖民野蛮。1921年,法朗士加入法国共产党,在法共党报《人道报》上发表文章。但这些斗争和行动最终令法朗士感到失望,1922年后,法朗士不再与任何共产党报纸合作,并与各党派保持距离。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经历使法朗士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带着乐观主义色彩,伴着善意的讽刺和怀疑主义特点,那么后期作品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讽刺也变得尖锐,富于战斗性,同时表现出对正义和真理的热切追求和人道主义的情怀。
1885年出版的《小友记》是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由法朗士在1879年到1884年期间陆续发表在《新杂志》《政治文学杂志》《时报》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组成。这部回忆录出版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普法战争的法国推行一种科学教育政策,整个法国笼罩在“客观性”“科学性”的氛围下。这种现象不仅充斥着科学领域,还蔓延到了哲学和文学领域,尤其反映在主观性很强的小说创作中。自然主义文学的盛行就是受追求科学这一观念的影响。法朗士对这种在文学中追求客观性和科学精神的观点持拒绝和反对态度,他曾不止一次公开嘲笑左拉式作家的科学抱负。这并非因为法朗士对科学一无所知,恰恰因为他本人曾经历过信仰科学解释的价值的阶段。在帕纳斯时期,他曾热衷于泰纳的实证主义批评理论、史前考古发现、生物学发现,以及对应于自然进化的社会进化等。但法朗士发现科学言论本身也是有争议性的,并非绝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并没有给出关于宇宙的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法朗士转向了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相反,一切都变化不定,转瞬即逝,这一相对主义影响了他的文学观。与当时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自然主义作家相反,他否定文学属于客观范畴的观念,肯定文学的主观性,认为作家在创作中,不管写什么,写的都是自己,不管研究什么,总是走不出有限的智力和感受力。而回忆和自传就是游离于外界的客观估量的主观文学,《小友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撰写《小友记》的另一个原因是法朗士对自传和回忆录一直青睐有加。这是因为自传和回忆具有某种永恒性,它不受时尚的影响,不需遵从按某个时代的喜好强加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回忆触及的是我们内心的真相。他在1887年3月20日就龚古尔的《日记》回答《时报》时说:“一个作家的回忆是我们在他作品中所得到的最持久、最个人的东西。可能一个作家的作品几乎被遗忘的时候,他们的回忆录仍然会有人读得津津有味。”[1]他认为作家只有在谈到自己的时候才是最伟大和最感人的。而比起普通人自发和非正式的回顾,作家笔下的自传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在法朗士看来,回忆是为了“赋予生活一个美丽的画面”。[2]《小友记》就是法朗士用童年回忆描绘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
《小友记》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皮埃尔篇》和《苏珊娜篇》。《皮埃尔篇》包括《牛刀初试》(共七章)和《新爱》(共十二章)两部分,讲述的是皮埃尔·诺齐埃的成长经历;《苏珊娜篇》包括《苏珊娜》(共四章)、《苏珊娜的小伙伴》(共三章)以及《苏珊娜的藏书》(共两章)三部分,前两部分讲述的是苏珊娜及其朋友的童年趣事,最后一部分是就儿童书籍和童话议题的思考。作者融合了一系列神话研究文章,参照十八世纪神话集编写者的研究,对涉及童话的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说。
从表面上看,《小友记》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似乎都有些松散,缺乏传统自传中的那种整体性和连续性。首先在结构上,全书都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作品的各部分及章节之间都相对独立,而且是由几个不同的童年组合而成的:《皮埃尔篇》像是作家对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而《苏珊娜篇》前两部分则是作家女儿苏珊娜及其小伙伴们的童年趣事,最后一部分的主题转向了书籍和童话。但是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者的巧妙用心:如果说《皮埃尔篇》代表了“我”个人的童年回忆,那么在《苏珊娜篇》中,苏珊娜及其朋友则无疑代表了泛指的童年,即不同时代、所有人的童年,而最后涉及童话的部分则上升到了象征意义上的童年,人类的童年,即处于远古神话时期的人类。因为童话是童年时期的人类想象的产物。从个体到普遍,最终汇合到人类集体,法朗士显然是用这种更宏观的线索将作品各部分之间连接在一起,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内容上,作品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从童年趣事到校园生活,从古希腊人文经典到法国大革命,从考古、人类进化到对美的哲学思考,从对儿童书籍的看法到对童话的见解等,可谓五花八门,并随不同的主题而呈现不同的风格。但是这些主题多样化的章节并没有破坏整体的和谐,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影响故事的核心本身和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从皮埃尔的成长经历到苏珊娜的童年故事,再到对书籍和童话的见解,几条重要的主线贯穿着整部作品:那就是对书籍和艺术的推崇,对童年、想象和激情的颂扬,对历史传承的肯定。
“如果生活可以在书本中间化作一个漫长而温馨的童年,就让我们祝福书吧!”[3]无论是在《皮埃尔篇》中还是《苏珊娜篇》中,书籍和艺术都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成为主人公成长和自我塑造的精神食粮。在《皮埃尔篇》中,书中的世界无处不在,并和现实生活交融在一起:小皮埃尔夜晚入睡前看到的怪兽来自他看过的版画书;《爱德华的孩子们》与一幅流行的画和一个古老的传说分不开;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童年的《一串葡萄》中,旧版画《圣经》中亚伯和该隐的故事让在亲人的精心呵护中长大的皮埃尔对无人看管、整天闲逛、招猫逗狗的洗衣妇的儿子的感情从羡慕转为怜悯;《隐修植物园》受到《圣徒传》的启发,是对圣徒言行的模仿;勒博老爹则因为擅长编目录而受到皮埃尔的无比崇拜;对祖母和家族的回忆带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印记;而课堂和老师带给他的最大收获是诗歌的启迪和人文经典的启蒙。《苏珊娜篇》更是对书籍和童话的重要性进行了直接的阐述。
皮埃尔的童年是一个与书为伴,从书中感受世界、认识世界的童年。古董市场、旧书摊、版画、《圣经》、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维吉尔,这些都是他的领路人、导师和安慰者。塞纳河畔的旧书商和大学老师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地启迪了他的智慧。他从孩提时代起就从那些被蛀虫啃蚀的旧书、被腐蚀或蛀空的版画中深深感受到事物的流逝、生命的无常和万物皆空。而文学作品更是滋养了皮埃尔的心灵,培养他的品位和情操,让他得到美的享受。法朗士对古希腊罗马人文经典尤为推崇。他认为没有比通过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能更好地培养一个人的了。他在书中写道:“文学修养赋予已经足够有能力接受它的心灵的是一份高贵、一种优雅的力量和一种美,那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获得的。”在《皮埃尔篇》中,我们看到皮埃尔在随身携带的维吉尔的诗中找到爱的启迪,在课堂上陶醉于荷马笔下动人的画面,在冬天傍晚街头的路灯下沉迷在古希腊悲剧中,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游离在街头烤栗子的香味和书中虚构的世界之间……书籍滋养着少年皮埃尔的心灵,陪伴着他的成长,塑造他的自我,也成为对不如意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补救。的确,相对于永恒的书中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了变数,美好的表象常常不堪一击:皮埃尔从小迷恋的年轻美貌的白衣夫人多年以后变成了和她姑妈一样的黑衣夫人;仙女般的教母最终成了一位备受爱情折磨的不幸女人,死在海上成了孤魂野鬼;令中学生皮埃尔初次感到意乱情迷的寡妇冈斯夫人再次出现时不再让他脸红心跳;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的勒芙尔小姐是个病态、平庸、蹩脚的诗歌爱好者;而令他肃然起敬的、代表上帝在人间的朱巴勒神父则在颁奖仪式上“像一根拐杖或一把伞一样被扔在角落里”……所有这些令人感慨、遗憾、伤心、失望、哭笑不得、变化无常的现实与美好的书中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书籍无疑是对现实生活的最好的安慰和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