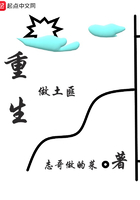哈孝明打马飞奔,耳听阵阵鼓声,余光已看见一艘艘鹰船,心头一喜,已知高二郎使用的战术了。再看前方,一块块布幔拉开,露出一辆辆鸡公车,上面皆是尖刺与木柴之类的燃烧物品。一百多名乡兵站在了鸡公车后面,手持着火把。
哈孝明纵马掠过了鸡公车之间的狭长道路,拉住了马缰绳。像其他骑兵一样,行注目礼,欣赏着火光冲天的这一幕。
“原来你是要用火攻啊!”
哈孝明第一次有了笑容,那笑容里还带着悲哀,这把大火用来祭奠死去的爹娘、妻子。
“吱呀呀”鸡公车瞬间合拢,成为一道屏障,乡兵们点燃了鸡公车,狭长的道路,前后两头,都被大火阻隔。三里长的死地上,蒙骑成了活靶子,上千匹战马首先遭到灭顶之灾,它们目标大,被箭矢射中,纷纷倒地。
蒙古鞑子死到临头,想到了活下去的办法,一个个躲在死马后面。胡尔察咬牙坚持着,看着前方的火光,这把火烧不死他,他会以十倍百倍还给这帮明军。
胡尔察对着身边那名向导问道:“那船上插着什么旗号?”
汉奸向导回道:“是高字战旗,黑色旗帜不是明军旗帜,应该是地方豪强的乡兵。这北口县没哪家乡兵有这么强实力,应该是隆地县大豪强高二的乡兵。哎呀!”
汉奸向导被一个燃烧的陶罐击中,整个人身上皆是石油,疼得他上蹦乱跳,又开始满地打滚。
胡尔察挥刀,一下了断了这名汉奸狗命。挪了一块地方,以躲避飞袭而来的陶罐子。只要不是被燃烧的陶罐直接砸中,活下来的几率还是很大。在他附近,皆是像他一样躲来躲去的蒙军。被河道上箭矢杀伤的蒙军,大概有一半。另一半蒙军都完好无损,趴在地上。身处死地,一个个胆战心惊,害怕敌人还有后招。
这次高二郎没用震天雷与“二斤半”,而是出动了刀车。但见一艘大船靠岸了,放在了跳板,两名乡兵推动一辆刀车上岸了,在他们身后是三名钩镰枪兵、一名刀盾兵与一名鸟铳兵,以七人组成一个战阵。
刀车有一百四十斤重,高过六尺,树立着一块铁皮挨牌,上面皆是尖利的铁茅。
当四辆刀车并排,基本上在道路上平推。
两排刀车之后,是两排刀斧手,共有十名刀斧手,一个个穿着沉重的步甲,怕是要有六十多斤重,再加上十多斤的长柄战斧,整个人负重将近八十斤。步战基本上是不怕刀砍枪刺的,唯一能打死他们的是重武器,而且要不断的击打。
戴着红领巾的军号手,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十艘大船都已靠岸,一辆辆刀车被推上了岸,杀声四起。
尚存的五百多名蒙军迎来灭顶之灾,看见那骇人的刀阵,知道末日来临了。面对杀上岸的乡兵刀阵,负隅顽抗。弓箭射不穿刀阵,短兵器不能靠近刀阵。甩过刀车的重家伙,被挡飞了。
“嘭”一声铳响,十几步开外的掣电铳开火了,铳管上方,冒起一股黑烟。
邓发军习惯性的闭眼,再睁开眼睛时,前面那名身穿白银盔甲的蒙军已然倒地,应该打死一名蒙古贵族子弟。邓发军飞速转动一下转轴,另一个子铳接入药室,火绳上的火星很快点燃了子铳里的药包,
“嘭”又声铳响,十步距离的蒙军身上打了一个小洞。铅子破甲而入,在身体里以不规则方向运动,搅烂了五脏六腑,这名蒙军惨叫着,身体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倒仰而死。
前有刀车挡着,邓发军觉得自己变成了神射手,第三个子铳接入药室,这次他直接把铳口顶住了一名蒙军肚子。
“嘭”邓发军眼睛差点睁不开了,脸上全是血肉。
“驴球子!”
邓发军骂骂咧咧,手按在转轴上,准备开放第四个子铳,可眼前已无蒙军身影。三名钩镰枪手抢在他身前,正杀得兴起。邓发军还在咒骂,说出来脸红,他这个乡兵大队长,是他第一次杀敌,跟随东主之后,寸功为立,好不容易逮到机会,又被钩镰枪手搅合了。他的掣电铳里还有三个子铳没有使用,这仗打得无趣。
三十步开外,倒是有个目标,那名蒙军正在开弓射箭,可惜没有十足把握。邓发军用铁护臂挡住了来箭,有仇报仇,等他靠近了这名蒙军,再装上第四个子铳。这掣电铳真是好武器,配合战阵作战,杀人如砍瓜切菜。
按理说,明军高级将领手中也有一些掣电铳,怎么就使用不好掣电铳呢?掣电铳射距短,可杀伤力大。与冷兵器配合作战,把敌人放在跟前,简直把敌人当做活靶子。
邓发军终于寻到机会,子铳转入药室,铳口对向了一名蒙军,叫道:“武豪,闪开。”
刀盾手武豪一个滚翻,离开了险地。“嘭”武豪再次出击,一刀捅入那名蒙军心脏。
数百名蒙古鞑子不甘心束手待毙,最后的疯狂,猛扑向刀车阵,要以血肉之躯,杀出一条活路。一具具死尸挂在刀车的铁茅上,钩镰枪手根本来不及清理,掩杀而来的蒙军踩着同胞的尸体,爬上了刀车。
邓发军早已射光了六个子铳里的铅子,来不及装药包,扔掉了掣电铳,拔出了十斤重的雁翅刀,护在了钩镰枪手黄光容身边。他们就算战死在此,也不会后退半步。在他们身后还有重甲刀斧手;旁边河面上,还有弓箭手;身边还有同生共死的战友。
平时训练得再刻苦,也不及这场惨烈的战斗一成。乡兵仗着甲固仗利,明显占据上风。战场上,旁边就是战友,人挤人,根本不容躲避,刀砍枪刺,基本自顾自的砍杀,不看敌人使出的招数,就看谁命硬。
蒙军虽然占得身体优势,刀沉力大,持久力强。但他们是轻甲骑兵,身上护甲轻。乡兵一刀就能破甲,而他们两三刀下去,才砍破乡兵二层甲。你一刀,我一刀,互相砍杀。蒙军大致遭受两刀就扛不住了,等到遭受第三刀,便是重伤倒地。
没有了战马的蒙军虽然很拼命,但肉搏战不是乡兵对手。这些乡兵体格强壮,在力量上稍许差蒙古人一点,但经过刻苦训练,体能绝对出色,武艺早已突飞猛进。在最血腥的砍杀中,不遑多让。
道路两边清理完毕的刀车阵,继续往中间压缩,互相对砍的区域越来越小了,小股蒙军已成强弩之末。
河面上,箭矢直射,还在取蒙军性命,这里注定是一场大屠杀。蒙军人数迅速下降,承受不住的蒙军跳入了河中,也许能躲过鹰船上钩镰枪手的刺杀。倒是真被十几名善于游泳的蒙军,逃出生天了。
乡兵们正在打扫战场,砍下一颗颗蒙古鞑子脑袋,搜寻着财物。以战场缴获规定,他们能取三成财货,但先要全部上交财货,战后统一下发财货。
已上了大船的哈孝明看着岸上的乡兵,激动不已,“高招练百户,你我算是平级。这样好不好,我从现在开始跟随你作战,听你差遣。你只要让我砍蒙古鞑子脑袋,让我干什么都成。”
高二郎心平气和的说:“那你看懂怎么打仗了吗?”
“看懂了!把敌人吸引到死地,然后给予致命一击。一颗人头也不放过,这才叫大胜。若像我这样骑兵互相搏杀,一颗脑袋也捞不着,得不偿失之举。”
哈孝明感慨万千,那高二郎指挥艺术太高超了,才数百人马,就砍杀上千名蒙古鞑子。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能跪在高二郎脚底下。很想花钱买些蒙古鞑子人头,可又一想,高二郎铁定不会同意,那只有希望下一次战斗,他能参与其中。高二郎算无遗策,一定还布置了下一个口袋阵。
高二郎道:“看在你还敢战的份上,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下次作战用你当敢死队。你要多少颗人头,才能晋升一级?”
哈孝明道:“我手下四名兄弟也能当敢死队员,他们要有四十颗战功人头,给个前程。我要两百颗战功人头。”
高二郎问道:“哈孝明,你要两百颗战功人头,要当多大的官啊?”
哈孝明颇为尴尬的说道:“我要将功赎罪,两百颗战功人头,才有出头之日,能当上千户、或是实授千总。若镇羌堡、四城堡、得胜口堡、巡河堡、五家堡都失陷,凭这点战功,我总可以镇守一个堡寨。至于游击、都司、守备这类官职,我怕得不到。”
“那我问你,以后还干走私买卖吗?”
哈孝明义愤填膺的说:“你这不是诛心吗?我爹娘都死无全尸了,我岂会再干走私买卖。”
高二郎瞥了一眼哈孝明,“以后再去西域了,就打过去。”
哈孝明假装咳嗽一声,好像是被硝烟熏的。原来高二郎知道他的背景经历,早已研究过他。看来松林道劫案,果真是高二郎干的。这次白面村伏击蒙古鞑子,与松林道劫案如出一辙。
火势越来越小,波澜不惊的河面上,十艘大船依旧在葫芦口。大量的蒙古鞑子已经靠近了岸边,正在扎羊皮筏子,准备渡河。
二十艘鹰船再次出动了,迎向了渡河口。蒙古鞑子赶紧后撤,箭如雨下,还点燃了火箭。射向了鹰船。二十艘鹰船这才后撤,军号声不断,似乎在吹奏胜利的号角。
小歹青建立了可靠的渡口,搭建了一座浮桥,这才引兵前行。崖边的道路上,皆是一具具无头尸体,兵甲也不见几具。那些战马的马鞍、褡裢、背囊等物品也已不见。只救起躲在河道的十五名幸存者,打听之下,才知这支水军是乡兵,隶属于隆地县大豪强高二。
小歹青气得暴跳如雷,下令连夜追击这支船队。询问刚获得台吉身份的夏鹤山,关于高二的情况。
夏鹤山倒还是一身儒服,戴着四方青帽,手里转动着念珠子,“高二,乃五家堡人氏,不过他家人皆在西台山上,乃是强盗出身,手下有一大帮为他卖命的强盗。他的官职是隆地县副巡检,管辖着一个县的水路枢纽,所以他在水上很有实力。想到打他七寸,让他实力大损。那要上山打山地战。我军要舍弃战马,闹不好要落入高二设置的圈套,怕是得不偿失啊!”
小歹青叫嚣道:“那难平我心头恶气,如何能打痛高二?”
夏鹤山道:“那先烧了他的水路巡检衙门,不过,我想那个水路巡检衙门也就剩下一个空壳子了。要想打疼他,只有攻下隆地县县城,高二的产业都在县城里。他的老丈人就是隆地县知县,很有可能他要去救他老丈人一家。”
“好!那我就兵发隆地县,打下县城,屠光所有汉狗,为死去的族人报仇雪恨。”
小歹青的人马只攻下了一座数千人的四城堡,他一共出动了上万族人,用以搬运抢劫而来的财货、汉奴。一个四城堡的财货根本不够分的,正想寻找下一个目标。一大群将领围着桑纸地图,定下行军路线。嘱咐手下将领,对于河道附近地形,要小心提防,不要着了高二的鬼魅伎俩。
原本蒙军集中主力,先要攻取北口县县城,现在小歹青带领四千精兵兵发水陆关。至于部落数万名搬运财货的老弱妇孺,则留在了边关附近,没敢深入明境。
各路蒙军分头出击,已经攻下了镇羌堡、四城堡、得胜口堡、巡河堡、五家堡。但在磐石堡遇见一块难啃的骨肉,顺义王卜石兔下令围而不攻,他们既然攻下了得胜关,大军有了退路,无需在磐石堡消耗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