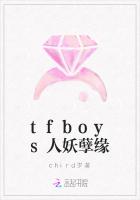时至正午,天空却灰暗暗的,巨大的墨色云团积压在头顶上空,光秃秃的树梢上伫立着两只不知名的鸟儿,视线落在同来访者脸色同样苍白的墓碑上,黑白照上的笑颜是天地间唯一的色彩。
南风今天出院,这是他醒来的第七天,从医院直奔墓园,期间孟秋的电话一直在响,她推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只为了亲自开车送他来墓园。
途中孟秋说:“买束花吧,望春喜欢粉玫瑰。”
南峰拒绝了她的提议。
也拒绝了孟秋陪他进入墓园,劝她回去开会,会议结束后再来接他。
当然这些都是推辞的借口,他想单独跟顾望春说说话。
孟秋明白,于是看着他进入墓园后驱车离开了。
南峰盘腿坐在墓碑前,照片上的顾望春三十九岁,是去年拍的一组证件照,那时候没想到,那么快这张照片就会被褪色贴到刻着她名字的墓碑上。
他们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世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时间只有四十年。
谁会觉得自己只能活四十岁呢?
关于死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老去,老去似乎是死亡的前提。
可是顾望春她才四十岁。
她还没有眼角生出掩不住的皱纹,还没有长出白发,没有步履蹒跚,就在最好的年纪最好的季节和世界说了再见。
顾望春死了,南风也死了一次,如果是真的随她去了也好,可是他好像只是做了一个冗长的梦,梦里他可以有重来的机会。
但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梦就醒了。
每一次闭上眼那一刻他都祈求自己再睁眼的时候可以回到那个梦中。
“顾望春,你说那个世界真的存在吗?”南峰声音很低,风一吹就散了,散落在梢头鸟儿的羽翼上,那浓厚的悲伤如一把利刃穿过羽翼刺破皮肉进入血管,鸟儿发出一声悲鸣,扑腾扑腾翅膀,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我走了,那个南峰他还记得那些事么?”
夏日的尾巴被初秋的第一缕热风卷走,蝉鸣是懒洋洋的,人也是。
陆潇潇支着胳膊半挡着脸打瞌睡,作掩饰用摊开的书上全是鬼画符。
顾望春桌上铺着卷子,手心起了细汗,润湿笔杆。
窗口突然冒出一颗头发茂盛的脑袋,顾望春不经意地一碰身旁人的胳膊肘,陆潇潇瞬间惊醒,在惊醒与写题之间无缝衔接地翻页,认真得仿佛刚才只是在沉思。
老李信步走进教室,巡视一圈收缴了一部手机后满意地离开。
陆潇潇心有余悸地回头瞄了瞄,呼出口气,“吓死我了。”
顾望春把自己的作业本扔给她说:“你赶紧补作业吧,下课就得交了。”
“什么作业啊?”
“英语。”
“我去刘孔雀真的有病!”陆潇潇边嘴里骂着,边愤愤地翻出作业本,照着顾望春的抄起来。
顾望春叠好卷子,整齐放进文件夹里,从桌肚里掏出了白色外壳的日记本。
陆潇潇瞥了一眼,说:“你又在记录你的梦了?”
“嗯。”
顾望春做了一个梦,真实得让她几乎分不清此刻她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
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
那个人的声音、笑容、掌心的温度,都清晰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
但是这只能是一场梦啊。
因为他,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