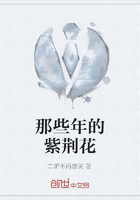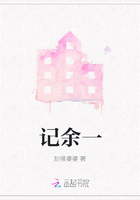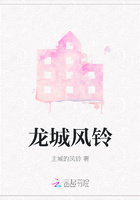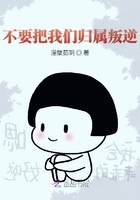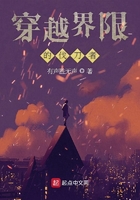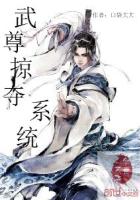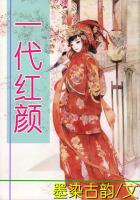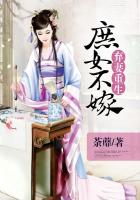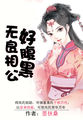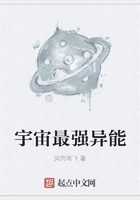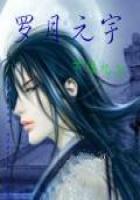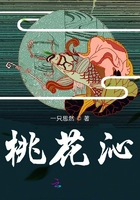多多的左邻六是小明。小明其实不小,他今年46岁。他原是中关村某公司的程序猿。据说很有钱,自从他父亲意外去世后他决定转行搞创作,写出自己对父亲的愧疚与思念。为此,他辗转来到圆明园做了一年保洁,并租住在福缘门Z排Z号。2017年,他在保洁部的工具间搁了一张书桌,正式开始写作。某个星期三的早晨,小明到写作屋打开电脑时,电脑显示07:42。他立马投入写作,但因为没吃早饭,他很快就头晕了。真是“欲速则不达”,本来他对吃早餐是很坚持的。就这天想脱稿而省略了早餐,结果脑袋出状况了。
一人过日子,吃饭始终是个问题。不吃头晕。吃吧,浪费时间呢。何况他的时间宝贵着呢。他40多岁了还没正式恋爱,就是怕恋爱耽误时间。为此,导致父亲意外去世。父亲去世后,他时间抓得更紧,很想写出惊世长篇,让世界人民知道自己是如何地愧对父亲。他哪里有时间吃饭呢?为了他的文章更有分量,6月19日开始泡图书馆,6月19日至6月22日,他早晨九点走进图书馆,不吃不喝不拉,一直坐到20:45提醒闭馆的广播响起,才意识到得马上去喝两杯水才行,要不可能会在路上挂了或在车上晕过去了,毕竟一天就吃了个早早餐啊!他的早餐比一般读书人吃得早,通常在早晨5点左右,反正不超过凌晨5点半,名无其实的早餐。但转念一想,也觉得不至于晕过去,毕竟自己这几天每天都是吃了早餐的。而且很多人三餐加起来还没他一餐吃的多呢。他的老家有个“三三得九,二五一十”的俗语,说的是有些人想节省,改一日三餐为一日两餐,本来每餐只能吃三两米的,改吃两餐后饿得慌,一餐得吃五两米才能吃饱,这样一来,本来每天只能吃九两米的,吃两餐后一天得吃十两。小明一天只吃一餐饭,也就直接“一十得十”,这按说没啥不好。当然,胃还得好好保护,确保吃下去的食物得到充分消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到了空调屋,务必穿上夹克,穿上冬鞋。让身体有微汗感。这样能暖胃,也就能保护胃的功能。总之他小明的时间很宝贝,吃饭绝不白吃,吃了一定充分消化。这样的话他一天吃一顿饭理当不碍事才对。
关于一天吃一顿饭可节省大量时间的问题,这里也得展开来分析一下。通常自己做饭,一顿饭得花去两个小时的功夫。去饭馆吃饭,来回得四十分钟,消化得半个小时,也就是吃一餐饭得花上70分钟,三餐下来至少得花160分钟。他一天吃一顿,虽然早餐自己做费劲点,但一天花在吃饭上的时间也就两小时,跟那些习惯叫外卖或有钱请保姆的同龄人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差不多。
但这天他头昏,脑袋一点都不灵。难道是身体开启了保卫反应吗?这种头晕是因为这几天饮食不合理吗?也就坚持了四天时间而已,自己的身体有这么不堪一击吗?况且周六周日他因图书馆闭馆太早待在家里,都是吃了早餐的。周六用鸡蛋洗头,算是休息了半天,中午去了姐姐家,蹭了一顿饭,外加吃了一个苹果两个杏。
“”昨天,确实忙了一天,主要没喝水。今天头晕可能和昨天水没喝够有关。”小明自言自语地解释说。小明固执地认为,现代人的病都是吃出来的,他绝对不会饿出病来,顶多头发白得快点,面容憔悴点。但小明在乎的是生活的长度而不是密度,生命越长,拥有的时间越多,这个是绝对的数量优势。因此,他对自己的父亲没活过天年痛心疾首,他父亲身体素质好活到九十岁是没问题的,可由于他没有顾及父亲的感受,导致父亲意外去世,这是他内心的痛。他只能靠想象来生活。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但他假设他父亲还活着,经常若无其事地唱“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听他唱歌的人都会以为他父母双全,但他心里却痛得滴血的。毕竟父亲在世和不在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况。
“苦不苦,想起红军二万五”。他目前的生活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好得多。在战争年代饿肚子是常事,而他毕竟每天都能很正式地吃上一餐饭,而且也没有那种得找饭吃的压力,毕竟北京到处是饭店,万一不行了,买吃还是很方便的。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小明确是晕得不行了,他只好先洗澡。这么热的天,每天擦一遍身子是必要的。他一个人生活,早擦晚擦都一样,只要擦了能保持毛孔畅通就行。还有,就是衣服,隔天洗也是必要的。最好是天天洗,但天天洗费时,只能定为隔天洗。
简单地洗完澡后,他发现自己清明了很多。但今天的计划是上午写作。下午从创作室直接去图书馆,因此他早晨没带水。如果继续留在创作室,有两个问题:一是电脑没电了,二是没水喝。如果去图书馆,他必须首先把电脑送回家,否则晚上回来晚进不了创作室,他的电脑充不了电。
本来他可以去洗手间充电,去向负责洗手间卫生工作的大叔那里要杯水喝。但这样的话,充电期间他必须歇着,这样想还不如回家充电,这样充电期间可以做饭吃,正好他很久没做过中午饭了。
回到家里,他开始充电。然后发现隔壁大姐的母亲一人在家,阿姨七十来岁,刚做完手术行动不怎么方便,虽然能走,但下三级台阶要半个钟头。阿姨手里拿着卫生纸要上厕所的样子。他走过去问候,看阿姨要不要帮忙。阿姨说不用他扶,她走慢点能行。于是他看着阿姨走完了所有的楼梯——从三层走到了一层才开始去做饭,其实这一看差不多过去了两个小时。
他去水池洗锅,却发现停水了。刚才洗手时水还很冲的,这会却停水了。这时二楼邻居探出头来说,他刚看到街道上到处是水,可能水管破裂了正在维修呢。既然充满电要两个多小时,这饭还是很有必要做的,好在车前草叶子已经在创作室那边洗过两遍了,用淘米水泡泡再用清水冲冲就行。幸运地是刚才他存了三壶水,洗米洗菜没问题,手在向阿姨问好前已经洗过了。做饭的决心已定,就开始忙开了。只是吃完饭一看,已经15:16分了,这下去图书馆看书显然不合适,路上的花去50分钟,还要花掉4元地铁费,卖馒头够吃两天了。
于是他还是决定去创作室,创作室很安静,但他觉得太安静了,要命的是没电,他想说不定天黑了也能打字呢。当他赶到创作室打开电脑时,电脑显示的时间是16:42分。因为在路口碰到几个问路的游客,还发现罗叔叔喝了酒。他对罗叔叔很亲,罗叔叔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小儿子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小儿子硕士,小儿子的妻子是博士。看到罗叔叔,他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其实,他父亲比罗叔叔还精神些。他想劝阻罗叔叔喝酒,因为这很容易出事。他认为父亲肯定喝了酒,要不也不至于从房顶掉下来。他忽略了父亲的感受,所以父亲没活过天年。小明想,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叔叔的儿子,当父亲健在时也会和自己一样,不懂得如何走进父亲的内心。我们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出人头地是很难的,虽然花掉了巨额的学费,但挣得并不比同村那些没上学的多,而父母送子女上学是很辛苦的,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子女走进城市后,面对出身知识分子世家的同行,压力山大,只能拼命赶路,很容易忽略父母的感受。“我就是在这一点上过早地失去了父亲。”小明在心里对自己说。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文化程度低并不意味着赚的少,文化程度高也不意味着赚的多。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高知,由于先天不足,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太多,生活技能差,动手能力差,不善于交流,往往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尽管接受了大学或更层次的教育,他们赚的不一定多。罗叔叔的小儿子在北京教大学,赚的并不比一个保洁主管多,一个保洁主管通常每月能赚6000多。但房子车子是迟早得买的,所以在北京工作的高知一般都很低调,只知道努力工作。特别是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他们愿意花百倍的辛苦去赚钱,也就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和父母的沟通。父母因此心里很苦,一方面他们送孩子上学吃了很多苦,而自己念书多的孩子不仅不比村里的某某赚得多,而且活得更辛苦。某某读书不多,却娶了几次老婆,听说还有数不清的情妇,而自己的高学历儿子,却对象都没找。罗叔叔的儿子还算成功,不仅娶了媳妇,而且还生了儿子,罗叔叔的老婆就是来北京带孙子的。罗婶带孩子,罗叔在家没事,又闲不住,就来圆明园做保洁。小明前几年也在圆明园做保洁,和罗叔同事了一年。
在工作中,小明发现罗叔的性格和自己的父亲很像,因此,他对罗叔很关注。他希望罗叔能活到他小儿子在北京还清了房贷,有能力定期带全家去旅游。这时候,也就是罗叔真正享福的时候。这时的儿子,没有了生存压力,才会懂得孝顺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活不到这个时候,儿子就会终身痛苦。小明自己就是这样。
小明没见过罗叔的儿子,但希望他比自己幸运。因此,他很希望罗叔长寿,比如,罗叔命中注定可以活到90岁,他希望罗叔能活到110多岁。总之,活过天年很多。自己的父亲少活了20年,他希望罗叔能比天年多活20年。这样一来,小明心里会好受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他反复对罗叔强调不能喝酒,他喝酒容易出事,说不定摔一跤就起不来了。本来,圆明园做保洁是不伤身体的,空气这么好,工作也不是很累。但喝酒有说不定了。
小明是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这注定他会活得很累。小明去做保洁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做保洁的和他父亲一样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而且一般都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他希望这些父母不要太把大学生孩子当回事。这年头读书没用。而且读书不是为了找工作,读书多和赚钱多没必然联系。他现在住在保洁大姐中间,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前几年听说一个父亲因儿子博士毕业回家教小学而喝农药自杀了,老人家认为儿子博士毕业就得做大官,回家教小学太没面子了。他希望父母能从他身上受到启发,不要对孩子期望过高。小明也幻想着出人头地,让做保洁旳大姐大哥知道上大学虽然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却还是多少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