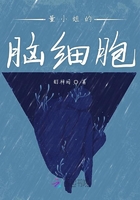胤禵将那玉佩妥帖收好,目光捎带瞥了一眼鱼儿:“好在这东西未有损伤,它若碎了,你十条命也不够抵。”
鱼儿低垂眉眼道:“是是,奴婢粗苯,奴婢......”
“多谢你。”胤禵这一生说得极轻,可听在鱼儿耳畔却如坠千斤。
多谢?他是在谢自己?
她抬首,满目惊异与胤禵眸色对上。
胤禵有些不自然的别过脸去,语气冷了些:“你捡了那玉要是想占为己有,我哪里还能在庭院里瞧见你?我一时大意险些丢了它,你替我捡着,我是该谢你。”
鱼儿本对他有一肚子怨气,听了他这一番话,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搔了搔后脑勺,摆手道:“嗨,多大点儿事儿啊。奴婢本就是伺候主子的,这东西名贵,我哪儿敢据为己有?”
胤禵点了点头径直去了,徒留鱼儿满心好奇留在原地。
他这样的身份,何以会对一块玉佩上心至此?
瞧他方才那奋不顾身的模样,倒像是舍了命去也必保住此物。
许是于他而言极为重要之人相赠的吧?
鱼儿一璧想着,一璧继续抡起扫帚来继续轻扫着庭院。
到了夜里,忙碌了一日的鱼儿回了居所。佩儿负责清扫南殿,差事要比鱼儿轻松些许,待鱼儿回来时,见桌上已经摆了两碟小菜和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面满头。佩儿点了灯正在一旁坐着,手持针线缝绣着什么。
她听了启门的动静停下手中活计,目光迎着鱼儿望去,浅浅一笑:“你回来了。我怕你去晚了旁人吃了你那份,便给你将饭菜打回来了。”
鱼儿谢了她两句,坐在桌前便狼吞虎咽起来。
一边吃着,口中还一边囫囵道:“我今儿洒扫时遇见了娴格格房中的月影,碰巧她去佛堂贡香,我顺便求她帮咱们求了张辟邪的符。”说话间取出贴身收着的一张黄符丢给佩儿:“你压在枕头底下,求个心安。”
佩儿谢了一声,将黄符随意扔在了榻上便不再说话。
入夜时,佩儿仍如前两日一般睡下的极早,鱼儿躺在榻上望着窗外繁星,不知觉来了困意,很快合了眼。
约莫睡了一个时辰,佩儿的一声尖叫将鱼儿惊醒。
她似预料到了这事一般,徐徐起身看一眼佩儿,平静问道:“怎么了?”
佩儿指着墙角地上的凭空现出的一滩水与一袭红衣,声音打着颤:“鱼儿,她......她又来了!”
奇怪的是,此番再见这怪事,鱼儿倒不怕了。
她下榻点了烛,行到那红衣旁将它捡起,在手中掂了掂。
佩儿吓得直唤:“那是脏东西,你小心些......”
“脏东西?”鱼儿回首看一眼佩儿,露出一记不明深浅的笑:“你都不怕,我为何要怕?”
“你......你这话何意?”
鱼儿轻嗤一声,上前两步将那红衣掷在佩儿的榻上:“你自己个儿闻闻。”
佩儿抓起红衣嗅了嗅,很快明白了。
是梨花粉的香气,幽微淡雅,却香味悠长。
她将红衣紧紧攥在手中,面上慌张神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淡定镇静:“你拿梨花粉给我是要试我?你何事知晓这事儿是我做下的?”
鱼儿苦笑摇头:“我是真心予你。我本只是对前日闹鬼一事存了个疑影,直到今日。”她转身回了榻上,由榻沿边儿上的缝隙内取出了一褐色的布袋。布袋启开,里头装着的却是凉了的饭菜。而那菜式,正是今日晚膳佩儿为她带回来的。
“这里头搁着分量极轻的迷药,旁人可能不会察觉,可我从前捕鱼时,毓泰也教过我将迷药撒入鱼饵里,令河鱼在缸内不做挣扎,免得还未入市集就在缸里挣扎用尽了气力,到了市集上一动不动瞧着奄奄一息卖不上价。所以我对那迷药的味道极其敏感,我进第一口时,已然发觉不对劲。”
她说着将那盛满了饭菜的布袋仍在桌案上,蹙眉道:“我不知你为何要对我下药,于是背对着你用膳时将它们偷偷藏在了随身携带的囊袋中。只待你早早儿睡下,我也躺下装作中了你的迷药睡去。也正因此,才能瞧见你偷摸从枕下取出了那身红衣扔在了地上,又将茶壶里的清水泼了一地。”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装神弄鬼吓唬我?”鱼儿高声发问,佩儿却低垂下头,一句不答。
鱼儿气闷不已,愤愤道:“你不愿说我不迫你,只是你携带迷药入府,安得是何心?这事儿我必得告诉崔嬷嬷,将你交给她发落。”
撂下这一句话,鱼儿急匆匆向门外行去。
佩儿见状急了,忙跳下榻,连鞋也顾不上穿,打着赤脚拦在了鱼儿身前:“不要鱼儿!我求你别告诉崔嬷嬷!我没有想过害你,我......”
“那你为何要装神弄鬼?”
“我......我只是想要你与我一起将这府邸里有女鬼的事儿闹大了去,如此才能替我长姐报仇......”
报仇?
鱼儿愣住,却见佩儿已然泪流满面。
她最是见不得人哭,心下不忍,反倒拍着佩儿的后背劝慰道:“你慢慢儿说,究竟是何事?”
佩儿抹一把眼泪,哽咽道:“从前我说入府是为了替我娘医病是诓你来着。我爹娘离世的早,自幼我便与长姐相依为命。原先在京城里一同在布纺做工,后来雍亲王府招下人,长姐说每月可以多赚些银子也能让我少吃些苦,就去了。本一切都顺顺当当,长姐还入了南殿的宋文姜宋格格房里当婢女,差事轻松月例银子也多,还说不日便要接我入府去。可这一切,在上月雍亲王迎娶了年晞尧后就都变了!”
佩儿不住抽泣着,身子不停颤抖:“年晞尧入府就是侧福晋,掌南偏殿事。一日年晞尧往宋格格房中闲话,长姐伺候时不当心,不甚将茶水泼在了年晞尧身上。她偏说她那是贵价料子,要长姐赔。可长姐哪里赔得起?年晞尧一怒之下就杖责了长姐三十大棍。后来......后来长姐就上吊自戕了。”
佩儿死死咬住嘴唇,连连摇头哭道:“长姐与我相依为命,我素知她性子,定不会因此事自戕了去!定不会如此!必是年晞尧暗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