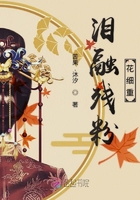清晨时分,国子监负责教务事宜的教士在监内击响了鸣钟,冉若华也正是在这厚重的钟声中踏进了地宇堂内班的教堂。
昨日和祭酒大人交谈一番,大人知她在宫内兼画师也并未多言,只是简单叮嘱了些传授之道。
作为黎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课业还是以诗书为主,绘画和武学为辅,因此祭酒给她安排的课也不多,只需负责地宇堂和玄清堂内外班,每三天一次课。
冉若华年纪与这国子监监生相仿,且未做过人师,难免会担心自己气势上压不住这些小子们,昨日从国师大人车上下来倒是特意去书坊买了几本祭酒大人所著的教经,临时抱佛脚,但貌似用处不大。
不过想来自己好歹在现代也是活了二十好几的人,对付这些个十几岁的少年应不成问题。
可这刚一踏进教室,那身穿教袍的瘦小之人脚步便停了下来,大而明亮的眸子疑糊的看了一下屋子里熙熙攘攘的监生们,又退回去一步看眼堂外的牌匾,是地宇堂内班,没有走错呀。
她分明记得名册上写这内班是二十人,可眼下这屋子里已足足坐了五十有余,这人都是哪里冒出来的?
尤其是青白监服中那向自己挥手的黄衣之人,不正是几日未见的六皇子卫长风吗?
他不是应该在天轩堂,怎么跑地宇堂来了。
“初来国子监,今日与在坐的监生们也是初识,在下花拾,日后负责传授你们绘画之技。”冉若华在教桌前说着,目光不断的打量着下面的监生们,倒也没有人在嬉笑打闹,反倒都一本正经的看着自己,顿时便放宽了心,没想到这国子监的学生倒是沉稳得紧。
“我这手上拿了地宇堂内班的名录,我粗粗一看竟是比在坐的各位少了许多,想必是有其他班的监生对我这课感兴趣的紧,也不知此时其他班授课的先生知不知此事。”冉若华翻着手里的名录,眼睛瞥到下面有一些监生听到自己的话开始局促不安了。
“既然你们如此喜欢,不如我就来挑一个人问问吧。”漂亮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后,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少年说道,“就你吧,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这少年身材高大,目光有神,皮肤泛黑,似乎经常在外日晒,不像是苦读的书生模样,倒是让她来了兴趣。
“燕离归,黄陨堂内班武贡贡生。”那监生见先生点到了自己,便大方的报上名来。
原来是凭武学选举进来的贡生,不过为何这下面人听到他的名字倒是有些骚动,难不成有什么不同。
“你既是黄陨堂监生,今日为何到这地宇堂来了?”感觉这监生也不像是个爱画之人。
“昨日是听人说监里来了个漂亮先生,所以今早便来看看。”少年此话说得甚是随意,竟引来了班内其它监生的一致附和,顿时让冉若华红了脸。
虽知自己长了张妖娆好看的脸,但就这么被人当众夸出来,还怪不好意思的,有失为师的体统。
“是吗?”台上之人面上一笑,“那你们倒是说说今日亲眼见到先生我,觉得如何?”
“花先生样貌自是极好。”
“就是仙人也不及先生的风姿。”
“…”
一时之间,赞美恭维之词如春笋般接连在屋内回荡。
只听“嘭”的一声,那美貌先生竟将桌上的戒尺狠狠的摔打在桌案之上,声音之大吓得众人屏息而望,不知先生这是要做什么。
“你们皆说美貌,可这样貌又有何用,先生我不还是要站在这里给你们教书讨生活”美目一瞪又说道,“既然你们都是来看我而非学画的,那今日之课,便临摹先生我,限你们一个时辰内作完。”
这美貌先生莫不是之前日子过得太苦,被大伙的玩笑话气疯了吧,竟让临摹他,国子监的监生们平日里可没什么时间练习作画,等一下先生看到他们的画作,可别吓晕过去。
其实冉若华只是佯装生气,一是为树立威信,二也是想探探这帮监生们的底子。
可一个时辰后,当冉若华看到手里这些画时,她顿时理解了为何祭酒大人一定要邀自己来国子监授课,想她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竟被化成了各种牛鬼蛇神的样子。
当初被自己嘲笑画技的卫长风,竟然画的还算好的。
突然,一只大手从一旁伸了过来,把那些画从她手里抽了过去,冉若华想抢回来,转头一看,竟是昨日刚和自己闹不愉快的国师大人,可他怎么会来地宇堂了。
“这画上为何人?”清冷的声音响彻在屋内,监生们大气不敢出,生怕惊了这位大人。
一向只管教天轩堂内班监生的类尘先生今日怎会到这地宇堂来,真是难得一见。
“是,花先生。”那燕离归倒是毫无惧意,直接回了他。
“噢?”淡薄的眸子打量了下身侧瘦小的男人,点头道,“倒是有几分相似。”
那纸上画得像个猪头,哪里和本小姐像了,冉若华生气的抽回了那些画,客气询问,“类尘先生来这地宇堂,所为何事呀?”
“天轩堂有个监生缺了早课,我来寻他。”男人回答道。
天轩堂敢翘课的除了六皇子还能有谁,在后门准备逃走的明黄身影立刻便被教务抓住,带到类尘先生面前。
“先生,我知错了,日后定不会再犯。”刚刚在堂内还吵吵嚷嚷的六皇子在国师大人面前立刻认怂,求饶起来,毕竟这事要再被捅到父皇那去,自己今后就不用想着出宫了。
“带下去吧。”不理会六皇子的求饶,类尘先生反倒将目光看向了屋内众人,所出之言让人背后生寒,“众监生需将今日所作之画贴在床头,日日欣赏。”
“啊!”堂内顿时传来了学生们的哀嚎,这要是真的花先生也还好,可让他们把自己鬼画符似的画贴在床头,类尘先生此举,未免也太狠了些吧。
“类尘先生,此举恐影响监生们休息,不太好吧?”看不下去的冉若华终是出声给监生们求情。
无论画得怎样也终归是她冉若华的画像,被人天天摆在床头供奉着,也太晦气了。
“无妨,不过你需随我去祭酒大人那里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