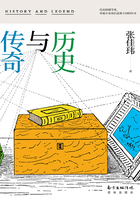手指尾根处传来一股尖锐清晰的疼痛,池北辙黑沉沉的双眸猛地一紧,作为曾经毕业于有名军医大学的人,他有着对威胁感知极强的敏锐,一旦遭到攻击,就会迅速做出反击,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本能,但这种本能在这个他深爱了10年的女人身上,一点都发挥不出来。
他本可以抬手捏住她的下巴,逼她松口,却相反的把大半截的手指送入她的贝齿下,任由她更加用力地咬,偏头看着她泪光和火焰丛生的眼眸,他喉咙发紧,心口剧痛,声音却波澜不惊,没有丝毫妥协退让,“音音,我不介意再被你多伤几次,哪怕我遍体鳞伤,今天你也妄想再逃开我。”
听着男人嘶哑低沉的声线,白倾念分不清胸腔里堆叠而起的究竟是疼痛还是仇恨,只知道伤他便能把这些复杂的情绪发泄出来,她用尽了力气咬下去,听到了骨骼的脆响,口腔里充斥着鲜血的腥甜气味。
身为医生的她对血没有抵触,但当她觉察到他手指上的鲜血,顺着她的喉咙滑到胃里时,她的胃里一片翻江倒海,一股恶心呕吐感涌上来,猛地抬手推开他的手指,弯下腰干呕起来。
池北辙一惊,慌忙捞起她的腰,“音音,你怎么了?”
“呵!”白倾念突然学着顾景年平日里的语气,嗤笑一声。
每次她听到顾景年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心口堵得慌,她不知道眼前这个满脸慌乱的男人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她低头看着他搭在她腰腹上的双手。
景观灯从四面照过来,她清楚地看到那些鲜血顺着他修长的手指淌下来,浸入她的白色裙子里,开出妖娆血红的花,她扯着唇角说:“真恶心。”
恶心?他竟然让她恶心了?这还是那个曾经说着爱自己,分手时哭得歇斯底里的女人吗?池北辙的胸腔里泛起一股浓烈的酸楚,她变了。
他不管流血的手指,一双血红的眼睛紧紧盯着她脸上的表情,哑着声音问:“我们分开不过五年,你已经不再爱我了吗?”
白倾念不想一再重复“你认错人了”,眼看着花墙外陈柏陌因为找不到她而离开,她慢慢地站起身,挺直脊背,咽下满嘴的鲜血,冷静下来后,她闭上眼睛考虑着脱身的办法。
池北辙盯着她苍白,却仍旧从容清冷的眉眼,眸中的光明明灭灭,不仅不松开手,反而抱得更紧。
月华清冷,花开无声,池北辙放轻了声音,在一片寂静里看着这张他日思夜想的脸,一时恍惚起来。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白倾念猛地睁开眼睛,再次透过蔷薇花墙看到前方走来的一男一女,那男的身形颀长挺拔,身侧的女人婀娜多姿,分明就是顾景年和他的女伴。
“顾少。”白倾念看到女人抱住顾景年的手臂,柔弱娇小的身子贴上去,撒娇一样央求着顾景年,“我们去那边的蔷薇花前拍个照好不好?”
白倾念的心口堵得慌,闭着眼睛不想再看下去,过了一会却还是忍不住看向顾景年。
顾景年轻轻推开女人的身体,伸出大手一搂女人曼妙纤细的腰肢,缓缓俯下身,抬手揉着女人的脸,声音暧昧,“比起花来,我更喜欢看你。”
白倾念用力咬紧唇,满是腥甜的喉咙竟有些发苦,也不知道再次吞下的是自己的血,还是刚刚那男人的血。
池北辙看到白倾念的反应后,心中痛怒交加,声音却充满了浓烈的讽刺意味,“这就是你的未婚夫,你将来要嫁的男人。”
他的目光往顾景年身后一扫,果真看到杜华跟在两人身后,心下明白顾景年又在逢场作戏,也不揭穿,故意让白倾念误会。
白倾念一怔,这男人怎么这样说?他不知道她是顾景年的妻子吗?转念一想,她今晚并没有以顾太太的身份和顾景年一起来,他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
她想到顾景年在T市只手遮天的本事,手指紧握,逼得自己用一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姿态问池北辙,“你知道我是顾景年的什么人吗?”
闻言,池北辙高大的身形陡然僵住。
白倾念觉察到刚刚手指差点被咬断时都没有任何动容的男人,此刻那放在她腰间的手指却轻轻颤抖起来。
她以为池北辙是忌惮顾景年,胸腔里竟然有些沸腾,再也没有这一刻觉得做顾太太是那么骄傲的事,不用再伪装,她抬着下巴说:“我是顾景年的……”
“你不用一再提醒我。”她的话被池北辙打断。
他又恢复成那种铜墙铁壁一样的硬冷来,但白倾念分明听出他语气里的苦涩之意,“我知道,你们从小就有婚约,你早晚要嫁给他,但那又如何?五年前你不能和我在一起,并不要代表五年后的今天你不属于我。”
白倾念眉头轻蹙,她记不起以前的事情,听不懂这男人在说什么,她从一开始就觉得这男人有神经病,病得还不轻。
有了开口的机会,她再次想喊顾景年的名字,但却发现顾景年早已揽着女人的腰转过身,慢慢地远走。
白倾念睁大了眼睛,看着顾景年的身影越来越远,在漆黑浩瀚的苍穹下变得越来越渺小,她心底渐渐滋生出一股绝望来,眼前浮现出那个冰天雪地的伦敦街头,俯身把她抱起,满眼柔软深情的男人来。
而那个曾经救她一命,给她一个安身之所,因为不要他的钱而和她冷战的男人,此刻却弃她于不顾,搂着另外一个女人离开。
白倾念突然很想哭,然而一直无坚不摧的她,连脆弱和无助都成了奢望,她的眼睛又酸又疼,却干涩得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想起那年她倒在他的脚边,意识模糊之际,死死拽着他的裤脚,让他救她。
一瞬间的绝望让她突然变得激狂起来,用尽全部的力气挣脱,歇斯底里地吼,“禽兽!你放开我!放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