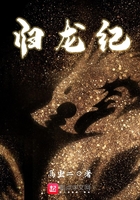初入玄妙境,时间持续很久,一直维持到蜕变结束。半寐半醒间,他体内的精气,聚集到眼目处,呈现出一片浩白,过了好一阵子,方才恢复清明。
“这种感觉好奇怪啊?”平白的空气里,赫然有涟漪状的水纹,竟以自己为中心,慢慢荡漾而开。
惊愕之余,却不知透视本源,而产生的明悟。俗语有言,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大抵就是这个境界。
但凡初开天眼者,皆以大周天之术,炼气温养识海。久而久之,能见他人周身气息,观其表能知其里,气机交感之间,也能望其色,而断其病。
闻言诸天仙佛,能知过去未来事,他们一眼望穿万年,透视万物本源,无障眼遮目。
五境中的凡人,他们肉眼凡胎,只能看眼前所见,目光极其浅薄,终其原因,皆是被妄想的执念所蒙尘。
凡人若想要和诸天仙佛一样透视万物本源而无障眼蒙尘,那么只有通过修炼得道来脱离凡胎。
因为凡人脱离凡躯,有先天一气入体,可助其初开天眼。方时微观内视,分辨阴阳鬼魅,不受肉眼所困。
尽管不如诸天仙佛,但随着修炼不断精进,其神通自会圆满起来。
故天地间,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诚如佛道所言,凡有九窍者,皆可成仙,凡有慧根者,皆可成佛。
不知过了多久,他不禁恍然一愣。
“哎呀,我怎么把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不知现在赶往府衙,还能否来的及?”
“哒哒,哒哒。”又是一阵马蹄声。
他在桥上远望,而那群骑马之人,不正是搀扶自己的人吗?
因为天眼初开者,能视百丈远的蚊蚁,那远处的骑马之人,自然能看的真真切切。
叶景天感慨万千道:“初入定,玄妙境,南柯黄粱皆可信,世间真有神仙在,古人诚不欺我也!”
刚才在冥想之中,时间过的漫长,如同经历数个须臾。但周边的人群依旧,从未有过异样变化,由此可见,时间不过弹指一瞬。
时间不等人,眼下不作多想,赶紧起过身子,拂去衣上的灰尘,动身赶路。
在炎炎夏日里,他行步如生风,不时已到府衙面前。
朝廷的衙门,无论大小,皆有三扇大门,中间最为高大的称为“仪门”。
朝廷独尊儒术后,依儒家伦理治国,礼制自然马虎不得。
平日里“礼门”一般不开,只有在重大庆典,或是迎接上宾方能开启。
“仪门”的两侧,则各有一扇小门。
东为“生门”,西为“死门”。
眼下三门全开,看来崇明寺的事,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再次放眼望去,府衙正门前,人群拥挤不堪,把道路都围的水泄不通。
只见三两成群,各自议论着,纷纷攘攘,好不热闹非凡,同赶庙会集市似的。
叶景天心里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为弄清楚缘由,他混在人群之中,努力挤到中间,才能抵近一听。
“你们知道吗?昨夜之事,明显是府君无道,天灾显警啊。”
“可不是吗?就不知这李笑之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听说从清晨起,开始大肆捕人,稍有嫌疑者,便当场格拿,也不问缘由是何?”
“哎,真是苦了我家官人啊。”一名妙龄美妇接过话后,提衣袖掩面哭声连连道:“如果是张府君在,岂会发生这样谎妙事情,苍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
“呜......呜......”
“就是呀!早年张府君司政,为人公正不阿,决狱讼鲜有偏袒,就连劝农桑、宣教化、掌礼仪、管理赋税,无一不是亲身躬行,哪里会像如今这样。”
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声,徒增了几分悲伤。
“唉!自从南荣世家主政青州,怎么就让李笑之当了府君,当真是苍天无道啊!”
“此獠为人无能,萧规曹随,司政中稍有纰漏,便把脏水往张府君身上泼,言明一切为张府君定下。他初来丽泽府司政,不敢朝政夕改坏了规矩,委实可恶至极。”
人群之中,各自附和议论,但提及李笑之,却无不恨的牙痒痒,可对于前任的张岸清,却又无不敬仰怀念。
两者之间的操守,随即高判立下。
“嘘,你们可不要再乱嚼舌头了,小心被人听见,因言获罪!”
一名身着员外服的男子,挺着圆鼓鼓的肚子,探过头来说道:“你们可知李笑之上任以来,因文字入狱的书生有多少吗?告诉你们可别被吓着啊,上下足有千百人之多。”
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无不把议论声放轻,生怕被别人听见,误了自己性命。
“不过呢,大家也不要过于害怕,我族亲在府内述职,从他那里得到消息,据说最近有大人物从中州过来。”
“照我看啊,这李笑之马上就要变成李哭之了。”
青州百姓对李笑之不满,自是由来已久,现在听他这么一说,皆被逗的哄堂大笑。
叶景天听声不语,鉴别三言两语,已然摸清眼前的境遇,不禁暗自生凉起来。
“当官务者,本应持大体,举手投足间,皆为民生国计,若不爱民如子,只怕百姓要归于罪朝廷了。”
心念至此,突然转而一想,否定先前的概论。
“天理昭昭,因果循环!若朝廷用人不识,也难怪会被人厌恶。”
“唉,我该用什么开脱之词呢?当真是苦恼甚烦呐!”
蓦然长叹一声,不敢再有耽搁,径直穿过人群,停在丽泽府门前。
眼前雄壮府衙,倒是平生初见,不由上下打量起来,先饱个眼福再说吧!也算是不枉前来省城了。
省城府衙,前府后邸,坐北朝南,正门高数丈,门上呈现朱红色,有黄铜大钉遍布,高立于两层三级的台阶上。
门前地势开阔,有一排侍卫持刀而立,其身威风凛凛,目光似射寒星,与之对视一眼,都能感到冰冷刺骨。
那是一股杀气,无形之中溢于体外,可不知为何?他却对此甚为敏感。
也就在此时,倏然响起一声惊喝。
“大胆,何人敢在此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