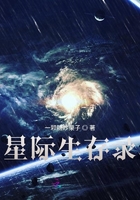“李振海,你在哪?”
他耳边传出清晰且清脆的声音,他抬起头,看着悬浮在空中的泪花,回答道:
“我在这,我在这。”
些许撕哑的震动汇合在他的回答中,声音的主人很快就从中感到了不对劲。
“你怎么了?”
“卡诺死了,就在刚刚,就在现在。”
她突然有些愕然,但随即用她也无法察觉到的颤抖的声音去问。
“发生了什么?卡诺它不是在月球上,怎么可能还有他们的存在!”
她很快被切断了通讯,李振海很容易就明白接下来的一系列和他相关联事件的发生。
来自于人类最根本的敌人:贝尔多利,它们刚刚杀死了她。
半个小时后,在其他人注视下,李振海缓步走进了一间被临时改造成的监控室,那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洁白,那是被灯光照耀下才产生的,一旦离开光,那么就与这之外的世界一样漆黑。
“你是怎么第一个知道卡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你又是如何能够确定它死了。”
洪司抓着牵引绳来到他的面前,手上拿着无壳步枪,用他不变的声音和他那一如既往的神情注视着他,好像能够透过他的面容看透他灵魂的目光,在李振海身上看不见任何不寻常的姿态,但是洪司能够感觉的李振海身上一种十分特殊的氛围,仿佛他站在另一种界限中,而自己只是在观望着,不……在仰望着。
独自两人的空间中,其实只有一个人。
李振海没有很快就回答问他的问题,而是注视着灯光,深深地呼出了口气。
然后把目光重新望向洪司说道:“是我杀的,我是拉美尔人。”
洪司突然觉得自己的头脑有些发热,瞬间回想起在于拉美尔直接的战争中经历的一切,不由得抓紧了手掌。
“你知道这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吗?”
洪司看上去有些恼怒,但依然保持着他一如既往的冰冷,李振海知道那些刻在他脸上的皱纹里蕴含着压抑的绝望,那是远去的战争遗留下的产物,并且这场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李振海用一种就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语气说着,平缓的语气中夹杂着难以忽略的沧桑,但又和新生的光辉交织一处。
“希望您不要阻拦我,因为我们拉美尔人是绝对站在人类的那一面的,我们一直以来面对的都是一样的。”
“什么是一样的?”洪司反问到。
“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来讲诉过去的一切,或许您永远都不会相信,但是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刻在你的灵魂深处。当然,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依然不能说。”
“看来你是想交代遗言了,可是我为什么要听呢?”
“没关系,我们已经等到了,你在临行前看见那漫步在整个世界的光辉,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抉择,其实之前我也不明白是否成功,直到不久前,卡诺告诉我仅属于我的选择。”
“什么?”他感觉到有些东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卡诺,怎么可能会与你交流!你们拉美尔人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癫狂的群体,也是给她带来难以描述的痛苦的存在……”
“但也是我们创造出她的,她挣脱了一切,但是她并没有挣脱来自于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道德。那些东西使得她选择和我们为敌,同时也使得她在她生命历程的最后选择对整个人类都是正确的选择。”
“你们可不算是人!一群为了自己的欲望肆意妄为的人!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一群向人类举起屠刀的畜生!”
洪司暴怒起来,他狠狠地向李振海挥拳,但是在无重力的环境下只不过使得挨中拳头的李振海撞向舱室壁上。
“那我们为什么会输呢?我们凭什么会输在接近终点的战争呢?”
李振海在半空中缓缓漂移着,平淡的提出他早已知晓答案的疑问。
“我们拉美尔,在当时占据了整个世界最为精华的地区,拥有着近千万无人军队,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战略性武器和科研技术都在我们手上,死寂的非洲是我们的工业区,荒芜的亚洲和美洲也不过只是我们投掷非低效性战略武器就可以轻易解决的实验场,广阔的七大洋只有印度洋还存在着些许不属于我们的舰船,然后我们大部分都输了,一部分投降了,更多的都死在了卡诺手中。”
“这些是奇迹吗?我们都知道不是,人从不拥有奇迹,只是那些东西拥有着无法描述的伟大而选择用奇迹去表述它们。”
洪司那激动的神情很快就被他自己平复起来,思考的冲动碾压了短暂精神上的冲击,狭小的空间里再次陷入了沉寂。
在经历了许多的人类,现在多出了许多用来思考的时间,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喧闹,中期的怒吼,到后期的沉寂,仿佛成长了一些,老了一些。
“李振海,你知道多少?”
洪司没有去问他真正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对拉美尔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他们自己才真正明白了意义。
“我知道许多,因为我曾经有幸和极光先生相处一段时间。那是一段美好与残酷交织的岁月,即便那段时间现在只有我还记得了,当然,我并不是什么都知晓,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作为遗言已经足够了。”
洪司用极细微的声音念道“遗言……”
在无尽的宇宙中,一间小舱室中,关于部分远去的岁月被其他人聆听着。
“你知道的,我们拉美尔科技集团从诞生到自我消亡不到三十年,然而对我来讲,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也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我知道这种说法很难被接受,毕竟我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在许许多多方面表现出来的都是充满着罪恶与残酷。
这种残酷不仅仅在于我们所做的那些人神公愤的事情,更多的在于我们对人类这个概念上新的定义,并且这种定义已经潜藏在现在的世界中。
你也是实践着这种定义的人,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在无形之中践行着这种定义。”
洪司很快就理解了他所说的那种定义是指什么,那是刻在时代中的刻度,即便现在也没有人真正意义上去公开解释其意义,或者说——不敢。
“作为人类的第一准则: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其负责,且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人类有意义。
这段话每个人都知道,是当时的华源和洁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但是你也知道,他是拉美尔人,洁也是。
当我回顾历史时,我发觉还有许多东西被抛弃了,被粉碎了,但是对许多人来讲,那些只言片语的东西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我们拉美尔人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只要是个人都觉得是错误的道路去走,然后死去。
然后你我都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什么,血非灾难,太平洋涡流群,亚欧间隙,环流死亡带,高原错位,电频实验,无人净化区,海岸线荒漠,南极核爆区。使用着现在看了也无比先进的科技进行着肆意妄为的屠杀与破坏,肆无忌惮的宣泄着无人记得的痛苦和绝望。
即便现在的全部人口加起来也不到当时的一半,活着并且记得那个时代的就更少了,我曾经在空闲的时候去那些老人聚集的地方去看,我看见他们许多人的目光中依然残留着恐惧和痛苦还有一种时代的积累。你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即便在那时候你和我都是一样只能够跟随着时代的冲击而随波逐流,然后携带着一份淡漠的回忆活着。
从某种角度上讲,我比你要幸运很多,因为我的一生走过了许多地方,知道更多的东西,即便和我有关的已经只有你们了,人从古至今都是依赖着其他人的存在才能活着的生命,而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些人选择独自一人承受着他自认为要承受的责任,然后死去。
我遇见许多这样的人,然而大部分都是散落在时间各地的拉美尔人,真正的拉美尔人活在崩溃后的世界中,而在之前的残酷战争中死去的,在历史的解说下,更像是承载着残缺的意志的墓碑。如果你用现在的人去和那个时代的人去比较,你会发现除了一些铸就现在人类社会整体意识有关的人,就像两种披着相似身躯的生命一样,但两者根本无法比较。而着之间的差距反而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创作出来的,人类最后的自我战争。
其实那次的战争中没有任何人真正意义上输了,所有的追求都得到了实现,拉美尔追求的是自由的,能够被人类掌握的科技力量和在这个世界迸发而出来的人类意志;他们却用最极端的民族意志,国家意志,种族意志组成身躯,挑起战争。
新国际联合共同体最初就是那种落后的思想和意志组成的;但是在使用了远远落后于拉美尔的武器和叛变的卡诺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却转变成了最本质的拉美尔所期望一样——绝对的人类意志共同体。”
李振海停顿了一下,有些释然的吐了口气,而洪司看着这一切。
“人类本就是不断进步的生命,并且在挑起战争后的荒漠中更加强大。
这是我们人类伟大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一群奉献出所有的人缔造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反而在我的脑海中根植,蔓延。
但是我依然选择了复仇,向着你们。那些积淀下来的回忆在带给我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时,也给予我重若泰山的痛苦,最后压倒一切的稻草则是极光叔叔的死亡。”在李振海做到这里时,他那漠然的面容有些黯淡,洪司很清楚那是因为才会诞生出的表情。在很久以前,在他知晓他所在的部队收到毁灭性打击时,在他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武器撕碎时,他不止一次在飞溅的碎片中看见自己的面容,和他一样。
像死亡一般。
“我无法描述他的伟大,也无法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但我能够看见他的愧疚与落魄,还有他那无比坚韧的灵魂。
说实话我不止一次幻想着人类存在灵魂这种东西,但这个名词更多是意志的另一种表述。
人类不存在灵魂,只有一些零碎的思绪驱动着身躯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在他身边时,只是个孩子,因为当我苟且活着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他的身边。
在他身边时,我第一次看见了我们人类的敌人,永远的敌人:贝尔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