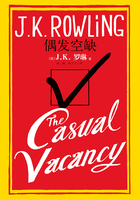“还要不要活啊?全世界的顶级帅哥,都在跟你谈恋爱,天,光是揣着这一本结婚证,我都可以吹一辈子牛。”
丁尔拉捧着结婚证由衷感叹,照片上的男人美得惊世骇俗,这他妈才叫沉鱼落雁,这他妈才叫闭月羞花,原来世界上描述如画女子的词语也可以用来描述男人,且毫不违和,美得她立刻在心里背叛了仍在无涯苦海中的裘小洛。照片上的美男子啪啪打了丁尔拉的脸,她不觉愧疚羞耻,因为所有至美事物都不应被愧对,这一对璧人,光是结婚证上两寸朴素婚照,都美得令人肃然起敬,这庄严来自灵魂深处,一点都不虚假。
“居然还比你小六岁!尤雾女士,您这是找了一小鲜肉啊?”
尤雾嬉皮笑脸,一双眼珠子黑白分明,藏在扇子似的长睫毛下,黑是对费孔城的温柔,白是对裘小洛的残酷。
“哎哟。”丁尔拉咂舌,“御姐和奶狗,这组合无敌了。”
丁尔拉把裘小洛扔到九霄云外,她忘了自己本是为裘小洛而来,替他问一问眼前这枉顾成性的残酷女人究竟何思何想。
但至美之前,不论做何思何想都会变得幼稚,丁尔拉决定愚蠢,暂时做一个重色轻友的人,她上上下下把结婚证上的美男子感慨了好几遍,终于收回理智,对尤雾供出一尊扑克牌脸:
“这位女士,你是不是欠裘小洛一个解释?”
“幼稚!”尤雾惊道,“婚姻这种事,存在即真理,不需要解释。”
“不爱了也一样。”尤雾补充道,没心没肺,十分完美。
丁尔拉思忖半秒,觉得无话,无话即认同,她郑重其事关掉录音笔,决定带回家给裘小洛的心再添一把刀子,这刀子足够让人死心。
不死就再多听几遍。
尤雾见那录音笔,朝着丁尔拉尖叫:“天啊,你简直可怕,居然偷偷录我音。”
“比我更可怕的女人就在我面前。”
尤雾努嘴,“拒绝可能不适合我的婚姻是一种勇气,可圈可点,一点都不可怕。”
“和一个认识七天的陌生男人结婚更是一种勇气,我为你鼓掌。”
丁尔拉佯装鼓掌,迅速收拾桌面起身将离:“我要回去给裘小洛扎刀,早死早超生。”
“帮我好好看着他行不行?失恋……还是会很痛苦的。”尤雾撅着嘴,说得特别真诚。
“这句话我不会录,免他听了死灰复燃。”丁尔拉快言快语,“顺道替他谢谢你菩萨心肠,还存了一点同情心给他,还好,没丧失人性。”
尤雾尖声娇笑,把丁尔拉笑得浑身骨头酥软,这女人太活色生香,不仅仅对男人。她夺包而逃,再迟下去,恐怕她就要和费孔城抢新娘了。
果不其然,录音实在太有杀伤力,把一个裘小洛杀得片甲不留,丁尔拉面不改色心不跳,逼着裘小洛听完录音,看他瞳孔里的光慢慢熄灭,一颗对尤雾尚存妄想的心,噼里啪啦跌碎殆尽。
“这招叫满灌疗法,不好意思。幻想会让你不能自拔,乖,走出来吧。”
丁尔拉不无同情,眼见裘小洛终于从茶饭不思进化到肯返回人间,虽还浑浑噩噩,但好歹有了点人气儿,见裘小洛这一副凄凄惨惨戚戚的模样儿,心里便又对尤雾的薄情憎恨了几分。
可话说回来,但再怎么憎恨,也不敌失恋之人身上温吞吞的气场,丁尔拉连守了裘小洛三天,守得她快要精分。恰逢这些天案子特别多,白天一对对小夫妻老夫妻,在丁尔拉面前黑脸白脸各色脸,哭脸笑脸无情脸,各色婚姻矛盾鸡毛蒜皮一字排开,调解室里,两夫妻一言不合就打架的有,跪下来磕头求复合的有,小三冲进来和原配干架的有……丁尔拉头昏脑涨,晚上下班后到裘小洛家,还得继续忍他一脸生无可恋,觉得世界简直黑暗,纵使心理素质够强够大,也顶不住好友这一脸无欲无求看破红尘。
裘小洛和尤雾纠纠缠缠十二年,这十二年,尤雾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裘小洛大人有大量,多少次都觉得无所谓,但临时悔婚又和别人闪婚这事儿,还是绝了点,裘小洛受了重创,结结实实,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尤雾已经嫁作他人妇的事实。丁尔拉虽和尤雾一把交情,这事儿她也很同情裘小洛,于是帮着在屁股后面收拾尤雾在这个家里留下的痕迹,内衣啦鞋子啦裘德洛的项圈儿啦厨房里她爱吃的辣椒酱啦……但失恋的人就差没把她当做尤雾,丁尔拉不止一次被裘小洛盯得毛骨悚然,偏偏每天陈蕊蕊微信轰炸,正愁着怎么揭竿反抗,裘小洛突然主动发话了。
“丁尔拉,你想过一周以后的事儿吗?”
“一周以后?”丁尔拉有气无力,怀里的裘德洛和主子一样一脸生无可恋,“谁他妈想一周以后,我只想现在去拳馆痛快打一场嘿嘿哈嘿。”
“我是说,一周以后尤雾的婚礼。”
“婚礼?”丁尔拉回答,“该吃吃该喝喝,一样不少,我还是伴娘,那档子事儿都陈蕊蕊帮着,我又管你又管婚礼,哪儿管得过来……”
“不是……尔拉……我是说,婚礼上有一个人会来。”
“谁啊?”丁尔拉懒洋洋地问,蓦地一个激灵,一股她几乎察觉不到的电流击中了她的心脏,她一下子明白裘小洛说的人是谁。
“确切的说,是两个人,梁清润和……”
“打住!”丁尔拉用一块红烧肉堵住了裘小洛的嘴巴,“不行,在你这里呆下去我要精神分裂,不管,裘小洛,您自求多福,我走了。”
丁尔拉拎起包打开房门,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不出意料,路上陈蕊蕊的电话追来,她不等对方发话,抢先占了头风:“不行,你这任务太艰难,裘小洛我不管了,阿弥陀佛。”
“你怎样了?”
“我?还是他?老样子,死不了!”
陈蕊蕊一声叹息,“现在回家了?”
丁尔拉抬头,夜幕降临,一片灯红酒绿,自嘲道,“我这种千年老妖,除了滚回老巢,还能去哪儿?”
“要么来我家?曾凡茗出差呢。”陈蕊蕊试探。
“拒绝。”丁尔拉干脆利落,“一,平时你电话过来,从来不管我的死活,今天电话突然关心我,有诈;二,我刚从裘小洛家走,你的电话就来,说明裘小洛跟你有串通;三,我很好,不用费心,脚趾头都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不想听,屏蔽。就酱,挂了,拜拜咯。”
丁尔拉掐了电话,关机。这种时候,她从来不想费心在他处得到安慰,她不是裘小洛,脆弱哀伤得像只小动物,需要有人呵护有人抚摸,她是谁,她是响当当的铜豌豆丁尔拉。
眼见灯火通明,已是隆冬,南方的冬夜又苦又难捱,丁尔拉一想到家中寂寞空虚冷,又断了回家的主意,扭头走进另一条街道,除了自家老巢,这里还有一个只属于她的秘密小巢。
职业装束质地考究,裹住丁尔拉纤腰翘臀,蜕下后却是一副线条极其明锐的身体:宽肩窄腰,臀部浑圆,腿肌流畅,马甲线恰到好处。所谓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大概讲得就是丁尔拉这样的好身材,既不锋利张扬,也不垮塌软弱,和尤雾的婀娜风情不一样,丁尔拉的体态带着力量美,紧致但并不僵硬,这是她多年规律训练的结果。
深色紧身速干T恤,黑色紧身速干短裤,头发扎紧成马尾,待她穿戴完毕从更衣室入场,果不其然,一进门,满场蒸腾热辣的汗水味儿和拳王油味儿扑面而来,人人皮肉汗光水亮,水沙袋砰响声不绝于耳,丁尔拉瞬间快活,运动即性感,凶猛而迅捷的拳击给丁尔拉带来另一种快感。
缠手带一丝不苟绑好,空击,出拳,正蹬,侧踢,扫踢。丁尔拉每一次出击都扎实稳当,力度惊人,她动作漂亮精准,水沙袋发出响亮干脆的声音,一时间,拳馆的人纷纷侧目,只见看似柔弱的一个女孩儿,打起拳来却异常生猛。丁尔拉心无旁骛,世界只剩下自己,周遭寂静,她只听见自己的呼吸。
待她一个小时结束,已是大汗淋漓,每一根血管里都有血液咆哮的声响,丁尔拉抹一把汗,静静下了场在一边休息,来往的教练与她熟稔,她不时和他们点头打着招呼,静待心跳平息。忽然,她觉得有些异样,似乎有人在某个角落盯着自己,她起身环顾,又想大概是幻觉,一来二去,丁尔拉索性去了盥洗室,冲洗干净穿衣回家。
隆冬深夜,丁尔拉裹紧衣服,从暖热拳馆走入萧飒大街,路上行人极少,丁尔拉加快步子,愈觉身后有什么人紧跟,她警觉驻足,那影子似乎也在暗处屏息等待。丁尔拉悄悄转了转手指上那枚防身戒指,浑身肌肉蓄势待发,方才一个小时的拳击,她的肌肉仍存着出拳的记忆。她继续稳步向前,不动声色,隐约听身后脚步声又起,便加快步子,选了一条似乎人多一些的宽敞大路,见路边一家酒吧,丁尔拉不假思索,推门而入。
一进门,炸了耳膜的通天音响让丁尔拉瞬间无措,她极少来这种场合,随意在吧台要了一杯低度鸡尾酒,看一池子群魔乱舞,每个细胞,倒也活跃起来了。
舞池中灯束狂乱,被裘小洛一话浸入冰窟的心死而复生,却在绝处逢生际涌出难以抵挡的回忆,梁清润和那个人的脸分明清晰地显露出来,丁尔拉烦躁,干脆她掷了酒杯,跳下人海,和一群男男女女贴面热舞,故意将一具肉身扭得痴醉,妄图将记忆挤出脑袋,人间多是纵情的欢愉,对苦痛的记忆,需时刻保持警惕。
没多久,丁尔拉就敏锐地感觉到,有人试图在用目光扫射她,应该是那跟踪者,丁尔拉想,这目光不怀好意,充满肉欲。年轻的单身女郎独自在夜店买醉,犹如一块美味诱饵,寂寞的猎艳者慢慢向她靠近,试图在激烈的音乐中,假装无意触点她的身体。
丁尔拉反感,欲拨出污浊人群,却被来人嬉皮笑脸故意挡住,四面八方尽无出路,丁尔拉鼻孔嗤出一声冷笑,对着来人裆下一膝,她动作轻且迅,但力量却是分毫不减,那人鬼叫一声,痛苦地弯下腰去,丁尔拉冷冷扫他一眼,趁机于人流中拨开一条甬道,钻了出来。
回望,音乐绝尘卷返,瞬间离她千百万里,她坐回位置,一时觉得了无生趣,酒杯中还剩最后一口,她拿起杯子,正欲一饮而尽走人,突然被一只手挡住,那人摘了她手里的杯盏,道:
“单身姑娘,不要碰自己离开过的杯子,片刻都不可以。”
丁尔拉诧异,抬头但见一张饱含了故事的面孔浮在眼前,那人取了杯盏,脸上表情轻佻冷漠,眼中沧桑却是难以掩盖,这两种神色形成古怪的对比,丁尔拉在往常饱受精神重创的来访者眼中看到过同样的表情,无色无味,但深刻见底。
丁尔拉不说话,低头见那人穿着一双与夜店格格不入的登山靴,工装裤,冲锋衣,泥灰尚存,丁尔拉认得,一身低调的户外名牌,价格不菲。灰白胡子,灰白头发,多日没修剪的样子,很是凌乱,但脸庞并不苍老,看不出真实年龄。这一身装扮在夜店里出现实在奇异,对方满目疮痍的样子,唯有一对睫毛尤其坚硬浓黑,丁尔拉盯着那睫毛,突然很想摸一摸,又被自己古怪的念头惊得一笑,只好顺着笑容向对方颔首:
“谢谢今天英雄救美,勉为其难,姑且算我还是美女。”
“姑且算我也是英雄。”对方笑得倒是可亲。
丁尔拉不想逗留,道谢后起身便走。如果尤雾在场,她一定要为这艳遇多来几段周旋,但丁尔拉是绝缘体,她不允许自己身陷声色犬马,单身主义丁尔拉,空窗期已是一年又一年,数不太清了。
没走几步,丁尔拉还是觉得身后似乎有人,心拔到顶端,她紧着步子往家走,突然路边窜出一辆醇黑大切诺基,车灯刷亮她前方道路,丁尔拉回头看,一颗灰白的脑袋在车后朝她颔首微笑,示意她先走。
丁尔拉抿嘴,大切诺基不紧不慢跟在她身后,像一个保护神,丁尔拉心里安定不少,却仍然不放弃警惕,和大切诺基保持着绝对距离。
没多久,车窗摇下,那人侧过身来喊她:“我送你。”
丁尔拉莞尔:“多谢,离开过的杯子不能碰,陌生人的车同样不能上。”
大切诺基不死心,缓缓追上,“丁小姐,我们不是陌生人。”
丁尔拉心一沉:“你怎么知道我姓丁?”
“丁尔拉小姐,绿地小区31幢1903,我认识您很久了。”
丁尔拉站定,大切诺基见状停下,那人跳出车,露一口好看的白牙:“上车吧,我们见过的,单身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丁尔拉有些迟疑,那人递上一张名片,来人名叫章知难,某户外健身公司首席执行官:
“怕我劫色,那我就不开车了,知道你有轻微幽闭恐惧症,车内空间让你不安,这样吧,离家不远了,你一个人确实不安全,我陪你走回去。”
丁尔拉大惊,来人不可小觑,不仅知道她姓甚名谁,居住地址,连自己一向不轻易示人的幽闭恐惧症都知道,她内心掠过一丝惶恐:“你究竟是谁?”
章知难撇撇嘴,“刚给你的名片,丁小姐,你太健忘。”
借着明亮的路灯,丁尔拉看清章知难的长相,一张并不会令人记忆深刻的脸,但很耐看,有些疲惫,但干干净净,沟壑分明,棱角有度,深且有神的双眼皮,睫毛刚硬,有故事但绝对透亮的瞳孔,看着并不像坏人。
丁尔拉警觉,她不是尤雾外貌协会,以貌取人,这事儿她不能干,来人知道她的底细,她如临大敌,竖起耳朵,“长得挺衣冠禽兽啊。”
章知难也不生气,自报家门:“一,我是你楼上新搬来的邻居,2003,我们常一起搭电梯,晨跑有时会遇到;二,电梯里你神色紧张,浑身僵硬,从不睁眼,快速进快速出,我断定你大概有幽闭恐惧;三,有人误将你的快递扔到我家,所以知道你的名字;四,我不是坏人,今天刚去办的落户证明,来,给你看,安心。”
丁尔拉半信半疑,接过章知难递过来的资料,的确和自己是同一幢楼,这才想起来前段时间楼上装修,给自家门口贴了张纸条,大意是装修噪音,敬请原谅云云,还贴心地在门把上挂了一份小礼物,一副隔音耳塞。
“我前两天刚搬过来,以后大概会常见面。”
丁尔拉释然,伸出手去:“抱歉,失礼了,你好。”
章知难握住,丁尔拉的手犹如蛇的鳞片,从他温暖干燥的手心滑过,他轻皱眉头,脱下自己的外套,“借你,天冷,我看不得美女受冻。”
丁尔拉吓了一跳,下意识跳着躲闪开来,“谢谢,太暧昧,我拒绝。”
章知难哈哈大笑,“好吧,防备心很强,这点不错。”
“不是防备心,是潜意识里比较拒绝亲密动作。”
“握手不算?”
“那是礼节,聊表歉意。”
“总见你独来独往,没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空巢青年,自给自足。”
“也没有恋爱对象?”
“这话问得别有深意。”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该死,这话真是老掉牙。”
“抱歉,我单身主义,绝对不想谈恋爱。”
“你怎知道我一定想和你谈恋爱?”
“男女鲜有纯洁友情,欲望驱使是男女交往动力之一,人之本性,没什么好掩饰。”
“你倒坦然,我现在应该哑口无言。”
“怎么可能,你一肚子反驳我的话蓄势待发,给我面子罢了。”
“有趣。”
“生活已经无趣,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怎么对得起这灯红酒绿?”
“所以人间冷暖,红男绿女,不谈场恋爱,怎么对得起自己有趣的灵魂?”
“灵魂不一定非要谈恋爱才能得到升华。”
“但没经受过爱情的洗礼,它一定非常寂寞。”
“我耐得住寂寞,大叔。”
“哈哈哈……”章知难抚掌大笑,“没有老到掉牙眼昏的年纪,没有品尝过膝下无子的寂寥人生,没有经历独守空门对酌祖宗的凄凉,就没有资格说自己耐得住寂寞。”
“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生来是为了享受老来携手的乐趣,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单打独斗,每个人追求不一样,你不能强迫。”
“我可没强迫。”
“你在试探我。”
“你并不反感。”
“那是念在你是我邻居,又比我老。”
“看,开始耍无赖了吧。”章知难笑。
“谢谢包容。”
“好了,到家了,该说再见了。”
丁尔拉这才发现电梯门开,自己已然跨出电梯,毫无察觉两人欣欣然已经聊到家门口,她回头想跟章知难告别,电梯门已经慢慢合拢,她没回过神来,惊讶得张大了嘴。
“你今天没有幽闭症,晚安。”章知难在电梯缝里温暖地和她说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