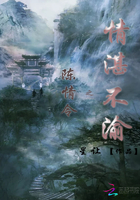天一的面前是一座墓碑,就像其它新立的墓,干净,素白,冷硬。它昭告天下,有一个人,一段经历,被登记上了那将被世人遗忘的长长的一串名单。
墓碑上的照片中的老人一头白发,笑得和蔼可亲,就像其他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样。也许他正微笑着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喂鸽子,也许他正搀着老伴儿在江边的小径上散步,但下一刻,他就死了,身体从四肢开始变凉,被赶到的儿女用棉被一包,绳子一捆,装进布袋,拉到殡仪馆。
没有人会在意他生前的故事,儿女总是对父母絮叨着的那些似真似幻的过去年岁感到不耐烦,无人传述,无人记录,这个人的历史成了一片空白,他是否曾经存在过已经是个不再重要的证伪命题了,因为——
他是个普通人。
用“命运”抹去一切信息,历史书上不再有名姓,亦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类记忆的荒谬性,真是个不错的玩笑。
“这里埋葬的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犯罪策划——顾问先生!”
如果是二十二岁的顾问,他一定会眉飞色舞地嘚瑟着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这句话。
可惜二十二岁的顾问死在二十三岁,这座墓碑的每个边角都在诉说着平庸:“这里埋葬着顾问,愿他安息。”
天一不无恶意地想,选择从天才之列落入庸人范畴的顾问成了一个无趣的人,或许连作为一个游戏的参与者都不够资格,已经不再值得他多看哪怕一眼了。
但他还是来到了这里,没有缘由地来到了这里。传述者已经过了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原因的年龄,因此也没了对自己的行事作令人头疼的深究的烦恼。
他穿得邋遢,没有带花,就像误入墓园的闲汉,无聊地咀嚼墓碑上的寥寥数语试图拼接墓主的生平。只是现在,这个奇怪的人却在一座墓碑前久久伫立,脸上的笑容意味不明。
天一想,他大概是来纪念一个天才的谢幕的,尽管对于天一来说,这个天才在丢下计划书向他道别时就已经死了。
但是在一个人开始进行物理意义上的腐烂前,他仍有无数种作出不一样选择的可能,而死亡让世态变迁尘埃落定,是非功过盖棺定论,眼前便只剩下一条路——烧成灰埋了。
天一哈哈大笑,笑这个曾经的天才原来也逃不过俗人的命运,笑自己原来在此之前还对这个自甘平庸的家伙抱有期待。
他想起了分别的那天。
“你是来道别的吗?”抢先把对方的真实意图问出可以促使对方在说出口时多作思考。
然而当时顾问“是啊”两字答得很干脆,既让天一意外了一下却也尽在意料之中,只能说顾问之所以为顾问不只是因为他叫顾问。
天一不是第一次见证天才死去,人总是要死的,而这个世界不乏天才。那些死人有的和他有过几年的交集,有的不过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有的名垂千古或遗臭万年,有的名字不曾为人所知,死得无声无息。天才这个物种就像工厂流水线上偶然生产出的精准贴合标准的产品,一样被送出去,卖掉,消耗掉,回收残余,再生产出新的来。
天一想起在和顾问的一次闲聊中(顾问离开前的一个月经常来找天一闲聊,虽然通常以两人互相中伤污辱告终),顾问用一如既往的“你答不答随你便”的语气问道:“照你说的你从史前活到现在,那你应该遇见过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吧?”
当时天一正往凝疴着上杯咖啡余垢的杯子里倒新的咖啡,用平常说“咖啡在炉上请自便”的语气答道:“是啊,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哦,那他们死后你怎么……处理他们?”顾问大概是斟酌了一下用词,所以句中略微停顿了一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难不成泡福尔马林里做成标本,找个天都那么大的私人博物馆收藏起来?”
“我是说,你还会记得他们吗?”
“当然都忘了啊,既然已经死了自然就不可能再爬起来为我跑腿了,放在脑子里除了占空间外没有任何作用。”
“看你把自己过成一幅中年失意大叔的样子,想不到还有定期清内存保养大脑的习惯啊。”
这场对话一样以两人的互喷告终。
纪念,无疑是一件活人出于不纯粹的目的而作的,对死人已毫无用处的事情。而记忆,不过是一场为了减轻负罪感的欺骗。
天一不喜欢记忆死人的名姓和事例——总会有人去做这无聊的事的,但如果一切关于顾问,那就不一样了。就像工厂专门团队正在精心开发新产品的时候忽然发现它在流水线上自己冒了出来,计划之外的东西总是令人惊喜,自然也会被人更长久地记忆。
于是这个意外之喜忝列严密策划的蓝图,并在将要变革时代的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
果然由此带来了更多的意外。
当被顾问用真理之线绑在床上时,天一除了翻了翻眼皮之外没有其他动作。反正死一次身体就会重置,天一对别人施加在他身体上的一切都给以大限度的宽容。
顾问盯着天一的眼睛黑得发亮,却还煞有介事地问了句:“做吗?”
天一记得自己当时虚着眼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怎么,是做之前还要定个价是吗?”
一经默许,不在计划之内的事便发生了。
顾问是个疯子,他总乐于尝试常人所不敢想象的事。天一作为一个疯子,总是对这些疯子存着几分纵容。顾问有什么特殊的呢?不过作为疯子的一员罢了。天一想,如果过去万年的那些疯子或天才们也对他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大概也不会拒绝吧。
但顾问又是特殊的,毕竟他是万年来第一个存了这种想法并且付诸实践的。
天一口吐白沫后化作黑烟,几秒后从厕所中走出来,整了整领角好像一切从未发生。
——JUST?A?TRY.
——A?GOOD?TRY.
这是他们事后达成的共识。传述者早已习惯爱人先死,不会愚蠢到因为一次约炮而爱得死去活来;某个一直致力于试探前者底线并在其上左右横跳的家伙也不会出于爱情或责任感,而放弃生活和自由。
几十年过去,当事人一方已死,而另一方不过是多了种新的体验。
就像顾问临走时说的那样:“我选择当一个平庸得令你讨厌的普通人,就不在你跟前晃悠碍你的眼了,估计你用不了多久就能忘了我吧?”
天一当时恶狠狠地说:“在你踏出书店的那一刻我就会删除我脑中所有关于你的记忆,记住你只会让我的脑中充满各种屎尿屁之类的词汇。”
随后顾问就踏出了书店,又折回来,指了指自己:“我是谁?”
天一第一次对顾问爆了粗口:“你他妈的赶紧滚吧!”
顾问确实再也没有回来。天一自然也不会去找他。所谓“最后一面”不过是人类自己施加于自己的不成熟观念,天一没见的多了,不讲究这些。
墓碑上的老人笑着看向来者,寻不出一丝年轻时恶劣的痕迹。最后的天一认知里的顾问就出现在分别的那天,记忆中的人一直年轻且鲜活。天一没有陪伴顾问老去的经历,也没有他逐渐生出皱纹衰老下去的记忆,直到这一刻才有一个完全陌生的老头的形象将那存续八十余年的记忆覆盖。
疯狂的顾问死在二十三岁,活下来的是平庸的他。而那个做过的,爱过的顾问确实陪伴天一到他死去。
天一想起那天做过之后,两人坐在床边,按理应该来一支事后烟。只是顾问供奉自己的身体有如供奉神像,是绝对不可能吸烟的;天一吸烟的样子我们同样难以想象。于是天一用咖啡淋了自己一脸,顺带溅到了顾问。
顾问说:“鄙人其实有那么一点洁癖。”
天一目视前方,用同样的口吻说道:“鄙人一周没洗澡最多用咖啡洗脸。”
“我没有洁癖了。”顾问索性略过这个话题,“我们这算是深入了解过了,把天都炸了之后要不挑个地方造间小屋?”
“然后你把你自己锁里面烂死和我永不相见是吗?”
“你难道就不想过几年退休生活?长期在压力下工作加上咖啡当饭造成的胃溃疡大概率能让人发疯。”
天一闻言哈哈大笑,笑了一阵,又用带着笑意的语气说道:“顾问,想不到你这么天真。欲望不过是生物基因决定的生理需求,由此形成的爱情、依赖等不过是激素和神经反射引发的错觉,而我早已脱离了被这种低端反射控制的层面。”
“这样啊,所以——”
“你做了个尝试,没有招致我暴怒后杀了你的后果。”
顾问是聪明人,向来懂得知难而退。
所以,现在,天一站在墓碑前,似祝福又似宣告:“恭喜你,顾问,你终于成了一个平庸乏味令人厌恶的普通人。你也终于自己一个人烂死在了你那座该死的小屋里。”
死亡是人类唯一的结局,那意味着他失去了被这个世界关注的权利,同时拥有了化成灰埋起来不占用土地的义务。人类总有无穷无尽的欲望,也总有大把的事来不及做,可无论如何终究逃不过红颜成枯骨,英雄化灰土。他们惧怕死亡,祈求永生,这多么顺理成章。
天一却不由得想,或许死亡有时也是一件美事,所有失去后反刍回忆的痛苦与被时光涂改得面目全非的记忆都被一捧黑土掩埋,无休止转动的时钟终于停摆,罪恶的盛宴中主座缺席,世界仍将照常运转。
但天一不打算在这不可能的事上作浪费时间的遐想——他很久没有这么做了,随时可能到来的崩溃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任何一次多思多虑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天一在多年实践后能够完美地控制自己大脑的内存,于是,他在大脑中筛选出所有和顾问有关的信息,清除,一干二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