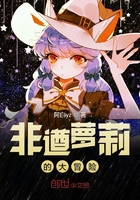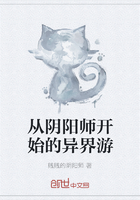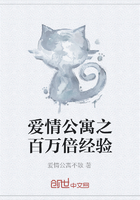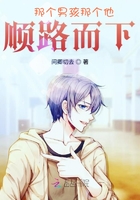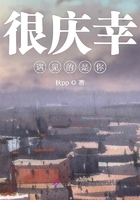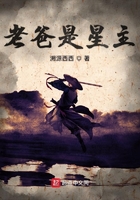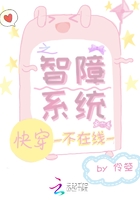通了高铁,大概一两个小时,便能到福建。
母亲想带我来看看武夷山水,好教我从纷杂的心境中脱身。
先是坐船,听船夫讲了一通朱熹,讲得眉飞色舞。两小时的船,没听到一字一句与柳永有关一一也许是我当时并不知福建是柳永故地,便未曾注意听讲的缘故罢。
下船后是到武夷宫去,方在入口看到一指示牌,极角落的地方标了“柳永纪念馆”几字。
我不了解柳永有何生平,仅背过一篇《雨霖铃》,知是他写的;再就是听过河图唱的《白衣》,知道唱的是他。除此之外,我再无更多的触动。不过,我向来自诩文人,到了一处景点,这些纪念馆甚么的,装模作样也总归是要去拜会一番的。
向柳永纪念馆的方向走去,人烟渐稀,道路两旁新生的草芽从石板的缝隙间钻出,側也别有一番情味。母亲道:“人来得少,想是不甚好看。”
但我总觉得,既是来了,进去走一圈也不妨事,便不知何时行至馆前了。那是座古建筑,正对过去是个石牌坊,看不出有甚么雕花,只觉像是刚从石崖上凿下的巨石胡乱一堆,教人喘不过气来。门旁有一座石碑,石碑上不知是被风雨还是青苔斑驳了的纹痕将碑文割得支离破碎,读不懂,读不进,读不出。
从前我读《雨霖铃》,只觉得很轻,连哀伤都是轻淡的,甚至敌不过尘埃,只消来一缕江南的细风,便能将它拂去。我便在心神间勾勒出那么一位词人的影像:散发、白衣、银灰的色调,神情憔悴而高傲,但一定消瘦而单薄,仿佛随时都会随风而去。
我难以想象那么位词人竟会被刻在石板上,和这些木讷笨重的死物共存。至少该给他留一卷长卷作为承载他的位置罢,最好再添些若虚若实的水墨画。
踏入纪念馆,心便空了,有如空荡荡的庭院一般。几座有字的墙壁国着长满衰草的庭院,墙上的字依旧在反复吞吐寥寥几句生平。我仍不甘心,非要在字里行间读出些什么来,没有;我便又在偌大的庭院中摸索,只有衰草。柳永的一生不该被写成生硬的生平,因为与其说他活在世间,倒不如说他活在词里。他打世间走过,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但他的词句却在中国文脉上刻下了重重一笔。
那些策划者们,他们知道柳永的名气,又知道他与福建有关系,便踌躇满志要折腾出一个纪念馆来。但当他们真正开始收集关于柳永的资料时,才发现这惊世词人除了宋词千篇外,所剩下的真是太少了,又不好将所有的词作都刻一番,便只好将大片的空白留给荒草了。但为什么不种些桃花柳树呢?柳永给人的印象不该是荒草萋萋,当是罗帐、残泪、笔墨、清酒,雕栏外几朝花树如烟,暧风熏人易醉,画楼内红烛点燃幻梦,柔美的姑娘轻拨琵琶将新写好的词弹上八九遍。
从后门出的纪念馆,一面墙壁撞入眼帘。总算寻到一丝宽慰了,那面墙壁上刻满了柳永的词句,柳永总算作为一个词人出现了。但我仍不满足,我想,柳永写下的那些词句该在大街小巷传唱,而不是被刻在墙壁上与时间一同消亡。可是,又有谁来唱呢?谁会唱呢?谁能唱呢?
河图的《白衣》在我耳畔萦绕:“那白衣,是平凡也不甘……一梦黄粱一壶酒,一身白衣一生哉……”
我却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我便也拿起笔,写起歌词来:“流连在烟花柳巷,失望于功名朝堂,凡有井水到过的地方,皆有我的歌谣在传唱……浮沉排浪摇碎了梦中江南,打湿我的笔何能再写出惊艳,回首望扬州一梦多少年……”
依旧不满意,柳永填了世间千百篇词,那得要什么样的词句才能写好他,写好这位将浮名换作浅斟低唱的白衣卿相?柳永不需要刻意的纪念,他需要的只是有人能在或寂寞或欣悦时,随口唱几句,唱的是他的词句。
次日下午,别过柳永,一两个小时后回到杭州,带回一身无名的悲怆。倘有机会,我还想带壶酒,带把琵琶,再去看一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