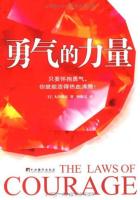李义山闭了闭眼睛,时间太紧迫,华阳命悬一系,无论如何自己也只能带大伙向前冲了!他要求大伙将无用的东西尽数抛弃,能防雨的衣服或布料为裴泽渡和华阳遮住头脸及伤处,其他的人则或用包袱布或用衣服胡乱遮一下,整队再出发。宁国将令狐绢托给春瑶,自己在头上顶了件包袱布也赶到前面来了,她早看出了李义山不断地望着头顶山峰和地面路径辨别行进方向,但此时天气如此恶劣,不知李义山还能不能辨别出路径来,她很是担忧。虽然李义山仍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但宁国知道他必是担心大伙知道了情绪不稳而故做镇定,她想此时也许最需要帮助的应该是他,于是再出发时走到了前面他的身边。
李义山转头见宁国跟上前来,不由欣然地一笑,只相视一眼,他知道她明白了什么,她也知道他担心着什么。他轻声地宽慰道:“放心!”
她眼中满是信任和依赖地望着他,点点头:“嗯。”
李义山想起来什么,又一笑:“你来的正好,瞧。”他将手中的一段草茎给她看,这草长得跟寻常的草没什么两样,但茎却是紫红的。
宁国很快明白了,点头道:“茎与别的不同。”
李义山赞许地看了她一眼:“没错,”他接着解释道,“这草俗名叫做抓地龙,因为它和别的草习性不一样,它只循着阳光生长。”他望了望头顶上什么也看不见的布满雨雾的天空。
宁国想了想,领悟地道:“但这里常年看不到阳光,只是日中偶有一瞬,此时太阳在正南方,所以——它应该是向南方生长的。”
李义山赞许地点点头:“你一路上帮我注意这草的长势,我借此来判断选择的路径是否偏离了方向。”
宁国点了点头。
可即使有宁国的帮助,他们的行进速度还是很缓慢。雨越来越大,道路不明,大伙儿伤的伤,痛的痛,饥寒交迫都让他们的速度进展得不快。
忽听李瑞钦在后面焦急地叫了起来:“华阳,你怎么了?华阳——”
宁国返头只见茫茫的雨雾中李瑞钦蹲在地上,一只手紧紧环抱着华阳,另一只手抓着她的一只手,华国则拼命挣扎着要推开他。春瑶也已放开扶着的令狐绢扑了过去,抓着华阳另一只手,宁国急忙上前帮忙,三个人一番手忙脚乱才制止住华阳,夺下她手中的匕首。但四人都是气喘吁吁,满身泥水满脸狼狈了。
原来行到途中华阳许是被雨水激打得醒了过来,疼痛难忍的她竟伸手将背着她的李瑞钦腰上佩的匕首拔了下来,李瑞钦发现了赶忙制止,挣扎中华阳跌落地上,不料她仍握着匕首要去扎自己,李瑞钦只能抵死抱紧她不放。
见华阳倒在草丛上,气息奄奄地仍然控制不住地乱抓乱挠,李瑞钦终于感觉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这几日来的辛苦和恐慌他都咬牙承受下来,但此时华阳的痛苦和绝望却让他的忍耐到达了极限,他对着天空大叫了一声,用匕首对着旁边的一棵树狠狠地扎过去:“老天,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她?为什么?”不料用力太猛,匕首扎得太深了,他自己竟一下子取不出来,无边的愤怒让他抬起脚对着树狠命地踢着……
李义山蹲下来扶住因剧痛尤在不断地抓挠颤抖的华阳,他伸手拂开华阳面上的乱发,抚摸华阳的额头,在雨水的淋浇下,她的额头居然还有些烫手,他不胜内疚地抱紧了她。
不料他这个动作激起了已是意识昏乱的华阳脑海中的深刻记忆,华阳突然安静下来,流泪叫道:“师父!”
李义山不由地一惊,华阳竟然已全然辩识不出人来,开始说胡话了。
他正发怔,华阳又轻声道:“师父,我好疼。”她的语气中有从来不曾展露出来过的脆弱和撒娇。
李义山禁不住抚摸着她的头:“我知道,我都知道,来,我背你回去。”
见华阳乖巧温驯地趴在李义山背上,宁国心中突然很不是滋味,但是立刻又甩了甩头,若非带他们入谷,华阳怎会中毒?又怎会落得如此?自己身为李唐公主肚量不能太小,这么一想,她心中又释然了。却见李瑞钦已止住了满腔的狂怒和愤懑,自己一声不吭地将树上的匕首费力弄了下来插回腰间,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跟在李义山身后,一向眼里只有自己的大唐小王爷,如今却惯能做小伏低,真正是让人诧异不已!
再往前走,雨势终于小了下来,但太阳也很快就出来了,夏日雨后的烈焰格外灼人,虽在山谷只能看到太阳的一线,但谷底的水汽蒸腾形成的雾汽更浓。走了这么长时间仍然不见谷口,大伙都已没了开口问询的勇气,只能坚信玉溪的决断正确了。李义山感觉到华阳贴在他背上的身体不断地传来热度,心里焦灼万分,但是仍镇定地鼓励着大伙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一会儿,千万不能掉队……
当看到了前日进谷来时的李瑞钦指给他们看的迎客松时,宁国尚不能相信已走到了神龙谷口,正犹豫着反复地辨别,突然听到前面一声大叫:“公主?真的是公主!”很快便见高喜连跌带撞地奔了过来,跪在了宁国面前,也不顾礼仪带着哭腔就嚷道:“公主,我们家小王爷呢?”
宁国才知道他们是真正地回到了神龙谷进口处,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她回头望了望,因为先前见马维迁体力不支,李瑞钦主动替换他去搀扶裴泽渡因而走在了后面。也真是的,要是在三天前她见了李瑞钦这副模样也会不敢相认的,那个颐指气使、光鲜亮眼的小王爷现在正弯着腰,头发零乱,一身衣服破败不堪,肩上还搭着裴泽渡的一条胳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在队伍最后。
高喜睁大了眼,一副打死也不敢相信的样子。终于他反应了过来,又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奔了过去:“小王爷,真的是小王爷!把奴才急死了,奴才都快把命给急没了,小王爷你可算是回来了。”一面说一面就要将从裴泽渡的胳膊从李瑞钦背上给掀下来。
“滚!”李瑞钦只低低地从嘶哑的嗓子里吼了声,又接着道了声,“水!”
高喜吓得手忙缩了回去,听见吩咐又赶紧从身边解下一个水囊,想想又缩了手,道:“这个是奴才的,奴才去给小王爷另取一个干净的来,可好?”
见李瑞钦不耐烦回答,只伸出手来,高喜忙小心地将水囊擦了又擦,才双手递给了他。
可李瑞钦自己并不喝,他将裴泽渡交给高喜,自己就气喘吁吁地忙忙地转头寻找,见李义山正小心地将华阳从背上给放下来,李瑞钦忙将水囊凑过去喂给华阳,但哪里喂得进?他拧紧了眉头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脸色,回头命正将裴泽渡小心地放在一棵树下的高喜:“把马全拉进来!快!”
高喜一怔,忙放下裴泽渡,小心翼翼地上前回报道:“爷,只有一匹马了。”
不光李瑞钦,众人都一齐愣了,李瑞钦的公子脾气瞬间又回来了,只是不像往日急躁得立刻用脚踢,只盯着高喜:“你连马都看不住?”
高喜慌忙跪下回报:“不是的,昨儿晚上,奴才在此等到日落,有几个人背着令狐公子和表少爷回来了,说令狐公子伤着了要赶紧就医,把马都骑走了,袁达也跟着一道去护送,当时他们说今儿一早就把马都送回来的,可是——,到现在还没送回来。”他看了李瑞钦一眼,又小心地邀功道,“还是我坚持说小王爷的马不能给别人骑,才留下了。”
众人都大吃一惊,令狐绹竟早已出谷,还被人挟持了?
本坐在一旁冷眼看着他主仆俩的令狐绢一听到有令狐绹的消息,急忙踮着一只脚跳过来问:“我哥伤了?伤得怎样?”
高喜低着头从眼角偷窥了一下李瑞钦铁青的脸色,向令狐绢轻轻摇了摇头道:“天色很晚了,那几个人急匆匆的,袁达武艺又高强,有他跟着我就没拦住仔细问。”
他的话很在理,让令狐绢不由地松了口气,袁达确实是令狐绹最得力的随从,一身好功夫不亚于令狐绹,而且沉稳机智,但她欣慰之余仍有些担忧。
李瑞钦却生气不已,要是依照往常的性子,他一定立刻就要踹死眼前这个不长眼睛的奴才,但他现在好像连生气的力气也没了。
高喜见他仍然阴沉着脸,又嗫嚅着解释道:“要不是他们说岔道多怕走岔了,奴才早就直接进谷去接小王爷了。”
李瑞钦沉默了一会,也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得先解决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道:“去拿水,还有吃的来!”
高喜如蒙大赦,忙一溜烟向谷口跑,一路还高声叫道:“高兴,高兴——,快,小王爷回来了,快,拿吃的来!”他的速度还真迅速,只不过一会儿,就又同高兴一起牵着李瑞钦的马进来了,马上不但驮着水囊,更有一大袋吃食。
李义山见华阳仍在昏迷之中,脸色发青,李瑞钦给她喝水也没反应,春瑶只得寻了个小勺一口口地喂给她,但一口水倒有一多半没有喂下去就流出来了。他又转头去看裴泽渡,裴泽渡虽然全力支撑着走了出来,但看得出来气力亦已消耗到极限了,马维迁正小心翼翼地将水喂给他喝。
“马给我!”李义山突然向牵马的高喜道。
高喜愣了愣,却转头去望向李瑞钦。
李瑞钦立刻就明白了李义山的意思,只问:“你自己去?”
李义山摇摇头:“我带华阳去,她不能拖了。”
李瑞钦有些犹豫了:“我……”但他没说下去,他很想自己护着华阳去,但他不敢保证自己能让华阳安然无恙,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此时此刻,他竟然不能保证自己心爱女人的安全。他又看看高喜,也许目前体力更好的高喜更合适护送华阳?
李义山明白他的想法,直率地道:“你觉得我去求云机道长更好还是别的人去更好?”
那倒是,让高喜去,只怕他费半天劲也不能把事情说清楚,还指不定云机道长压根就不会见他呢!李瑞钦终于点了点头,整理了一下衣服,对李义山一个到地长揖。高喜在旁边看得有点傻了,回过神来忙将马缰马鞭恭恭敬敬地交到李义山手里。
宁国已迅速地将一个水囊和一包干粮包好递到李义山手上,李义山又转头看了裴泽渡一眼:“玉松,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裴泽渡睁开双眼,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当心!”
李义山点点头,他明白这件事不是那么偶然的,仿佛有一只大手隐在后面,处心积虑地阻止着他们出谷来,前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危机在等着他,他不知道。
望着李义山打马飞驰而去的背影,李瑞钦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在华阳生死危关的时候他却每次都束手无策,这种无力和无能的感觉让他非常地郁闷,他愤愤地用力踢着身旁的树,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
高喜马上过来了,蹲下来抱住他的脚:“小王爷,当心脚疼,小王爷要是生气就踢奴才好了,可千万别踢伤了自己。”每每李瑞钦生气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劝解,而每次小王爷就算有再大的气也会就此罢脚,最多不过再轻踹上他一脚就算了。
可李瑞钦只是满眼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这本是自己最得力最贴心的奴才,但现在他压根就不明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