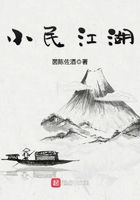(一)
一个步兵排,火力配置是3挺轻机枪和30支步枪,配备军卡两辆。
一个工兵排,军卡两辆,按照作战条例配备了绳索工具雷管炸药等等物资。
营直属机炮连,6挺马克沁重机枪和2门82迫击炮,配备军卡三辆。
师直属高射机枪连,4门20毫米高射炮,配备军卡四辆。
后勤通讯部队,连同被护送人员,配备军卡两辆。
原本就是想整一挺重机枪,没想到居然凑了一支营级规模的队伍出来!
总共人数居然接近400人,配备了十三辆军卡!
“呵呵呵,这要是不整出来点动静的话,辜负很多人啊!”岳小川笑着说道。
洪世寿笑着说道:“要是还不想讲的话,也不用勉强啊!等到胡家骥来了你跟他聊!嘿嘿嘿嘿。”
看看手表,夜里十一点多,宋希濂说的人员物资车辆全部到位时间是明天凌晨五点半,还有六个多小时。
大家都在忙,岳小川琢磨着,自己也要抓紧时间整点东西。
(二)
“胡家骥亲自带队,还配备了师直属高射机枪连?还有骑兵?”
张治中内心里暗暗嘀咕了一下,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王敬久给张治中汇报此事的电报算起来效率也挺高了,不算耽误。
要把电文转译成军用密码,然后交给发报员拍发,接收方记录下来后再转给破译员转译出来,由机要处视密级决定交由谁来阅读批示。
给德国顾问安排个护卫队这种事情,都在王敬久和宋希濂的权限范围之内,他们不需要得到张治中批准。
“如遇袭扰进犯,以驱离为主,万不可恋战,重中之重还是德国顾问和洪联络员的人身安全”,王敬久下达的指令也很清晰,胡家骥不可能理解歪的。
值班参谋符昭骞抱歉地说道:“军座,非常抱歉,虽然按照密级和重要程度,并不需要现在打扰您......”
张治中摆摆手,说道:“不用兜圈子,昭骞,你怎么想的就直接说!”
符昭骞犹豫了一下,说道:“军座,属下不敢妄言,属下只是觉得有些蹊跷,所以想提醒一下军座,是不是尽快把这个事情向上面报告一下?”
张治中看着符昭骞的眼睛,心想,你不喊醒我不问我,等我明早上醒了再处理,不就行了吗?坦白说,有些蹊跷就你符昭骞看出来了啊,你觉得宋希濂傻还是王敬久傻啊!
“怎么个蹊跷法呢?不用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张治中站起身来去拿暖壶亲自给这个手下倒水。
符昭骞是1901年生人,虽然也就30出头,但是因为符昭骞的阅历丰富,在张治中的参谋团队里算是心思比较缜密的一个。
符昭骞出生在海南文昌,10岁时候跟着长辈下南洋,在当时还属于马来亚的新加坡半工半读,15岁那年在远房亲戚推荐下考进云南讲武堂跟了唐继尧9年之久。1925年因为路线问题,符昭骞放弃了唐继尧陈炯明军阀转投革命,参加了粤军独立团和东征,1926年担任粤军独立师参谋处长。
1927年路线选择上,出生于海南文昌与宋家有些世家关系的符昭骞,在粤系和凯申总之间选择了后者,并且于1928年考入陆军大学9期,正式成为了“黄浙陆一”嫡系。
符昭骞打了个立正,说道:“报告军座!正是因为属下说不清楚,所以才觉得应该尽快报告上去!”
“好!就按你的意思办!”
张治中说完,拿起钢笔在电文上写道:“阅,请及时上报凯申总司令并知会宋部长。”
看了一眼手表,张治中签名并且注明时间,把电文递给符昭骞。
符昭骞双手接过电报,转身走了出去。
看着符昭骞走出去之后,张治中揉了揉太阳穴,伸过去拿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了下去,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地图前面,盯着南京浦口码头的位置看了很长时间。
(三)
码头调度室给他们安排了一间休息室,颠簸了一路的洪世寿很快就睡着了,然而一觉醒来之后,洪世寿发现岳小川仍然台灯下面写写画画,诧异地问道:“啊?你你,岳顾问你这啥情况啊,一夜没睡啊!”
岳小川抬头看看洪世寿,笑着说道:“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情况复杂,所以只能争分夺秒啊!”
洪世寿慢慢走过来,一边揉眼睛一边问道:“为啥争分夺秒啊?什么任务......这这这,这是那啥?嗯?”
一张一张的白纸上,画都是军舰的剖面图,各种数据标注的很仔细,还有红红蓝蓝的色块,标注着航海室、雷达室、无线电室、弹药库、炮塔......
岳小川嘿嘿一笑,说道:“咋了,很奇怪吗?”
洪世寿已经困意全无,他指着图纸疑惑地问道:“小鬼子的军舰?”
岳小川努努嘴,说道:“是啊!码头上就能看到,旗舰轻巡天龙号;筑摩级防护巡洋舰1艘,平户号;新高型防护巡洋舰1艘,对马号;睦月级驱逐舰四艘,三日月号、菊月号、望月号,这三艘在江面,还有一艘夕月号正做检修。总共七艘,六艘在江面咱们眼皮底下,一艘在上海船坞,这就是小鬼子在南京的23驱逐舰队的全部兵力了。”
“嘶......”洪世寿瞪大了眼睛,用不可思议的口吻问道:“你们对小鬼子的情报工作很到位啊!不过......”
后面的话,洪世寿没说出来。
“嗯,知道你想问啥,稍等会啊,几分钟,我把这些标注弄完。”
洪世寿看看埋头专心作着标注的岳小川,搓搓手呵口热气,拎着暖瓶往外面走去。
天还没亮,黑咕隆咚的江面上,小鬼子的舰队耀武扬威地用探照灯向江面和岸上肆无忌惮地照射。
嘶,好冷!
一月底二月初的南京,差不多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了,尤其是这里还是江边,硬硬的江风像小刀子一样割的耳朵疼。
可是......好几千吨排水量的钢铁堡垒,怎么可能会被那么容易击沉?
洪世寿不知道岳小川这一夜熬的,到底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