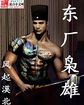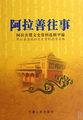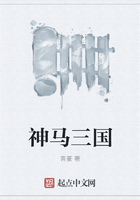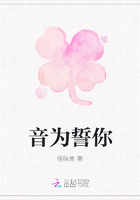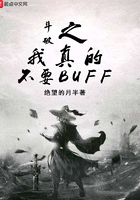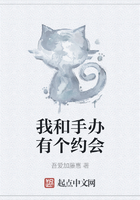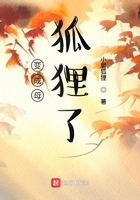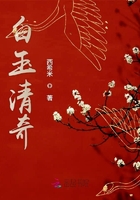和楚浩一起面圣的有三位,都是四五十岁了,只有楚浩一个人不紧不慢按照太监和卫兵指导的程序一步一步来到偏殿等候,其他那三位外官,汗如雨下,又怕湿了朝服,紧张地不知所以。
九成宫位于天台山上,这里四季无酷暑,夏季气候宜人,况且已经立秋,还能热到哪儿去,可那几个人不停擦汗,嘴里不时小声念念有词,大约是背诵职位上的业绩,模糊听到有数字。
大约一刻钟,太监把他们领进大殿。
粗大的柱子和阳光照亮的地面花砖,立刻让人肃穆,楚浩第一次到这么规矩的地方,不由得也有些紧绷。殿里面熏着一种绵绵的香,闻着很舒服。
一旁的太监说:“拜。”
几人跪倒地上,山呼万岁。
皇上一个接一个问了业绩,给他们升了官,安排了差事。只留楚浩一个在地上跪了半个时辰,膝盖都受不了。
等其他人都走了,楚浩甚至听到皇上喝水的声音,接着听太监说:“起。”
楚浩站起身来,不顾太监讲的规矩,抬头看了一眼皇上,才又低下去。
“你就是楚浩。”皇上问。
“微臣正是。”
“卢大人才把你的荐议折子呈上来,你就要辞职,你这官刚当上就腻歪了?别人都是被迫辞官,你被典选看中,就要升迁,为什么要辞?”
“启禀陛下,微臣自小就散慢惯了,守不住当官的规矩,朝廷对官员都有考核,微臣怕官位还没坐稳,就被拉下来。重要的是,微臣觉得太局促,愿意养马、做生意,活个自在。”
“父母养你如斯,你懒与仕途、不求上进,此为不孝;你能骑马打仗,不为国家效力,此为不忠;轻视前辈举荐,此为不义。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义,做个商人也难免欺诈妄为。”
“商人获利也可以赡养父母,便利百姓也是造福国家,不违心对待举荐的人,也是仁义。”
“哼,你倒振振有词、头头是道。那朕问你,朕本想十月去凉州,大臣们以为不可,说西垂尚未息兵,陇右户口凋敝,銮舆所至,供亿百端。我听了大臣的劝谏,罢了西巡。如果朕也由着性子,一意孤行,那和隋炀帝有何不同?朕尚且如此,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官却要活得恣意?”
“自古帝王,莫不巡守。陛下说要去凉州,大臣们所以劝谏,是因为那凉州边远,诸多不便,而非说巡守不对。”
“哦,那你说在富足地区巡守就对了?”
“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巡守大约也要如此吧。陛下如果去富足的地方巡守,首先要整修道路,修路利国利民;其次要购置銮驾锦旗、帐幔,花钱从百姓手中购置物品,老百姓才能有钱;百姓有钱,才舍得花钱从匠人手里买绢帛、滑犁;匠人有了钱就会买农人的粮食;农人有了钱,可以交税,买商人的商品。这样商人、匠人、农人乃至国家都会有钱。所以有钱要花,商人、匠人、农人、官员都不可或缺,这一切从那儿开始的呢,是从陛下的巡守开始的。陛下巡守推动了百姓钱财流动的波澜,钱财流通起来,百姓才能活起来。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那建造宫室也花钱啊,照你这么说就要多建宫殿了?”
“对啊,建宫殿要买木材,运石材,买绸缎。雇佣些官员要发给他们俸禄,这些官员去市场和坊间进货、花销,富了商人,商人去买货,富了百姓,岂不是好事?”
“倒是从来没有臣下给朕说这样的观点,你如此天马行空,听起来又有几分道理。”
“凡事要有度,陛下之所以罢了这次西巡,并不是由着性子去做,是因为陛下是明君,能够掌握那个度,平衡大臣和百姓。”
“朕一直以来希望身边能有一个直言劝谏的人,封你做个监察御史,做朕的耳目,难道还不比你做个商人?”
“陛下,微臣私下常想,商人地位低贱,为什么哪朝、哪代、哪国都离不开商人?微臣愚钝,想不通个中道理,只浅薄了一个拙见:没有流通,价值就不能体现。比如一个农人,百斤种子,十亩地,来年收了三千斤粮食,刨除种子一百斤,自家一年吃掉一千斤,交税三百斤,留出为来年灾荒存储六百斤,还有一千斤,如果不卖给商人,那这一千斤粮食的价值留在农家就没有意义,只有经过商人流通把这一千斤粮食卖给需要的人,这些粮食才有价值。农人从商人那儿拿到钱,可以购置需要的东西,商人从中获利可以购置自己需要的东西,商人再把匠人的生产富余卖给农人等等依次推下去,价值就流通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多,国家就会越来越富庶。而那一千斤粮食就是农人生产的价值,商人负责购买运输再卖出就是商人创造的价值。这样流通起来,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得到增长。而微臣喜欢做,愿意做的正是让国家和百姓都富庶的事情,为什么不让微臣去做呢?微臣说得拙劣,却是微臣的肺腑之言,望陛下斟酌。”
皇上深思着,缓缓说道:“不,能跟朕畅聊的大臣没有几个,何况你一个七品官,首次见到朕就能分析劝谏,朕要把你派到工部去,让你去负责皇宫的采买。不,朕要按照皇后的意见,把你派到靺鞨,从当地贩运山货回京,让你在荒凉的地方做商人,看你有什么本事在当地为朕富国强兵。”
“微臣,微臣倒是有个主意。”
“主意,你小小年纪、小小的官,哪儿有什么主意?莫非你也要像你的哥哥一样跟朕讨价还价。”
“微臣不敢,微臣愿意去守靺鞨,只是陛下要给微臣些便利。”
“哈哈哈,果然不出朕所料,说来听听,什么便利?”
“陛下知道商人的利来自流通、流动,靺鞨那个地方微臣去过,百里不见人烟,若是守在靺鞨那个地方,别说经商,饿死都有可能,所以陛下要给微臣永久开通的路条,微臣担保,十年内让靺鞨繁荣如幽州。”
……
楚浩与皇上达成了协定,回长安的路上,四周的景色变得那么靓丽,一点儿都没有秋天的萧瑟。
牧场上,李林接到洛阳那边的信,说梁毅派来的船队过几日就可到达洛阳。楚浩纳闷了,梁毅没有船只,没有沿途驿站可以使用,怎么可能把山货运到洛阳,他一刻没有停歇,叫上杨卫州骑马向东而去。
到了洛阳,楚浩把洛阳码头的每一个官兵都问了一个遍,也没有辽东船只靠岸的消息。第三天,他去到板渚,就在他站在板渚的河堤上向东远眺的时候,河面升起一个巨大的木筏,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一共九条一丈多宽,十几丈长的大木筏从远至近而来。打头的就是梁毅,楚浩高兴地跳进河里去迎接他们。
那宽大的木筏由几十根大木头连接而城,木筏上面用木板简单搭建一个小屋,除了供撑杆的人吃住,还栽了不少的山货,有皮毛、山参、木耳、蘑菇之类的。
楚浩见到梁毅说:“你比我心急,我正筹划着买船,你这已经到了,这样运木材,真是太好了。一路上可有关卡为难?”
“浩,多亏了你的兄弟赵将军,他给了咱们路条,签了他的名字,说他就管着这永济渠,让我们放心走,我们这头一趟,没敢多运,就整了这些来。”
“你们把木筏划进河湾停稳,我去找人来卸货。”
“怎么不走了,这河不是一直可以通到长安吗?”
“从这里转过去,就是黄河,黄河与运河不同,水流湍急,这样大的木筏,撑不过去,况且这么大的阵仗,进城太过麻烦。木材就在板渚上岸,等冬天黄河冰冻,再运到长安、洛阳去。”
“啊,还有这说法,看来哥哥我在山里呆久了,真是不知道城里这些道道。”
“先把木筏停好,咱们再作打算。”
“也好,那黄河俺在山东也见过,样子也没那么吓人。”
“黄河流经千里,河面宽就平缓、窄就湍急。”
“哈哈哈,这么说俺明白了。”
等他们把货物安顿好,梁毅随楚浩坐船去长安,经过三门峡,他才真正见识了黄河。
楚浩让李林拿出钱跟梁毅结账,梁毅都跳起来了:“兄弟,你让哥哥们给你备些山货,可没有说要跟哥哥们做买卖,兄弟们攒齐了,一腔热情给弟弟送来,哪儿有收钱的道理。”
楚浩完全被梁毅和高军参的兄弟义气所感动,不在提结账的事儿,带他们在长安和洛阳又玩了几日,挑了两匹马,送给高军参和梁毅,让杨卫州找关系买了两条小船,载着丝绸和生活必需品回辽东,楚浩给高军参写了一封共同长久贸易的信,亲自送梁毅他们到板渚。
辽东的皮子,楚浩让牧场把最好的存下来,其它的连同山货和木材都卖了好价钱。近年来,皇上、皇后在洛阳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这里修建了合璧宫、上阳宫,又整修了洛阳宫,耗用了大量木材。皇上来,官员和显贵们自然也跟着来,所以洛阳的房产和木材也跟着走俏。
江南的贸易长时间稳定、成熟,想要介入并不容易,倒是辽东动荡不安,大量的原生物资可以送来洛阳和长安。腊月,楚浩攒了很大的商队,准备去山后与父母团聚。
来来回回几次走辽东,楚浩因此建立了一连串的生意网络:他把辽东的特产,人参、鹿茸、兽皮等特产运回长安和洛阳,再从内地贩卖生活必需品到辽东。山大王高军参和梁益按照楚浩的意思山路上开设好几个驿站,走马帮,帮楚浩运送货物,再也不用冒死去抢。
商人很难做到像楚浩这样的长线生意,楚浩把当地商人一节一节连在一起,打通贯穿东西的商路,不光自己可以大笔盈利,也能极大促进辽东的繁荣,方便当地百姓。
因为黑水靺鞨和白水靺鞨余部不断侵扰,粟末靺鞨部落的边界吏部没有办法标明,只是按照高句丽官方的记载,说明是在白山一带的山地丛林部落聚集地,靺鞨本族人不会使用地图,楚浩就更不知道自己的封地到底有多大、在哪里。一年多了,户部才传他去受印。
楚浩满怀期待,沐浴更衣来到户部。户部授予了楚浩渤海县男封印,给了户口簿,楚浩低头一看,簿上只有二十三户!户部那个官员一边宣召,旁边值班的官员还低头偷偷抿嘴笑。
楚浩把户口簿拿给李林,李林也瞪大了眼睛:“县男好歹是个五品爵位,应食邑三百户,这二十三户,都没有一个村子大!”
“开始我还洋洋得意于县男这个爵位,也没指望有食邑,听说靺鞨人都住在土坑里,没有资产,渔猎为生,哪儿有税可收。可就是这样的人也被朝廷内迁,整个成了一片荒地,而且还不知道地儿有多大,只在海边画了一个圈。什么靺鞨县男,空头衔而已。好在半圆洞地域给了,我也别无所求了。”
“有军队驻扎,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守国门。”
“国门,高句丽境内叛乱不断,靺鞨还在高句丽北面,守什么门?”
“靺鞨北面还契丹和其余靺鞨部落啊。”
“你怎么知道?”
“地图,这不是你拿给我的地图吗?”
“这个他们倒是标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