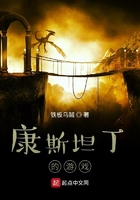东州,鲁国,王都汶阳。
王宫后宫之中,年迈发福的鲁王鲁嵩山,一袭金色华服,并未着冠,随意散着灰白稀疏的长发。踞坐榻上,昏昏欲睡。
乐师手中的丝竹之音渐低,似怕惊扰了鲁嵩山的睡意。殿前随音起舞的十八名舞女,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如彩蝶纷飞一般,不知疲累的舞动着羽裳。
宫中近侍小心的与鲁嵩山耳语。鲁嵩山睡眼惺忪,微微颔首。
乐师与舞女纷纷领命退去。
不多时,一名身着丞相官服的男子入殿。
此男子细目长眉,鼻高颧鼓。面白须重,长髯打理精细,垂于胸前。虽已年逾四十,却是一副三十上下的好相貌。
来者不是旁人,正是‘风流相’,谢石。
鲁嵩山微抬眼皮问道:
“相国何事啊?”
谢石行礼,满面忧色的回道:
“回大王,东燕、北燕议和已成。事有不妙啊!”
鲁嵩山眉头微蹙。
“如此说来,两路刺杀皆失手了?相国此前曾言,借北燕招安之计设伏,当能成事的?”
鲁国带甲近百万,因何不战,反去刺人?
谢石本无意行刺杀之事,只是鲁嵩山执意如此。故而借北燕招安山贼路匪之举,将计就计,刺杀燕北王。
老丈人瞒着女儿杀女婿,却要他谢石献计……
如今看来,茜熙公主献计,刺杀东方玄那路也未能得手。
谢石虽早知此事未必能成,但不知为何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茜熙公主此番回来的突兀,走的又蹊跷。鲁王言她忧心鲁国安危,特来献计刺杀东方玄。可于谢石眼中,甚为可疑。只是疏不间亲,不好与鲁王多言罢了。
你看,果不其然。他爱女献计刺杀东方玄未成便过往不提。我这被迫出谋划策的倒要被诘问了。
谢石只得行礼,叹气告罪道:
“大王恕罪,是臣所虑不周,以致事败。”
鲁嵩山心中略微可惜,却也不会真的去怪罪谢石。摆了摆手道: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相国无罪。”
谢石行礼谢过,忙又言道:
“大王,如今琅琊城、锁牢关已归东燕。疥癣之疾,或成肘腋之患。”
鲁嵩山略有不耐道:
“北燕的城池关卡为东燕得了,又与我鲁国有何干系?”
谢石面露焦急道:
“大王此言差矣!东燕、北燕两国接壤。背倚东海,向西而伐。进可齐攻,退可同守。
只须得三五年光景,便可用兵,与我鲁国,一争东州。”
鲁嵩山摇首笑道:
“呵呵!相国所虑的可是东燕、北燕暗中结盟?莫非相国不知那东方玄东牢山一把大火,烧死了北燕两万人马?”
东方玄如此行事,确令谢石百思不解。用两万人马来行苦肉计么?未免也太过了一些。莫说旁人不信,谢石自己都是不信的。
但谢石仍是坚信心中所想,强自言道:
“或是两国苦肉之计,也未可知。大王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鲁嵩山瞥了眼谢石,笑问道:
“好!若依相国之意,该当如何应对呢?”
谢石退后三步,跪倒跽坐,行天揖跽礼。朗声言道:
“臣请大王即刻下令,调西南诸郡之兵,步、骑、水军四十万,讨伐北燕!
北面渤海、河间、交河三郡待命。若东燕驰援北燕,则三郡兵马同出,夹击东燕!”
鲁嵩山微微正容,出言问道:
“大将军尉迟金若去西南统军,北方兵马,何人可为统领?卫将军皇甫川么?”
谢石跽坐挺身,正色言道:
“大将军尉迟金,卫将军皇甫川皆不可妄动。若东燕有变,北面还须二位将军领军。
正所谓举贤不避亲,西南四十万大军,当交由大都督谢樽统领。”
‘好一个举贤不避亲。你谢石于内统领群臣,你族弟谢樽于外再掌半国兵马。
颍川谢氏保我鲁家六百载封土不假,但这鲁国到底是我鲁家的,还是你谢家的?
我儿他日继位,岂非要受制于你等?’
鲁嵩山心中冷笑,面上也是如常笑道:
“呵呵!大都督之能本王如何不知?相国亦是治世能臣,天下名相。颍川谢氏,碧血丹心,王谢风流为天下人颂。”
鲁嵩山又作愁怨之色,继而言道:
“只是我儿茜熙方归北燕,本王此时兴兵讨伐,恐害我儿性命。不如待本王修书一封,召她归来,再行用兵之事。
相国若不放心,可先多撒耳目。察探东燕、北燕可有暗中备战之举。
待我儿茜熙归来,本王定依相国所言。交西南诸郡兵马与大都督,起步骑、水军四十万众,讨伐北燕。”
谢石闻听鲁嵩山此言,已明其意。也未再多谏言,起身行礼,欲要告退。
鲁嵩山忙笑言道:
“呵呵!相国日夜为国事操劳,本王不知该作何封赏。今新得离狐舞女十八人,已遣人送往相国府上。以增平日闲暇之趣。”
‘风流相’谢石,少时拜相,喜携歌妓舞女出游。行至形胜之地,便抚琴唱曲,与歌妓舞女一同载歌载舞。世人见他行事无忌,风流成性。故戏称其为‘风流相’。
谢石如何不知鲁嵩山此言何意,这是说他谢石今日已是封无可封,赏无可赏。颍川谢氏,亦是如此。
谢石再度行礼拜谢,躬身倒退出殿。
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
东州,鲁国,微山湖。
纵横东州七百里,九河疏瀹成一湖。
六月时节,微山湖上。
碧波含虚,万顷茫然,岚光作雾烟渺。远岫千峰百嶂,泛泛水中浮。菡萏待放,莲叶接天。古来渔樵之地。斜阳飞鹭,断霞鱼尾。波间钓舟,如游镜里。一阵湖风雾散,吹皱琉璃。
钓舟之上,一名六尺来高,肤色黢黑,獐头鼠目,颇为精壮的汉子正在持篙撑舟。
另一名身形修长,着一领月色锦袍。腰系玉带,足蹬月白锦靴的男子。则披头散发,毫无形象的瘫靠于舟中酒坛之中,好似睡去。
舟速不缓不疾,徐徐而进。横波纵浪俱无颠簸,一看便知这驾舟之人,当是水上行舟的渔家好手。
可偏偏此人又着甲挎刀,脚蹬短靴,一副军中将领打扮。
此人名李成,乃是鲁国微山李氏的虎子,‘醉都督’谢樽麾下的猛将,官拜六品横江中郎将。
微山李氏,以渔起家,后成巨贾。李氏一族,并无经学传家。遂斥巨资请来名师,教族中子弟,识文习武。
李成自是微山李氏此代,最为杰出的族中弟子。八岁感气而成,天资出众。能文能武,颇有心机。
微山李氏子弟,皆精于凫水驾舟。而能令李成亲自撑篙驾舟者,自然并非寻常之人。正是鲁国水军大都督,嗜酒如命的‘醉都督’,谢樽。
湖风轻软,水鸟争噪晚。
谢樽一手梳拢分开遮挡于前的乱发,露出细目长眉,鼻若悬梁,唇如涂脂的俊朗面容来。
一手随意指向前方,醉笑道:
“哈哈哈……呃……钓舟…且到湖心泊,临风把盏…更欲仙…哈哈哈……”
李成无奈,加了几分力道,钓舟破浪如飞。
谢樽两袖挥舞,迎风大笑道:
“哈哈哈……快划!快划!……哈哈哈哈哈……呃……哇啊!”——
李成急呼道:
“大都督!”
原来,谢樽一歪脑袋,似水龙吐水般,将吃食与酒水一道喷洒了出去,落在了舟侧湖中。
一时间,引来无数湖鱼争食。看的李成不知为何觉得有些反胃,感觉以后再也不想吃鱼炙了……
谢樽此时酒已半醒,便又挽过一壶酒来,仰首灌了一口。一炼内息,又如箭喷了出去。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白袍提酒江中走,不是谪仙是酒仙。古往今来,唯荒朝李颠与樽,方知这酒中乾坤!”
言罢,谢樽一边灌酒,一边以内息将口中之酒如箭射出,如那顽童也似。
湖鱼嗅到酒香,纷纷浮出水面游弋。
谢樽望了望湖面攒动的游鱼,又双手枕于头后仰躺在纷杂的酒坛之上,白皙的脸旁上仍留有几分酒晕,远眺群峰淡笑道:
“
戏水浅鳞知不知,
江山换手几浮沉?
王谢风流六百载,
犹报当年一饭恩。
”
李成一直不懂,以谢家于颍川之根基,于鲁国之声望。谢家缘何不反?
当真是为了六百年前,鲁家老祖赠了谢家老祖一餐饭食?
什么饭食他娘的如此金贵?令颍川谢氏代代英雄之辈甘为鲁家驱驰?如何当年不是他李家老祖来给上这餐饭食?
李成于舟上行礼,不忿言道:
“前番北燕伐鲁,大都督坐断沧江。救大将军性命,解汶阳之危。我水军上下全无封赏也便罢了!
今次大都督请命,趁东燕、北燕两国交战之际。领水军顺流而下,入沧江、击琅琊以制彭城。此等妙计,大王竟也弃之不用!”
谢樽瞥了一眼李成。
印堂狭窄人中短,獐头鼠目三白眼。天生反骨,小人之相。
若非惜其勇,且用其号令军中李氏子弟。早已设计取其性命,哪能留他至今。
谢樽佯醉笑道:
“哈哈!可是有怨?”
李成神色一变,转而憨笑道:
“呵呵!属下有何怨?属下是替大都督不平。大都督步战、骑战、水战皆能,缘何领不得大将军印?
大都督建功不赏,献谋不用。空有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可是全无半分气恼?”
谢樽起身立于舟头,回风水皱,白浪生花,临风笑道:
“呵呵!烦恼场空,身在清凉世界。营求念绝,方得自在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