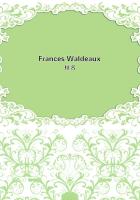林桡的消息一直没有从西北过来,姚殊只当战事吃紧,他无法抽出时间来写家信。
好在和薛老板商议开的成衣铺子已经着手在进行了,她的大部分精力便放在了生意上,经常跟裁缝师傅一聊便是大半日,身边也总带着阿思。
裁缝师傅中有三男七女,其中还有一对夫妻,最是喜爱小孩子。
这日一大早,姚殊带着阿思去检查裁缝师傅们做的衣裳,平日里对阿思关注最多的胡氏瞧见两人,笑着迎了上去:“阿思小姐又跟着东家来了?”
阿思站住了,乖乖打招呼道:“胡婶。”
胡氏生得面皮白净,手指也是从未做过粗活的纤细柔软,只牵起了阿思的手,看着姚殊,道:“东家,这几天我们做的衣裳都在屋里了。您进去看,我带着阿思小姐去厢房。”
阿思黑玉一般的双眼一下子亮了:“胡婶上次说给我做裙子,已经做出来了吗?”
胡婶笑了,摸摸阿思的头,柔声道:“做出来了,颜色和款式都好,阿思小姐一定喜欢。”
小姑娘欢呼一声,看向了母亲,眼神里写满了希冀。
姚殊自然不会阻碍阿思有自己喜爱和亲近之人,只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自己去了正屋,瞧她几日前吩咐了的衣裳是否完成。
等胡氏牵着阿思的手,把她带回正屋时,姚殊正在低声和几个裁缝师傅说着需要修改的小细节。
小姑娘清脆悦耳的声音带着笑意响起:“阿娘!快看胡婶给我做的裙子,好不好看?”
姚殊抬眼,便见本就很白的阿思穿了一身白色和鹅黄相间的衣裙,愈发现得她生得白白嫩嫩。
那衣裙正合阿思的身,裙摆既不因为过长显得臃肿,也不因为过短而失了庄重;腰间用鹅黄色的带子勾勒出小姑娘的腰身,再加上几根同色的丝带垂下来,行走间尽显活泼可爱。
姚殊笑着道:“好看,哪里来的小蝴蝶成了精?快让阿娘看看,许是偷吃了迎春花的蜜,这才化成了人形!”
一时间,屋内众人都笑了起来。
阿思这一身衣裳着实漂亮,尤其符合她的气质,可见胡氏是用了心的。
小姑娘脆生生道:“胡婶说了,这身衣裳她还能再做一套纯白色的,下次去白姐姐家中我要带上,跟她穿同样的式样!”
姚殊眉眼间尽是温柔之意,笑着应了阿思的话,真心实意道:“辛苦胡姐姐了。还有大家,做出来的衣裳也当真不负众位巧手知名,这几日赶工确实不容易,咱们今日不如去酒楼用饭,也好松快松快?”
花费心力做出来的衣裳被东家称赞,几个裁缝师傅心中也十分舒坦,又见她真心相邀,众人便齐声说好。
姚殊这边欣欣向荣,杜蘅那里,过的就不那么舒坦了。
锦绣布庄经过一次流言的洗礼,再不敢把带有异香的布料卖出去,从此失了这么一个噱头。
除此之外,从布料的质量、花样的多寡,再到布庄服务的质量,姚记布庄全都胜过一条街外的锦绣布庄。
客人自然不会舍了好的,偏偏跑去名声不好的锦绣布庄去选料子,这一仗还未开始打,杜蘅便已经失了先机。
无奈之下,锦绣布庄只能通过压低价格,来赢取客人了。
可偏偏就连降价,姚殊都不肯让他们如意——
这一日,锦绣布庄的掌柜手里捧着账本,一脸为难地向杜蘅回禀:“东家,咱们的布料已经降到最低了,您看这……”
杜蘅这几日时不时来一趟布庄,今日也不例外。
她一大早便带了小红过来,询问这些天布料卖出去的情况,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却被愁眉苦脸的掌柜拦在了门口。
杜蘅心中不悦,只觉对方过于失礼,可转念一想,一个小小布庄的掌柜,能懂什么礼仪?终归不过是一个粗鄙之人而已。
铺子里照例没有什么客人,杜蘅蒙着面纱,一双冷目扫了一眼柜台旁边闲着的伙计,对掌柜的道:“有什么事情,进去说。”
掌柜亦步亦趋跟着杜蘅进了厢房,许是熬了不少夜,精神实在不济,连茶水也忘了给杜蘅上。
左右她也不喝铺子里的劣茶,倒了又有什么用?
杜蘅坐定了,声线清冷地问:“这两日生意如何?可曾把存货卖出去了?”
掌柜的捧着账本,一五一十道:“咱们把价格压低三成之后,果然卖出去不少。只是那些有香味的布料,还是无人问津……”
杜蘅心中升起些暗火,皱眉道:“价格不能再降了吗?”
掌柜的苦笑道:“当日东家说要在布料上染香,咱们为着这个留香久一条,便花了大把的银两。一匹布料算下来,成本要比寻常布料高了一倍还不止,现下这个价钱,已经是赔本在卖了。”
杜蘅摇头,淡声道:“那就是不够,再降些。”
掌柜的满脑子都是库房里堆积如山的布料,从前若是卖出去了,他只会高兴到浑身舒畅;可如今赔着本卖,这一屋子的布料,每卖出一匹便像一把小刀从他身上剜下来一小块肉,着实让人难受得紧。
听见东家说还要降,掌柜的险些要晕过去:“东家!如今风气不好,咱们就算把这些布卖到寻常布料的价格,也未必有人肯买啊!”
若掌柜的只是管着替杜蘅办事,铺子里的盈亏他自然不会过于放在心上,顶多是干砸了被东家辞掉。
可当日他见杜蘅花大力气给布料染上香味,而京城中贵人也都非常吃这一套,不由鬼迷心窍,跟风投了一大笔钱到布庄里。
如今库房里那些卖不出去的货,有两成是他自己的积蓄囤下的布料,如何能说赔本就赔本?
掌柜的只好苦口婆心地劝杜蘅:“东家,这个价,实在是不能再降了。满屋子的料子都赔钱卖,咱们铺子还怎么维持?”
谁料杜蘅却不买账,只淡淡道:“赔钱又如何?只要价格压的足够低,总有人买回家去。届时布料制成衣裳穿在身上,流言不攻自破。”
掌柜的快要哭了,杜蘅赔得起,可他赔不起啊!
他满脸倦容,眼底还带着彻夜难眠的红血丝,只忍着脾气,好声好气地同杜蘅商量:“东家,如今流言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哪里还用花这么大代价去证明?不若再等等,过几个月,人们都忘了这事,咱们的布料自然还能卖的出去。”
掌柜的为了这事已经愁了不是一日两日,办法也想了无数,如今便一股脑说了出来:“实在不行,咱们还能把有香的布运到南方去卖,便是不开铺子,左右也不过是支个摊子的事……”
杜蘅不为所动,仿佛掌柜的为之头痛了几宿的布庄和料子,都与她无关似的。
她只摇头道:“我说卖掉,你只管压价卖便是。”
掌柜的说的口都干了,却见东家还是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险些被气了个倒仰。
杜蘅选择亏着本把布料卖掉,自然有她的考虑。除了攻破流言之外,这也是赢得客人驻足最快捷有效的手段。
至于亏本不亏本,便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