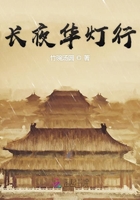这一回,郑安是真的愣住了。
他细细回味了一下林桡的话,怎么都觉得不像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
林桡习惯用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若是平时,他也不会喜欢麻烦别人。
今日反常的耐心,还有对谢谦颇为熟悉的口吻,都有些让人费解。
郑安原是坐着的,不由站起了身,绕着林桡转了一圈,看了一眼,又一眼,才后知后觉道:“林兄弟,你今天这模样,有点不对啊。”
林桡回看过去,没有吭声。
郑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平日里可是一句废话都不肯多说的,今日怎么说了这么多?”
男人淡淡道:“我今日说的,有一句废话不成?”
“倒也不是……”郑安想了想,接着道:“平日你也不会听我说这么多废话呀!”
林桡没有理他。
郑安喋喋不休问起来:“林兄弟今日心情不错?说起来,昨日那个谢大人怎么还跟你一起回了家?他什么来路?”
见林桡还是没有什么动静,郑安径自摸着下巴说了起来:“而且往日你是最早一个到巡捕府的,今日晚了那么多,看上去心情又不错的样子,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好事。”
见他越说越不像话,林桡站起了身,懒得理会。
难得瞧见林桡脸上不那么冷淡的神色,郑安倍感新奇,缠磨了一会儿,见他还是没什么反应,终于一屁股坐了下来:“算了算了,你这闷油瓶的性子,哪里能指望你多说几句。中午一起去吃饭?”
林桡可算给了反应,却是摇头拒绝:“我在等人,你先去吧。”
郑安被噎了一下。
他可算明白为什么今天林桡耐心这么好,一直坐着听他抱怨着抱怨那,感情人家不是在听他说话,而是要等人!
郑安一腔感动瞬间变了味,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表情,转身就要走。
到了门前,竟迎面碰见谢谦,他抱拳道:“谢大人。午饭时候了,还不去用饭?不如同去——”
他邀谢谦也是好意,巡捕大人事忙,未必能照看得好客人,郑安怕谢谦碍于面子吃不好饭,这才想要拉着他一起。
可还没等郑安说完,谢谦淡淡道:“抱歉,已有约在身。”
他脸上的表情和林桡平日里冷淡的模样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林桡方才气人的模样。
郑安深深提了一口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呼出去,差点没喘过气来。
谢谦径直进了会客厅,和林桡淡淡地招呼了一声,两人没有多说,默契地一起走了出去。
郑安一边摇头,一边朝府外走去,心里想着——
谁说性子冷淡的人就不善交际的,他分明瞧着,两个一样不爱说话的人反倒能走到一处去。
倒是他……中午一个人孤零零的,随便吃碗稀粥得了。
午间谢谦和林桡吃了一顿便饭。
如今春闱在即,翰林院事务繁忙,谢谦不能久待,便提出了告辞。
对于谢谦,林桡心中始终有些陌生感,似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听他说要走,林桡只道:“何时启程?”
谢谦答道:“明日一早。”
林桡嘴上虽未唤他舅舅,心里早认了谢谦,便开口道:“阿殊和三宝,你都还未见到。”
谢谦也就只有在最开始见到林桡时,心绪有颇大的起伏,现下早已恢复了他平时的模样。
不喜麻烦、不爱交际。
闻言,谢谦淡淡道:“替我问声好便是。”
他虽辈分比林桡高上一辈,可看上去年纪不大,倒像是林桡的兄长。
两人的气质相像极了,只是谢谦的冷更像是万花不能入眼,林桡的冷偏向于不怒自威。
林桡有时候在想,若自己身边没有姚殊相伴,会不会也同谢谦一般,冷淡孤寂,仿佛与世隔绝的一处幽潭,漆黑幽深不见底,也没有一点波澜。
他不强求谢谦,低声道:“我安排人送你回去。”
两人又商量了一下明日的行程,如今巡捕府事忙,谢谦不欲过多麻烦众人,只道:“我来时如何来,去时便如何去。不必安排人送。”
谢谦来时,不过一辆马车、一个车夫,林桡却是不能让他这般回去的。
他作主加了两个护卫还有一个负责起居的小厮,谢谦没有再推辞。
最后,安置好一切,林桡还是多问了一句:“当真不见见阿殊他们?”
他私心是希望谢谦和姚殊见面的。
许是昨日姚殊的开解,让他解开了心结,在林桡看来,谢谦是他关于母亲所有想象的媒介——是他仅有的母家亲人了。
而于谢谦而言,林桡一家,也是他在世上仅有的血脉。有谁能拒绝得了血缘至亲?更何况,谢谦无儿无女,没有成家,孤身一人也确实十分寂寞。
可谢谦却仍坚持,摇头道:“不必麻烦。”
林桡没有再劝。
他们从酒楼出来,径直回了巡捕府。两人并肩走在路上,脸上的神情倒也如出一辙。
巡防大营新到的马匹还要林桡亲自去检查,而且训练兵士一事也该着手进行了,他把谢谦送回巡捕府,骑马去了城郊。
第二日一大早,谢谦没等林桡相送,便动身回了京城。
郑安还惊讶了一番,有些看不懂:“这谢大人也当真是来去匆匆。我以为,他与林兄弟关系不错,至少还要等你送一送。”
林桡摇头:“他是这样的性子。”
只这一句,没有多说,谢谦也不是在乎别人看法的人。
或许郑安等人不了解谢谦,可林桡与他相处不过短短一日,却打心眼里理解他的做法。
血缘与他,一如功名、官职,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否则他不会连成亲的念头都没有。
也仅仅因为林桡是他胞姐的孩子,是谢谦多年的愧疚和念想,他才会走这么一遭,对林桡投入关注。
至于其他,就没有再多了。
好在林桡能体会这种心情,是以不觉得他冷漠,若换个旁人,恐怕也理解不了谢谦的古怪脾气。
……
谢谦走后,林桡过了几日便收到他的来信。
信上倒是谢谦一贯的风格,简洁明了,没有什么废话,说明了京中如今国子监的情况,让他和姚殊尽快商量,是否要送阿志进京。
等春闱过后,便是国子监招生的时候。
京城中多少贵族子弟也巴望着进国子监读书,阿志若想进,该早些准备考校了。
等下午林桡到家,把信给姚殊看了,也同她说了之前谢谦有意让阿志去国子监读书之事。
到了晚饭时分,恰好孩子们也都在跟前,姚殊便问阿志:“你怎么想?想去么?”
阿志没有说想不想,而是认真道:“谢爷爷和我说了话,我觉得,京城离家比较近。”
一旁阿思懵懵懂懂,却知道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姚殊道:“哥哥去京城,京城!”
姚殊点点头,又笑着揉了揉阿思的脑袋,一家人开始吃饭,也没有就这个话题多说什么。
到了晚间,孩子们都睡下了,姚殊和林桡商量道:“我方才好好想了想,若是能去国子监,自然要比寻常的书院好上许多。只是……”
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
林桡抬头,疑问地看向姚殊。
只听姚殊道:“谢大人那里,是什么态度?”
她虽是在这样问,林桡却明白姚殊真正的顾虑。
谢谦性子冷淡,又跟阿志隔着辈,姚殊担心他不能真的对孩子用心。
林桡温声道:“不用担心,他是个不爱麻烦的人,既然这么说了,自是真心想让阿志去的。”
姚殊轻轻地“嗯”了一声。
她相信林桡的判断,心里也觉得,至少京城要比苏州近上许多,到时候若阿志有什么事情,离得近总归是方便许多的。
姚殊把手里的针线放了放,起身把油灯拨亮了些。
如今林桡对姚殊的心情感知十分灵敏,瞧见她的模样,便知道她心里还是有事。
男人问:“怎么还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姚殊重新拿起针线。阿志开春后个子长高了不少,脚也大了些。
姚殊不常给孩子们做衣裳,但偶尔纳个鞋底,还是常做的。
她手里的针一边穿插,一边低声道:“京城是天子脚下,国子监又多官家子弟,阿志去了,会不会受欺负?”
这个问题,怕是只有母亲才会考虑到。
林桡道:“这些问题,阿志总要面对的。即便今日不曾进京,他日若科举高中,难不成他还能不进京了?届时面对的是同僚,有相处好的,自然便有政见不合的,他又该如何处理?”
姚殊贝齿轻咬下唇,不吭声了。
她有什么事情拿不准主意时,便爱咬嘴唇。
林桡从前不觉得,昨日后,便舍不得她咬了。
男人把手覆在了她的手上,止住了她手里针线继续的动作,看着姚殊的眼睛安抚道:“别担心了,阿志总要长大的。”
姚殊回望他,脸上露出些不舍的神情:“可那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了。我们不能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多陪陪他么?”
林桡摸了摸姚殊的头发,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若是舅舅瞧见你的模样,一定会喜欢你的。”
姚殊愣了愣,笑道:“这是什么话?”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称谢谦舅舅,也是他第一次,唤出那个人的名字:“虽我从未见过母亲,可我想,她应该跟你一样温柔吧。”
男人神色柔软下来,接着道:“我听舅舅说,他小时候不爱读经史子集,偏偏喜欢看些杂书……常常被夫子逮住打手心。那个时候,母亲一直都护着他。我想,若舅舅看见你对阿志的模样,定会想起母亲。”
姚殊的眼神也更加柔和,轻声道:“做姐姐的,自然会护着弟弟。阿志现在还小,我也会护着他。”
林桡点点头。
姚殊又开始做起了针线。油灯很亮,倒也不觉得费眼。
只是姚殊想着阿志这个年纪爱跑爱跳,鞋子总是鞋底坏的快些,便把鞋底纳得厚厚的,针有些难扎。
林桡就这样静静地瞧着她做事,倒也不觉得无聊,反而因为能和她多相处感到平静和安然。
两人互不打扰过了半晌,却听林桡冷不丁说了一句:“你若放心不下阿志,我们也可以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