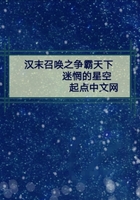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2016年第5期
近年来,儒家文化的复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海外“孔子学院”建设、政府主持祭孔、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等官方行为以及民间儒学研究团体、会议、杂志等的发展以及儒学的普及,都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儒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大陆儒学的研究者也越来越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建设联系在一起,小到计划生育等公共政策,大到国家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均能发声,在产生一定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论。本文仅就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一年有影响的争论进行简单梳理。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
2015年1月23日,台湾儒家学者李明辉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发表了“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观点,[1]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两岸诸多学者如蒋庆、陈明、李存山、杨儒宾、赖锡三、干春松、姚中秋、曾亦、唐文明、白彤东、黄玉顺、方旭东、陈贇等均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这一争论范围广泛,影响较大,被儒家网、中国儒教网、儒学联合论坛共同推选为儒学研究年度十大热点之首。
这些争论有着诸多新意,但焦点仍然汇聚在港台“心性儒学”与大陆“政治儒学”的基本分歧上。在越来越强烈的现实关怀取向的引导下,大陆儒学的研究者更多重视儒学治国、平天下的内涵:不但关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更多地关怀政治,直接切入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体现在儒家宪政等重大政治主题上。
这种强烈现实关怀不仅拉开了大陆儒学研究与港台心性儒学的距离;而且,即使是与港台心性儒学更接近的一面,大陆儒学的研究者也更多强调对精神和道德生活的教化,试图将儒家的道德教化落实到现实社会当中,形成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主流的社会,甚至是以儒家理念为核心来塑造天下秩序观。
李明辉对大陆儒学研究者的批评集中在政治儒学层面,这也是这一批评能够激起如此热烈争论的一个原因。政治儒学被认为是现代大陆新儒家的标志性贡献。然而,在李明辉看来,这一贡献基本是空想,公羊家的那套讲法都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认为,君主制只适用于乱世、升平世,而太平世则适用选贤举能、天下为公的大同制度。然而,李明辉认为,这里提到的大同制度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蒋庆设计的“儒教宪政”只是一种乌托邦。[2]对李明辉的观点,大陆儒学的研究者给予回应,重申了政治儒学的基本观点和现实依据。
在蒋庆看来,李明辉的观点无疑与中国历史相违,而且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蒋庆随即发表了一个访谈,更加全面地阐释了大陆政治儒学与港台心性儒学的区别,并且再一次重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在儒学传统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是不同时代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3]曾亦也认为,台湾学者对大陆儒家这几年的发展和努力实在“缺乏了解”,李明辉的言论“厚诬古人……有些无知”。[4]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大陆儒家都认为政治儒学是最重要的。比如,唐文明认为,以教化来定位儒家传统是最恰当的,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都非常重要,而大陆思想界关于儒学复兴的讨论,“政治气味太浓了……存在很大的误区”。儒教最好的东西是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本质上是超越政治的。唐文明对左右两派均不满,认为在关于现代中国的叙事框架中,有启蒙的主体性,有革命的主体性,唯独没有教化的主体性。我们应当在认真对待启蒙和革命主题的同时,将教化的主题呈现出来,从而“以古持今,以中化西”。[5]
从教化的意义出发,唐文明把儒学定位在“儒教”。在唐文明看来,中国古代儒教与国家制度的联结与互相渗透,其实就是一种巧妙的国教制度。唐文明以“定于民、定于一、定于孔”来描述中国“儒教”的命运。前两个环节都是针对儒教展开的,启蒙主体性的确立主要是启传统儒教的蒙,革命主体性的确立主要是革传统儒教的命。第三个环节,即“定于孔”,这是教化的回归,一个还没有完成的环节。为此,他特别强调了儒教的重要性,认为“儒教作为国族教化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因而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本”[6]。然而,将儒家复兴寄托于宗教化的手段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宋大琦认为,把儒家复兴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宗教化,就会面临“两难困境”。要想使儒家成为主流文化,“普通宗教化不行,国教化也不行,而且儒家也没有基督教佛教等义理和组织形式”。他还批评了康晓光等人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努力。[7]
儒学内部的分歧只是这些争论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分歧还来源于外部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批评上。这其中包括了邓晓芒、易中天、钱刚、贺卫方、江平等知名学者。他们或多或少地从不同的方面对儒家思想,包括广义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评。邓晓芒是其中影响较大、理论比较系统的一位了,2015年更是持续发力,批判儒学。对国内一批儒学研究者,邓晓芒直截了当地称其“缺乏现实感……显得很无知”;对于海外儒学研究者,邓晓芒虽报以理解,但认为是故土情节“影响理性判断”[8]。
对儒家的批判更多从西学,或是现代价值的角度展开。在邓晓芒看来,即使是那些几乎得到普遍认同的儒家理念,比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如果没有经过具体批判,也很可能成为“鱼目混珠的赝品”。邓晓芒更是将儒家思想归结为“伪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的理论,但最终实现出来,却是“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事实上,邓晓芒的主张是一种融合论,也就是他从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双重标准论”。中国“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相反,西方则有必要批判自己的传统,转而引入东方或中国文化。”[9]
儒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
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评论,并不仅仅限于对儒家自身的理解,还在于人们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西方价值。方朝晖与李存山就“三纲”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谱系中,儒家文化与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能否兼容,与自由主义如何对话,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儒家的定位,还关系到儒家传统的转化与创新,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
大陆“新儒家”从产生那天起,就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争论。最早的大陆“新儒家”就是因为凸显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而被认为是贬义词。但后来,陈明等人逐渐接受了原本带有贬义的大陆“新儒家”一词,而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也逐渐壮大起来,包括张祥龙的“后现代主义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也被列入其中。随着大陆“新儒家”阵营的不断扩大,其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各种争论也逐渐浮出水面,甚至是引人注目。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对话仍然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事实上,儒家学者很早就做过沟通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努力。比如,熊十力先生1956年出版的《原儒》。当代的儒学研究者蒋庆、陈新华等人也都曾经涉及这个主题。总的来讲,多数儒学研究者还是得出了共识性的一致结论,儒家与社会主义有亲和性。至少,儒家不必拒绝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儒家理想实践应该结合社会主义。当然,也有儒家学者认为应该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正统。
更可行的一个切入路径可能在儒家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和合关系的建构上。2015年7月31日,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接受中纪委网站专访,提出“执政党要中国化,要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1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就在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条就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所本。2015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29次集体学习,陈来教授就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问题进行了讲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既是一套完整、独立的体系,同时,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价值观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优秀价值。事实上,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友善等观念完全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传统资源,还有一些价值观,比如民主、法治的思想,也是可以从传统儒家的民本和礼治的现代转换中获得支持的。
拒斥某些西方价值,尤其是自由主义,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是大陆部分儒学研究者的一个特征,尽管他们拒斥的内容并不相同。比较激进的儒学研究者拒斥自由主义,主张保持儒家的传统个性,反对自由主义的一切要素。比较温和的儒学研究者则主张与自由主义对话,吸收自由主义的合理要素。然而,他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一致,那就是否认自由主义成为正统。比如,陈贇认为,自由主义“不堪重负”,无法承担“文明体”的正面架构,将自由主义放大为文明体本身是自由主义者常有的“一个愿景,甚至幻觉”。
儒学的开放性也是儒学在各种意识形态争论中的一个基本态度,学者争论不一。在李明辉看来,大陆新儒家虽然不愿意接受“大国沙文主义者”的名号,更愿意以“文化民族主义者”自居;但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在批评儒学封闭观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学的开放性问题,甚至提出了儒家全球化的观点。在王学典看来,儒学要想复兴,必须走向世界,因为人类现在是在同一个地球村内生活,不是在一个个封闭的帝国内生活。在这里,包括了儒学与个人主义、社群主义、集体主义等的对话,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对话就是,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他指出,“儒家学说要想获得世界性的地位,它除了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王学典认为,“儒学的生命力能不能最终拯救中国尤其要体现在另一点上:儒学要想主流化,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诸种意识形态见仁见智,歧义丛生,甚至缺少共同的底线。这在陈贇看来是一个遗憾。他试图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作为争论的出发点,即承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此之外,他强调了一个作为文明体的“中国”,认为当今世界的大国竞争,并不仅仅是政治体的国家之争,同时更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竞争,甚至后者更为根本,而“文明论”上的“爱国主义”要求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予以肯认,这应该构成左、右与保守主义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共同出发点。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恩格斯合力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研究”的支持)
注释
[1]李明辉:“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思想》,2015年第29期。
[2]李明辉:“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思想》,2015年第29期。
[3]蒋庆:“政治儒学并非乌托邦”,中国当代儒学网,
[4]曾亦:“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天涯社区,
[5]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1期。
[6]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1期。
[7]宋大琦,杨万江,洪范:“儒学的机遇与方向——大陆新儒家评议”,《当代儒学》第7辑,第169页。
[8]邓晓芒:“我与儒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9]邓晓芒:“我与儒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10]“著名哲学家陈来:作为中华文化忠实传承者,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发展责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