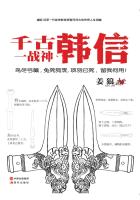陈布雷不断地抽烟,待烟蒂灼痛了他的手指,掷掉再吸,然后拿着香烟发怔。官邸如此肃静,但隐约的电话声,狼犬的轻吠声,却为平静的官邸增添了莫大的紧张和不安。陈布雷实在想看一眼他的子女、他的妻子,他辛酸地啜泣着,低呼着孩子们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他原谅孩子们的出走,同情孩子们的出走。“时代是前进的,我们是落伍了,我们在老百姓面前有罪!”陈布雷悲不自胜,“孩子啊,你们来看看我吧!我是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想念你们!你们在向新的世纪跃进,我却在找寻坟墓之门!孩子们啊!我的头痛欲裂,心如刀割,我……”
但陈布雷又立刻醒悟到:孩子们是不可能再回来找他了。别提多年来“官邸一入深似海,从此父子陌路人”,即使儿女来了,等待他们的也是监狱,这样会面到底是为了爱孩子,还是害孩子?陈布雷的心里越来越乱了。
陈布雷开始镇静下来,他感到今晚是非死不可!他躺在床上,想起明天他太太获得噩耗,该如何悲伤!******得知此事,他心头的真正感情是什么?陈布雷深深地向他的妻子忏悔,因为他名义上的妻子早已疏远了,事实上他已变成******的婢仆。
想着妻子,陈布雷又联想到著名四川诗人乔大壮在苏州投河的悲剧。乔曾工作于监察院,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妻子逝世而终身不娶,但房中陈设,床上双枕,一如妻子在世时。他长子参加空军,在抗战时有战功,次子参加人民解放军且已攻下开封,如今他长子奉命轰炸开封。风闻次子已牺牲在南京的炸弹下,乔大壮痛苦极了。他对新的力量没有新的认识,对旧的一切深恶痛绝,就在这彷徨无计、不可自拔的情况下,乔大壮在暑假中离台去沪,转赴苏州,纵酒吟诗,痛哭流涕,纵身护城河中,以毁灭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切。
“这是悲剧,”陈布雷深深叹息,“今晚上我所走的,就是乔大壮的老路了。”他开始摊开信纸,拿起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墨,却又写不下去,鼻子一酸,泪下如雨。
就在泪水已干的信纸上,陈布雷开始给他妻子写遗书。夫妻一场,到头来却如此永别,陈布雷大恸,却又不敢哭出声来,怕遭人怀疑。他以极大的气力忍住哭泣,写完给妻子的遗书又写给儿女们的遗书,这几封信写得更为吃力,因为陈布雷已经原谅,并且同情他的孩子“叛变”行为了,但此意在信上又怎能说得?
已经深夜3点钟了,万籁俱寂,夜风劲厉,忽地有脚步声传来,陈布雷倾耳细听,三几个人的脚步声停留在他的窗前,他一怔,接着******低沉的声音在问:“陈主任还没睡吗?”陈布雷忙把大叠遗书往卷宗内一塞,藏起安眠药片,仓促启门道:“先生怎么还没休息?”
******入室往太师椅上一坐,苦笑反问道:“你说我怎么睡得着?你为什么不睡?”
陈布雷支吾以对:“我睡在床上同坐在椅子上一样,也睡不着,已经好久好久了。”
“好久好久了。”******怜悯地问,“刚才你到我那儿来,好像意犹未尽,是吗?”
陈布雷强笑道:“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请原谅。”说罢落泪。
******叹道:“你要说就说吧。”他推卸责任道,“我不是不能容人的人,只是大家瞒着我,又怕我太辛苦,好多事情不向我报告……”
陈布雷凭着最后一点勇气插嘴道:“先生,满朝文武都对不起你,其中经过如何?谁负的责任要多些?今天不必谈了,今天布雷斗胆上言,立老果老同辞修之间的摩擦,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再发展下去,更不能想象。”******其实知道,却把脸一沉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陈布雷明知又是那一套,说:“我一定把整个事情经过、现况及其发展写下来,报告先生。”
“那很好。”
“还有,”陈布雷嗫嚅开言道,“白天布雷曾报告先生,希望纬国能到国外留学,现在我想做补充,”陈布雷把心一横,说:“希望先生也出国休息一阵。”
******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了,强自镇静,声音颤抖:“哦,你也这样想呐!”
“先生,”陈布雷感到此言一出,轻松多了,“人家这样想,同我的出发点不一样。人家的动机何在,先生明察,布雷的建议,则纯粹为了先生。先生犯不着再为这个局面……”******蓦地起立,强笑道:“多谢你的建议,不必再说下去了,你把关于立夫果夫与辞修之间的摩擦,详详细细写给我看,我们再商定。”说罢怏怏而去。
陈布雷目送到门口,望着******的背影叹息。摇摇摆摆回房、锁门、抽烟、喝茶、摊纸、执笔,他苦笑一声,伏案疾书……
听远郊鸡啼,抽香烟半罐,陈布雷不知涕泪之何从,两眼模糊。稍停,极度疲乏的陈布雷从文件中,抽出早已写好的《三陈摩擦情况》重读一遍,略加增删,签了个名,抬头一望,见东方已显鱼肚白。
******官邸中侍卫换班,脚步清晰,陈布雷知道天快亮了,他勉强下得床来,颤巍巍抓住那个安眠药瓶,倒茶、润喉、启盖、吞药、喝水、再吞、喝水……
“完了,”陈布雷喃喃地说,“完了!”他摸索到椅子上,将几封遗书分别封好,再在致******第一封遗书文尾加了行“夫人前并致敬意”,眼睛却停滞于“部属布雷负罪谨上”那行字上,微微摇头,不断苦笑。再按照老习惯将文稿再读一遍,做了极小的改动,然后将文房四宝,几椅什物一一放妥,往床上一躺,静候死神光临。
窗外的人语,树影,风声,室内的灯光,书画,挂钟,都模糊不可辨了。陈布雷已陷入天旋地转、神志昏迷的景况之中。他痛苦地、喃喃地呼唤着他妻子儿女的名字,在朝阳初升时停止了最后一口呼吸。
陈布雷的心脏停摆了,挂钟仍然“滴答滴答”地摇摆着。
******闻讯愕然。
他感到连陈布雷都自杀死去,证明局势不但不可为,而且危在旦夕,无法自拔了。******失神地以手支颐,沉默良久,汗涔涔下,不发一言。
宋美龄在看了陈布雷那封“夫人前并致敬意”的遗书后,连呼“国失栋梁!”并吟出如下八句诗来,便是:
文星陨落天欲摧,
四海悲歌动地哀。
不合此时撒手去,
神州尚有未消灾。
而今直失先生面,
终古难忘后死心。
风雨鸡鸣增百感,
潸潸泪下满衣襟。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在报纸以外风传,人们并不是因为陈布雷的身份重要才奔走相告,而是因为象征局势的重大变化即将来到,陈布雷作为那根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已经给热火朝天的高温爆裂了。
陈布雷之死,给徐州之战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伯韬阵亡,淮海惨败
陈布雷死后不几天,******即使灌肚子两杯白兰地也无法入梦了:
黄伯韬阵亡的消息传来,淮海大战第一阶段自11月6日至22日16天中,******18个整师178万余人遭歼灭,17座县城失去,铁路500余公里落入解放军掌握之中。而更甚者,******还有48个师遭对方分割为南北两半!
这一仗是够惨的。
******见人不言语,动辄发脾气。他几乎连自己的影子都得戒备,都要责骂,平白无故,坐在沙发里也会蓦地蹦起,有些神经质,连侍卫也人人自危,担心大祸临头。
下午,******照例举行官邸会议,文武大臣一旁侍候,只能报告当前危机,对明天的事情应该怎样对付,个个束手无策。倒是有几个立委发牢骚触怒了他,******拍桌打凳,破口大骂:
“直到今日你们还要不满政府,简直毫无人性!这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马上得之,马上失之,你们不想待下去,可以远走高飞,没有人强迫你留在这里!”
众人无声。
半晌,******再骂道:“娘希匹!大家不好好地干,我会变成战犯,你们要变成白俄!你们以为共产党会让你们活下去吗?共产共妻你们受得了才怪!”他把脸一沉,“还不好好地反共!”
……
三句话离不开骂娘,整个会在骂娘声中结束。
以酒解愁。会后,******关门饮酒。
他眼睛血红,抓起白兰地瓶子便倒,仰着脖子干了半杯。
宋美龄在门外见状折回,不拟入室。
******又喝了半杯。
后来,他就索性不再用杯了,抓起了白兰地瓶子朝天吹起了“喇叭”,咕噜噜一阵,像老牛饮水似的。继而,他走到收音机前,也不关机,只往地下一推,一阵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之后,他自己也倒在沙发上了。
侍卫官们仍不敢入内,宋美龄闻声赶至,见蒋无恙,才放下心来抱怨道:“委座,这又何必呢!”边说边把手一招,要侍卫“打扫战场”,******刚才“战胜”了对方的广播。
******声色俱厉道:“你不要管……”
宋美龄按住一肚子火,佯笑道:“你喝醉啦!”接着要他回房去,低声劝道,“别让他们看笑话。”
******火儿更大,嗓门又哑又尖:“什么笑话!什么笑话!娘希匹,这是什么局势,还说风凉话!”宋美龄一听有气,扭头就走道:“人家有要紧事,华盛顿有电报来,你还装疯卖傻撒赖!”
******一听酒醒了一大半。
宋美龄示意侍卫退出,把门关好,狠狠地说:“电报说形势不好。”
“怎么不好法?”
“说美国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援助南京政府。”
“不会的!”******摆了摆手,“我知道不会的。”
“你听我说完!”宋美龄蹬脚道,“影响太大,别以为不会的不会的!电报说他们指出两党政策以美国纳税人的金钱支持南京,美国人民不能赞成……”
“我烦得很!”******道,“对于美国,我断定他非援助我们不可!布立特看过我两次,司徒雷登决定不回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留在这里,巴大维飞东京同麦克阿瑟商量,共和党参议员马伦昨天见我以后又飞回上海,这些事情都说明了……”
宋美龄泼他一头冷水道:“你上午还在生气,说美国人要你下野休息,出国躲避,现在你又满不在乎,你根据什么又乐观起来?”
“乐观?”******指指收音机那个空位置,“我还能乐观?娘希匹,我根据美国人非要我下台不可!我明白他们在东找西找,希望找个人来顶我,李德邻这家伙这几天又抖起来啦!可是我不怕,由他们搞去吧!我就是不下台!我就是不走开!我绝不把兵权交出来!美国人能咬掉我……”
宋美龄道:“好好,你有办法,你有办法,可是眼看南京危急,大局严重,你为什么不到美国走一趟?”
“我,我到美国?”******惨笑道,“夫人,你怎么也来一套妇人之言!我这个时候去美国,脸上还有光彩吗?万一我到美国,他们却想尽方法,软硬齐下,不准我回来,我又怎么办?你这种说法,——嘿!”
“嘿什么!我还不是为你好!”
“为我好?”******厉声说,“当初陈布雷也同我这样说过,我一听就有气!如果这个主意是旁人出的,”******大喊:“我就对他不客气!”
宋美龄蹬脚道:“你对我不客气?好!来吧!看你怎样对我不客气!”说罢双手往腰间一叉,杏眼圆睁,柳眉倒竖。
******一怔、一瞧、一退,一句话也没说,抓住酒瓶斟酒再喝,酒没有了。他把瓶子像摔手榴弹似的往窗口扔去,玻璃碎了一地,侍卫破门而入。
紧随侍卫官之后,秘书捧着大红卷宗在那里欲进又止。宋美龄忙叫:“拿来!”秘书连忙呈上紧急公文,******也跟着紧张。原来驻美大使馆来电,说美国民主党议员布鲁姆曾向杜鲁门建议邀请******访美,会商南京善后问题。杜鲁门断定蒋不会赴美,于是希望派一个人,无论如何要去谈谈,俾使美方对中国局势有比较鲜明的理解。美国并不打算取消反共政策,但目前既欲在华反共,却又苦于不得其法。
宋美龄说:“看来我是去定了!上个月我曾去过信,希望他们同美国当局谈谈,看样子他们已经谈过了。”
******沉思久之,由于疲乏至极,酒性发作,竟在沙发上呼呼入睡。待他醒来,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女秘书忙作一团,七七八八地收拾衣服、鞋子、化妆品,弄了一屋子。
“你几时走!”
“明天。”
“都准备好了?”
“飞机是他们的,可能赶不及就坐空中霸王去。”宋美龄道,“而且我已经同马歇尔通过一次电话。”
“他怎么说?”
“我告诉他,你的处境不大合适。我用什么名义到美国?美国怎样招待我?我没办法。他说这样好了,一到美国就住他家,算是他的客人。”
“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应该利用这一次出国,多走几个地方作演讲旅行,呼吁美国立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蒋某人,制止共产主义事态。”
******道:“那很好,美国人人像他那样热心反共,就好了。我这几天脑子很乱,想不出什么新玩意来,不过有人给我建议,说应该把戡乱‘剿匪’说成‘反侵略战争’,这样对国际的呼吁效力大些,美援也会滚滚而来,你以为怎样?”
宋美龄一心一意飞美国,无心作答,漫应道:“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什么事情?”******一怔。
“财产转移问题,”宋美龄低声道,“就按照以前的办法,不再改变啦。”
******闻言凄然道:“这种局面,还谈这个干什么?”但他立刻改口道,“也好也好,我们的还是在一起,也不必分了,你可以在香港同子文先面谈。”
宋美龄见一只只箱子相继装好,洗了个脸道:“你还有什么要同马歇尔他们说的?”
“我没什么说的。”******颓然道,“你前几天对美国广播作的紧急呼吁,说局势危急,希望他们积极援助,我要说的也不过这几句。”
宋美龄凄然道:“上帝保佑!你说实话,南京守住守不住?能守多久?我们的问题同他们不一样,”她失声而泣,“我们是既失国,又失家啊!”
******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