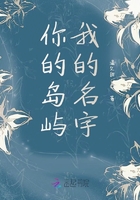是夜,开宴。
酒过三巡,白染鱼看歌舞杂耍看得都快睡着了,眼睛一直瞟身边的席位。
那是吕岫沨的位子,从开宴到现在一直空着。
其他在席的酒楼掌柜们说着谀词,上位的平王一脸平静地受着大家的恭维。
这群狗腿子里没有金风楼的金子詹,因为平王的请柬请了江陵前十的大酒楼,独独没有龙头金风楼。
游子休也并不在席上,那野郎中嘴里果然没一句真话!
席面几乎照搬宫里的样式,没劲得很,白染鱼曾随他那便宜爹爹进宫蹭饭,着实不喜宫里那些没新意的御膳,下酒的菜肴来去不过是群仙炙、太平毕罗、缕丝羹、莲花肉饼那些,而且一席必须喝足九盏,才算完。
他从来没撑到第九盏过,不由得唉声叹气,怀念曾为自己挡酒的吕岫沨,她到底去哪儿了?
在场众人,除了他似乎没人在意吕岫沨在还是不在,就连平王也是,把人请来,人失踪了他倒不管不问。
白染鱼抚摸着红玉酒杯上凸起的花纹,心里转着一个念头——
原来她和自己是一样的,江陵饮馔界的人,从未真正接纳过吕岫沨,就好像白家也从未把他当作自家人。
金枝宫灯将整个前厅照得恍如白昼,他的手悬在额前挡光,眼睛却远眺门口,酒上头了,恍惚间似乎看见门口多出一道人影,径直向他走来,越来越近。
白染鱼停杯投箸,眯着眼睛看那道人影。
是吕岫沨。
她换了身新衣裳,霜色织金广袖衫,和雨过天青并蒂莲花裙,肩上是雾一般的蹙金披帛。
脸上不画时兴的妆,不贴花钿,只略施粉黛,勾勒出一双淡漠却轻灵的双目,无喜无悲,飘然出尘。
高耸翩跹的流云髻,不用任何钗环,别一簇刚摘下的桃花,耳下摇着一对翡翠碧桃耳环。
白染鱼望着眼前的佳人,屏住了呼吸,他早说过,吕岫沨根本不需要和岚岚争什么艳若桃李,她便是她,盈盈素简,浑不似人间诸艳。
她这一出现,堂内顿时鸦雀无声,白染鱼嘴角不禁翘了翘。
“岫沨姗姗来迟,望王爷恕罪。”吕岫沨向平王福了一福。
“等女子更衣化妆,是男子的天职,”平王满意地捻须微笑,“小白,你说是吗?”
“这不公平啊王爷,”白染鱼挑了挑眉,搓火搓得不亦乐乎,“凭什么其他掌柜没有如此待遇?”
怎么扯到他们身上了?在场的掌柜们不由得暗自滴汗,谁不知道这场夜宴他们只是陪衬,八珍阁才是真正的主角?
吕岫沨和白染鱼来赴宴,轿子接送,来是空手来,走却一套新衣首饰带回家。
他们呢,接到请柬巴巴地赶来,诚惶诚恐地献上礼物,平王也没对他们多说一句好话,多给一分笑容。
“白公子此言差矣,”天鲜阁的少东家袁律瘦得皮包骨,一笑起来满脸褶子,“我们一群大老粗,哪里需要像小娘子一样沐浴更衣,描眉画眼的?”
一身肥肉的聚星楼徐掌柜点头称是:“正是正是,也只有白公子这样的天人之姿,才配得上小娘子一般的待遇,我等才要为白公子鸣不平,怎么桃花衣都穿上了,桃花妆却没有呢?”
“徐掌柜你胡说什么,”袁律假惺惺地斥道,“哪个配得上给白公子化妆呀?”
两个人一唱一和,在座掌柜无不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齐齐望向身穿藕粉桃花衣的白染鱼,眼神里俱是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