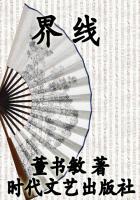桑尼不在身边的痛苦就像牙疼一样真实。白天的时候,鲍比一个人待在卧室,用剥墙皮打发时间。后来,他开始一根一根地拆窗帘上的线,不过最后,无聊还是渗透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他甚至能从自己藏起来的饼干和苹果中尝到无聊的滋味。他感觉每吸进一口气,都能感受到肺部的无聊。鲍比睡着了,一夜无梦。
布鲁斯和辛迪对他完全视而不见。偶尔,鲍比会听到笑声,他会溜进客厅,想知道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开心,但他们从不会与鲍比分享。然而,最令鲍比不知所措的并不是他们不说话,而是鲍比的父亲总会在睡前和他说晚安。一天中可以交流的事情有很多,为什么布鲁斯一定要选择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进行这样一次无法回复的交流呢?事实上,这正是布鲁斯想要的结果。
到了晚上,布鲁斯和辛迪很快就会入睡,这时鲍比就会开始他的档案记录。他会看看垃圾箱里有些什么,好知道父亲晚餐的内容。自从鲍比的母亲离开后,布鲁斯的烹饪习惯就发生了改变,具体的变化甚至可以用一张图表画出来。鲍比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整理档案,在那些时候,只有窗外的月亮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上帝想象成一个独眼巨人,那轮明月就是上帝的眼罩。
当鲍比把所有档案都整理完毕后,他会坐在母亲的地毯上,关上声音,关上灯,看一会儿电视。这时候,电视机五颜六色的光亮会以各种各样的形状映在四周的墙上。他看到过一则新闻,有十四辆警车包围了乡间一户破旧的农舍。远处的城市闪闪发亮,看起来像是一群人在跳康茄舞。那个农民绷紧下巴,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的嘴唇颤抖着,好像他只能用脸的下半部来感受周围的一切。不过,通常,男人确实是这样的。他看起来忧心忡忡,不知道干草堆里藏着什么东西。这时,屏幕下方出现一行字幕:搜捕仍在继续……
鲍比打开卫生间的灯,发现马桶座上有几摊尿迹,在灯光下闪着亮光,像是几粒青蛙卵。父亲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口水一条条地流到了瓷砖上面。
这时,布鲁斯醒了,盯着鲍比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看清了他是谁。他的本能反应是太丢人了,鲍比让他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而鲍比,这种羞辱的见证者,此刻正畏缩在洗衣篓后面。
“你觉得偷偷摸摸地过来,到我这个老家伙旁边,很有意思,嗯?”
“不是的。”
“是要监视我?”布鲁斯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不是的,我发誓不是这样的。”鲍比哆哆嗦嗦地说。布鲁斯开始用大拇指在腰带扣上摸索,鲍比趁机赶紧逃了出去。他穿过厨房,跑上台阶,在那里,他闻不到坏啤酒的味道了。
在那周剩下的几天里,没人想要化解父子之间的冷暴力,这冰冷的距离像监狱的围墙一样真实。有时,布鲁斯确实想跟鲍比说事情,而鲍比听到后,总会“嗖”的一声跳起来,好像脚底长了水疱一般。没过多久,鲍比发现自己完全睡不着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睡意终究还是会来,只不过来得太晚,像一个迟到的宴会客人,毫无歉意。
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周一早上,鲍比吃了麦片盒里剩下的一小撮米黄色的碎渣,之后上了小山顶。他放眼四望,发现邻居们的房子刚好围出一块盆地,而他家所在的那条街正好就在盆地正中央。在小镇周边的郊区,柔软的草地形成斜坡,此刻正好给眼前的景色围上一个边环。整个小镇看起来像坐落在一座死火山上,而镇上的居民好似都以食用脚下温热的火山熔岩为生。
鲍比来到了池塘边,以前他常常和母亲一起来这里,看看是不是到了青蛙遍地的季节。不过,今天他显然没这个运气。一潭死水上漂着一层厚厚的水藻,像海绵蛋糕一样,不时还冒着水泡,发出刺鼻的气味。
街角便利店的店主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她正在装饰精心挑选出的巧克力,把带红宝石色包装纸的巧克力垒成了金字塔形状。鲍比走上前去,大力恭维她的品位,夸赞她竟可以将巧克力摆出如此引人注目的造型。鲍比希望可以搭讪成功,那样的话,她兴许能让他在店里多待一会儿,或是给他一份整理货架的活计。
“我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老太太说,同时认真地给金字塔顶加上了一块比利时巧克力作为装饰,“但是我还没有老糊涂。”
“不好意思,您的意思是?”鲍比问道。老太太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她身上的香水有股玫瑰味,通常只有很年轻的女士才会选择这种香调。鲍比惊奇地发现,这香味其实还挺好闻的。
“你想跟我闲聊,来吸引我的注意力,然后就会有几个年龄大一点儿的男孩冲进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偷光。”
“不,并不是这样的……”
“我在这附近见过他们。”老太太打开门,将指示牌翻到“关门”的一面,“出去。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待在家里,和父母待在一起。”鲍比一听这话,简直想朝她的窗户扔一块砖头。不过他知道,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走到公园的栅栏前,在齐膝高的地方发现一个小洞,于是他眯起一只眼睛朝里面张望,想知道公园里有没有人。结果,他看到了学校里那三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大凯文、小凯文和两人的大哥阿米尔·金戴尔。他们正用什么东西在木桩上一下一下地刻字,刻的是名字的首字母。尽管他们离鲍比还有一段距离,但鲍比一下就认出了他们,不是通过他们的长相,而是通过他们刻字的样子,通过一种深刻烙印在其言行中的东西——吊儿郎当,无法无天。鲍比知道,如果自己穿过公园,他们一定会抓住自己,困住自己的胳膊,在他后脑勺上狠狠地来几下,再把他书包里的东西都扔进泥潭。鲍比闭上眼睛祈祷,要是桑尼现在在这里就好了,他可以用他那力大无穷的半机器手臂把栅栏砸个稀巴烂,再用他的肩炮把那几个坏蛋炸成碎片。鲍比一边假想,一边颤颤巍巍地走回主路。
下午过去了一半,他也快无事可做了,想了半天,只想到一个还没去过的地方。从他家往旁边数五扇门,在拐角那里有一小片灌木丛,六步宽,四步长。它不是前花园,也不是后花园,而是一处在小镇规划中被遗忘的、无人看管的地方。
野草和野花夹杂在一丛丛凤尾草中间,耀眼的樱桃红肆虐地侵占着绿色和棕色的领地。花瓣随风摇摆,如蝴蝶飞舞。一只蜜蜂在水仙花中间来来回回地做媒,一只虎斑猫在追逐散落空中的芭蕾雪花莲种子。鲍比在一摊湿湿的烂泥堆旁坐着,泥水来自上方悬挂着的一盆吊兰,鲍比正用手指搅着烂泥玩儿。
身后传来一阵橡胶车轮滚动的声音,鲍比转身一看,是一个小女孩,正骑着一辆红色的三轮车朝这边过来。不过,这辆三轮车不是蹒跚学步的小毛孩骑的那种,它像是专为那个女孩定制的,因为车轮像啤酒桶一样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就像一匹忠实的铁马。女孩在自言自语,她的小脸圆嘟嘟的,嘴唇周围有一点儿皲裂。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就像新收割的麦仁的颜色,整个发型像一只碗,刘海短短的,正好把眼睛露出来。她的身高刚过五英尺,不过据鲍比猜想,尽管她穿的衣服颜色鲜艳,上面还印有自己早就不再关注的卡通图案,但她可能比自己大一岁。她的小肚子鼓鼓的,她正张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肚子,好让身上那套运动服的下边不要卷起来。衣服压平了以后,上面露出一只褪色的张牙舞爪的卡通海星。
鲍比把自己藏在一处高一些的草丛里,希望不要被发现。他现在需要伪装起来,就像他和桑尼玩打仗游戏时那样,身上最好来点儿烂泥的颜色,再来点儿树叶子。头顶上树叶的影子打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光影,就像灰白色的油漆。这下正好,他和树皮完全融为一体了。他现在就像大自然中的动物,被大地托在掌心之中。
三轮车停了下来,小女孩直勾勾地看着他,好像他们两个认识一样。他尴尬极了,迅速跳了出来,好像从没有想过要藏起来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发问了。
鲍比不想这么说,但这女孩说话时确实有一点儿像托马斯·艾伦。托马斯是鲍比班上的一个男孩,他总会让人想起小镇另一边德普斯区学校里的特殊儿童。他说话时总会卷起舌头,舌尖顶着下唇,说话速度异常慢,发音听起来极为愚蠢。
“鲍比。”他回答道。
“那你姓什么?”
“努斯库。”鲍比踩到一块石头上,踮着脚尖,摇摇晃晃地想要保持平衡。他回头偷偷向小山那边看了看,没有人。就在刚才,他突然想到,要是学校的人看见他正在和小女孩说话,那就完了。因为他们会取笑他,欺负他,在桑尼完全恢复半机器人的能力之前,他都必须一个人面对这些。于是他想,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小女孩。
鲍比之前从没有过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刚才的想法让他羞愧不已:如果母亲回来了,发现自己不像她所教育的那样友善、包容,反而成了相反的样子,那会怎么样呢?
小女孩拉了拉运动服下边的松紧带,然后又松开,短裤上面的小肚皮上露出了一圈儿松紧带留下的痕迹。
“我叫罗莎·里德,”她说,“你想和我玩儿吗?”她从三轮车上下来,手里抓着一支黑色毡尖笔,像运动员递接力棒一样,递给了鲍比。“你想玩儿吗?”她又问了一遍。他不说话,手指正在卷一截长长的草叶。
“玩儿什么?”鲍比开口了。他发现那支毡尖笔被咬过了,塑料外壳上印着一串长长的牙印。“你干吗给我笔?”
“写你的名字。”罗莎把手伸进三轮车前面拴着的车筐,拿出一个卷皮儿的笔记本,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迹,重复写着“罗莎·里德罗莎·里德罗莎·里德”,有几处写得并不连贯。
“为什么要给你写?”
“我要收集名字。”
“但是你只有一个名字呀。”
“鲍比·努斯库,”她摇摇头,“有时候你还挺逗的。”鲍比拿过笔记本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递还给她。他想,最重要的是,不要和她有任何接触,不要碰到她,不要和她同时接触一件东西。他迅速把重心从左脚转移到右脚,同时开始大量分泌唾液,就好像自己的偏见竟令他恶心得几乎要呕吐。
“现在,”他说,“你有两个名字了。”
“你在这儿等一下。”她说。过了一会儿,她走向街角的那幢房子,从花园里取来一个破损不堪的篮球。鲍比完全没想到她住在那儿,没想到她竟然如此普通,和自己住在一条街上。他刚刚还在害怕,怕被别人看到他们在一起,而现在,他为自己刚刚那个无知的想法感到无比尴尬,因而更加嫌弃自己了。他想把那种感觉吞咽下去,就像吞下一块恶心的肉。
他们坐在马路牙子上把球传过来又传过去。尽管罗莎手指短,动作慢,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但他们还是迅速找到了玩游戏的方法。每次罗莎没接到球,鲍比都会模仿她把球弄掉的样子,她看到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肚子疼。鲍比没有忘记留心朝这边走来的人,还好,没有人走过来。
罗莎也模仿了鲍比,但她的动作很笨拙,这让鲍比觉得她身体里仿佛住着一个小人,踩着踏板拉着线,在控制她的一举一动。他们俩玩儿的每一种游戏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模仿游戏,鲍比做一个动作,罗莎跟着做一个,但是她的肢体不太协调。他举起胳膊,她也跟着举起胳膊;他把球扔给她,她又把球扔回给他。这个游戏里没有竞争,它就像一场奇怪的没有声音的模仿秀,他们就像一朵花上的两片花瓣,互相嬉戏、打闹,只有微风才能将他们分离开一秒。
鲍比玩儿得太开心了,这是他去医院看望桑尼后,第一次把桑尼抛诸脑后,他甚至忘记了别人可能会发现他和罗莎在一起。有那么几个短暂又温暖的瞬间,他忘记了刚刚萌发的自我意识,玩得无比开心。和桑尼一起度过的时间让他知道,这就是友谊。友谊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魂的锁。
黄昏下,一丝凉意袭来,鲍比身上起满了鸡皮疙瘩。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笑声,那笑声在空中盘旋,又渐渐变弱,消失,像是毫无价值的想法就这样被否决了。鲍比一阵恐慌。
“罗莎,”鲍比突然说,“我要走了。”
“怎么啦?”她一边问,一边用手转着球。
“我就是要走了。你也得走了,你得回家了。”
“为什么呀?”
“赶紧回家!”他轻轻地推了她一把,想把她转向家的方向,但罗莎比他想象的要壮实,倔得一动不动。“求你了。”鲍比说。
“到底为什么呀?”
鲍比又听到笑声了,这次他听得很清楚,笑声是从不远处传来的。他们来了,他们一定会看到自己和罗莎在一起的。这一切还是来了。这一次,鲍比抓住了罗莎的肩膀。
“罗莎,你必须得走,现在就走!”
罗莎从口袋里拿出笔和纸,开始歪歪扭扭地在上面写“罗莎·里德鲍比·努斯库”。
“我才不呢!”她生气地说,“我还要继续玩儿。”
在夕阳的剪影中,鲍比看到公园里的那三个男孩正向小山这边走来。
“对不起了。”鲍比说。
太晚了,已经没时间逃跑了。鲍比没有办法,只得赶紧钻进树丛,把罗莎一个人留在了原地。他把头塞进两腿中间,使出最大的力气用胳膊紧紧地抱住膝盖,屏住气不敢呼吸。
他们来了,但是没有看到鲍比。
“你们好呀,我叫罗莎·里德。你们叫什么呀?”阿米尔开始重复她的话,就好像录音机的半速回放,凯文兄弟听了哈哈大笑。鲍比听到笑声,想冲出去帮罗莎一把,但他太害怕了,根本挪不动步子。那些人对着罗莎一阵嘲弄,但是她好像什么都没听懂。他们的笑声渐渐变小,成了窃窃私语,然后他们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他听到罗莎的笔和本子掉到了地上。
他听到罗莎的鞋底来回刮擦着地面。
他听到罗莎在号啕大哭,那哭声像惊人的风暴。
鲍比能做的只有听着,恐慌着,预想着最坏的结局。她惊声尖叫,又突然失声,好像有人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她的腿突然不再踢腾,好像有人把她拎了起来,又重重地摔在了泥滩里。
泥滩中一直有搅动的声音。
她在试图向鲍比伸手,好几次都蹭到了树丛,引起一阵晃动。
鲍比此刻感到了深深的羞耻。那感觉就像内心的黑暗涌了上来,鬼鬼祟祟地匍匐前进,挣扎着想重见天日。这时,在一米开外,那个他羞愧得不敢面对的女孩,此时此刻终于感到了恐惧。
直到听到他们都走远了,嘲讽的笑声消失了,鲍比才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四周一片安静,只能听见乌鸦的啼叫声。
罗莎躺在泥滩里,那几个男孩把她的肩膀和胳膊狠狠地按在里面,留下了一个人形轮廓。她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都灌满了泥水,眼睛里流出两行古怪的红泪,流过了沾在脸上的泥浆。鲍比把她拉起来,让她坐在地上,然后开始用手指清理她呼吸道里的烂泥。之后,他脱下毛衣,帮她清理耳道和鼻腔里的泥水。突然,罗莎号啕大哭。她的两个眼珠里布满了红血丝,双眼呆滞,不知在想什么,思维好像飘向了另一个世界。
“罗莎,我对不住你。”鲍比说。
他用尽全身力气才扶她站起来,这时,她头发和衣服上挂着的土块一下都滚到了地上。他把她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上,她的哭声太大了,以至他们还没走到她家门口,已经有人打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她皮肤苍白,眼眸和头发黑亮,像是吉卜赛版的麦当娜。罗莎冲过去抱住她,她们一下就抱头痛哭起来,泥水沾满了她们的脸庞。
几小时前,罗莎央求妈妈让她出去玩,因为实在拗不过女儿,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答应。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瞬间做出的决定,就是这千千万万决定中的一个,让她立刻就后悔了,而且会后悔一辈子。合时宜的母性是需要一生去追寻的东西,而不合时宜的母性只要一秒钟就会控制你的头脑。
一大片乌云吞没了太阳。女人直勾勾地瞪着鲍比,用一种无比强势的语气开始了问询。她的眼神太过愤怒,以至鲍比都能看到她眼球的颜色,是那种湿蛇皮的青紫色。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开始了。
“有几个男孩过来了,”鲍比开始解释,“他们把她按倒,在她嘴里、耳朵和鼻孔里塞满了烂泥。”女人立刻转身走进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瓶水。罗莎这时候还是不能顺畅地呼吸,她把头仰起来,让妈妈把水灌进她嘴里,然后又用水冲洗了脸。冲洗完后,罗莎拿着瓶子,她妈妈朝鲍比走了过来。她用手按着鲍比的后脑勺,强迫他迎向自己的目光。在她头顶上,乌云遮住了太阳,形成一个暗沉沉的光圈。
“那几个男孩,”她问,“是你的朋友吗?”
“不,不是。”他回答道,但是羞愧好像拴住了他的舌头,让他说起话来软绵绵的,像是在撒谎。她的手按得更用力了,说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几个男孩。我并没有看见他们。”
“你最好老实点儿。是不是你干的?”她指了一下罗莎。鲍比摇摇头。两行泪从女人的脸上滑落,鲍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真的不是。”
“要是你干的,我就杀了你。”
鲍比哆哆嗦嗦地说:“我当时吓傻了,就藏了起来。对不起。”
“要是上帝允许,我会打断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不要!”罗莎大喊一声。她妈妈放开了鲍比。罗莎紧攥的拳头松开了,脏兮兮的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们两个的名字。她妈妈接过那张纸,大声地念了出来。
“鲍比·努斯库。”
“他就是鲍比·努斯库,”罗莎指着他说,“鲍比·努斯库是我的朋友。”
鲍比裤子上的尿渍现在虽轻了一些,但仍能看清楚。他的胆怯和尿渍一样,板结在裤子上,罗莎的妈妈看到了这一切。他羞愧至极,以最快的速度跑了出去。当他跑回自己家时,屋子里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