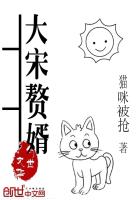客人位置的李攀脸色有些难看。
这衣裳清凉的陈相公太不给面子了。
“晚上我跟夫人吹吹枕边风~帮打听打听。”
陈相公补救道。
李攀用着茶。
“赵相公在旮沓角罗家村开了个纺织坊~这用上了新式的纺车,我家夫人经常挂在嘴边。”
“是有这回事。”
陈相公非常有兴趣,紧问道“一台纺车一日能纺出两匹布?”
“差不多吧。”
李攀敷衍回了一句。
“这新纺织车是好东西。”
陈相公扭了扭摔在太师椅没几两人的身体,屁股多动症般“平南城历来不是产布大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下中之姿的县城。”
“我家夫人很看好新式的纺车,常常挂在嘴边同衙里同僚讨论。”
“想在平南城推广开。”
”做出一番政绩,往上升升官。”
“不怕你笑话。”
“我夫人不是嫡出的,今年吏部考核~陈吴两家关系已用尽,效果不尽人意,只平调京府衙门的七品治中,管管些刑狱案件。”
“推广开?”
李攀若有所思。
他摇了摇头。
即使新纺车的前景再好。
罗家村已经没有扩充浣溪坊的本钱。
也不可能全推广开这种新物式。
利益即得体。
罗家何县丞李攀都不会同意。
推广开。
纺车技术还能一骑绝尘~独领瑛朝纺织业的风骚吗。
这不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吗!
“三方都没有钱银扩大浣溪坊了。”
李攀委婉拒绝。
“我夫人能牵头,衙门方面出面担保,同本地办的许记海运行~借资金增扩浣溪坊数量。”
“若是浣溪坊肯让股。”
“平南城大商人~士绅都非常愿意出资金入股的。”
陈相公头头是道说。
听了一耳朵。
客位的李攀有些腹诽。
这陈相公为了给夫人铺官路。
舌灿莲花游说。
他隐约收到一点风声。
陈知县今年铁定调离平南城。
人走茶凉。
又鞭长莫及。
那还管得了浣溪坊的事。
偏偏新式纺车又是一块好大的肥肉。
原。
眼不见为净。
现在看到了隐约能凭此做出政绩~平步青云,却是无论如何也想抓住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升官升到新高度的尾巴不放。
“浣溪沙坊不是我一言堂能决定的,想扩大布匹产能,陈大人最好跟何县丞商量着来。”
李攀谨慎道。
“……哼。”
陈相公胸堂剧烈起伏。
提到何县丞。
他面色难看。
自家夫人处理完公务~睡前常常挂在嘴边唠叨~更上一层楼的怨念颇深。
他此会不清楚本土派的难缠。
以何县丞为首的人马。
是茅坑里的石头。
态度又臭又硬。
衙里各房典吏也是墙头草。
哪边给的好处多就吹向哪边。
两人都没再说话。
厅内气氛有些沉闷。
腰肢纤细的小侍男~进来给再次续上茶水。
待下人福了身退出。
陈相公头歪向李攀这边,满头珠翠跟着晃“赵相公。浣溪坊的技艺都傍在你一人身上,若是你首肯多增开设布坊,我夫人是鼎力相助的,缺什么给什么。”
李攀心里瑶瑶头。
他有些愁闷。
事情谈不下去了。
这陈知县想在明年升走前把新式纺车在平南城推广开来,做个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政绩。
但他和罗家村的人都是何县丞派系的人马。
不能干吃里扒外~引狼入室的事情。
偏嫂嫂罗向阳的人命官司就压在陈知县手中。
利益交换不到位。
衙门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倾扎。
嫂嫂罗向阳决计没有好果子吃。
最轻也要判个流放。
搞不好。
判防卫过当。
判。
秋后问斩。
李攀直接询问道:
“衙门肯牵线开设增加浣溪坊的数量,对平南城的商业繁荣有偌大好处,何县丞为何反对阻拦?”
陈相公咬牙切齿道“不甘于人后诶~她翅膀硬了,压着浣溪纺做晋身之姿,窥知县正位。”
“还有这缘由。”
“当官的花花肠子真多。”
“怪不得浣溪坊官面上没人找麻烦~一片祥和。”
李攀心里升起强烈的危机感。
罗家村浣溪坊的股份四四二分。
他占40%。
罗氏族人占40%。
何县丞占20%。
但来自现代的信息爆炸告诉他!
他手段很嫩很不妙。
巧取豪夺四字直接出现在了他脑海中~浑身发冷。
他咽了一下,道:
“我本人是接受资金入股的,按资分配个股,我技艺入股,能者~劳者多分。”
他斟酌了一下,道:
“何县丞那边就劳烦陈知县沟通了,我本人愿均给陈相公现在浣溪坊5%的认购股份以示我城意。”
主位的陈相公拽着汗巾子。
他静静听。
两条黑眉锁在一起。
他心里亦喜亦忧。
这边的赵相公松了口。
浣溪坊推广的事情有了操作的余地。
当即开始松口:
“刁民甚是可恶~凭白冤枉好人。”
李攀心里一喜。
陈相公定了调子。
嫂嫂罗向阳就不会被重判。
至于告官的那方是不是真的刁~陈相公李攀都没放在心上。
一介没权没势的草民而已。
揉扁搓圆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坐主位的陈相公对贴身侍男耳语了几句~即挥手摒退。
小侍男福了身退出。
虽猜到了谈话内容。
李攀并没有询问的意思。
走后门~以势欺苦主并不是太光彩的事。
“喝茶喝茶。”
陈相公热情招呼。
传话的小侍男脚步匆匆。
过廊视满塘荷不见。
径直穿过垂花拱门。
莲步轻移至绿树成荫~避暑的外书房。
他和门口的护卫递了话。
片刻功夫。
三十余岁微胖的女幕僚出来。
直直看着他。
十五岁的小侍男顿感压力,红白嘴唇动了动,把陈相公托的事道来。
听仔细的幕僚有些惊讶。
“你在这站着别动。”
传话的小侍男自是不敢乱走离开~垂手站旁等候。
书房内。
“东主。”
“浣溪坊的事情有了转机。”
幕僚振奋道:
“浣溪坊其中的东家‘赵相公’大有来头,是浔阳郡城赵将军的女婿,其女儿赵静的侧室。”
“来访的赵相公有松口的意思。”
“肯让出现如今浣溪坊5%的股份给东主,另有意愿增加浣溪坊在平南城开设的数量。”
幕僚声音又小了些。
她把利益交换的对象,罗向阳一案详细前后过程道了出来。
国字脸的陈知县玉背挺拔。
在文书后处理公务。
她静思了片刻。
道:
“案件内情我知道了,告诉他,衙门决不会冤枉一个勇斗淫贼的好人。”
幕僚笑了笑。
颇有些意味深长。
书房外。
垂手而立规规矩矩的小侍男没一思多余的不耐烦。
片刻钟后。
幕僚出来。
示意小待男近前。
小声对他耳语了几句。
得话的小侍男福了身。
匆匆离开避暑的外书房。
甬道前待客厅内。
气氛有些轻松。
不像没谈扰前般沉重。
李攀等了一盏茶的时间。
陈相公的贴身小侍男匆匆而归。
恭恭敬敬在主子边耳语了会。
听完。
主位的陈相公满面笑容。
似骄横似早有所料。
对客位的李攀道:
“衙门决不会放过几个坏人清白的淫贼。”
“再好不过了。”
李攀虚伪笑了笑。
躲在屏风后听了事情始尾的稚嫩少年撅了撅嘴。
嘴型做了个‘坏人’的表情。
这赵将军的女婿不是个好东西。
“午膳在这用吧。”
“我这个主家尽尽地主之谊。”
夫人的官途顺利些。
陈相公心情不错。
他邀请用午饭。
上午巷弄里的蝉还是形影单只赛叫,到了正午,衙门府园树上的蝉却是连成一片咶噪。
李攀拒绝道:
“浣溪坊的工期很短,今日还是请了一天假拜访陈相公,下午要赶回去追落下的进度嗳。”
陈相公没强留人用饭。
吩咐贴身侍男去让府内管家备一份厚礼。
见状李攀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要求“方不方便去牢内探视亲人?”
“方便方便。”
陈相公起身:
“这就去吧。”
两人客套一番。
出了厅。
前呼后拥。
十几人径过回廊。
李攀陈相公谈论了一番荷花池塘内鲜艳绽放的荷花。
随行的仆人护卫离七步停下。
贴身的小侍男石桌上斟茶水~放置点心待客人拿用。
“观荷我有一诗以拟景。”
这次跟过来的稚嫩少年打断两人家室互吹式的谈话。
“我这表亲有点歪才的。”
陈相公剜了一眼高高少年。
他有些生气。
“……哦?十步成诗?说出来大家帮鉴赏鉴赏。”
李攀适当吹捧道。
仿佛没看到这个比自己年龄小几岁丸子头少年眼里的挑衅。
他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就怼上他了。
旁的陈相公看出些了什么,笑容有点劬强“我这个娘家表弟是有几分急才,想一出是一出,猴儿似的上蹿下跳。”
他定了调子。
给兜底。
丸子头稚嫩少年也没生气。
他娴熟互吹道:
“赵相公是侯府世族的女婿,又得赵将军青睐,想必诗词琴棋书画都一绝,不吝请赐教。”
丸子头少年说得很诚恳。
他郑重做了个瑛朝男子互见面的躬身大礼。
“赐教不谈。”
“未辈先请。”
李攀躬身回了礼。
尽管不爽。
他还是捏着鼻子说了一句。
黄衫男子脸如温玉。
高挺鼻子上翘。
两条似横竖的弯黑眉。
举手投足间~带不一灵性风情。
面对面。
丸子头少年甚至看到。
黄衫男子鸡蛋青般的额下~血管脉络隐约可见。
脸蛋比不过算了。
更让他嫉妒的是。
锁肩也是衣服架子。
鲜艳的黄衫一字撑开~举止又欲又端庄,像及了青楼热情接客的男妓。
竿湖尺三丈。
苞苞发荷花。
塘底藏淤泥。
馨香无复全。
旁的贴身侍男石桌上摆弄茶具杯子。
七步远持刀枪的女护卫眼观鼻鼻观心。
听了这首荷花诗的陈相公给了丸子头少年一个赞赏的眼神。
鼓励道:
“这荷花诗能在邱报上投稿~传颂四方了。”
丸子头少年被赞赏没有喜形于色~却是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直直看着黄衫男子。
“水平还不错的五律诗。”
“瑕不掩瑜。”
李攀心底嘀咕了一句。
叫他现做是做不出来的。
他又不是七步成诗的曹子健。
能立刻写出比这首好的荷花诗。
都无色可并。
不奈此香荷。
回廊乘凉意。
金覊午落过。
回衾灯照绮。
渡袜水沾罗。
预想前秋别。
离居梦棹歌。
李攀念出了李商隐的荷花诗。
前四句既有点晴之笔又有景物~后四句抒发寄情。
直接秒杀丸子头少年的短小无力的四句荷花诗。
“好诗好诗。”
陈相公极为捧眼。
鼓着掌。
丸子头少年脖子有些僵硬。
银盘包子脸涨红。
欲言又止止又欲言。
这不是现做的五律诗。
“我下午还要赶回罗家村,探监事情先了。”
看到丸子头少年要说话。
李攀先出声。
“是极是极。”
“可不能耽搁了赵相公的事。”
陈相公附和。
至于。
刚才的插曲。
都没有人再提。
前呼后拥~步行五分钟后。
监牢外。
门口污秽荤臭。
管家跟女牢头交涉。
女牢头看了这边前呼后拥的人一眼。
她便满脸堆笑。
脊梁骨都软了三分。
脸上肥肉跟着颤了颤。
“贵人这边请。”
“不知有贵人要进来探监,没来得及洒扫~见谅见谅。”
女牢头陪着笑。
陈相公掩着鼻。
没有说话。
交涉完的管家“赵相公里边请。”
“前面带路。”
李攀面色如常。
心底却是直干呕。
平南城大牢门前太臭了。
地上一条污浊通道直通阴森的大牢里面。
通过未干的黄白污渍。
隐约能看出是人的屎尿~兼排泄物。
李攀脸色有些难看。
管家一语未发。
女牢头脸有些涨红。
嘟囔道:
“该死的老黄头。”
“挑个犯人的屎尿还洒出这么多。”
说着一脸匪气。
进了牢里。
有些空旷。
厅内两旁放置有盆装一人高的烛台~燃烧着拇指粗的蜡烛照明。
“牢头。”
“你老怎么来了。”
望风的狱卒一激灵。
倚墙上歪歪斜斜的身体机灵站直。
“都坐好。”
“站没站相。”
女牢头向四周大声呵斥了一句。
匪里匪气。
警告意味十足。
她顺着用刀拍醒了几条滚在一起的酒虫。
另桌上玩骰子的狱卒也忙收置好五色骰子~堆置身前的铜钱一窝蜂塞放怀里。
“贵人请。”
“你探监的在九十四号牢房。”
女牢头殷勤道。
进来的管家和李攀都用手捏着鼻子。
如果说牢门口前是上厕所时排便的臭。
那么进了狱中就是米共池中的臭。
“……啊!”
“……哎呦。”
此时厅中寂静可闻。
站起的女狱卒拘谨看着~四下好奇打量的黄衫男子。
微迹可查下。
狱深处传来的皮鞭击打呻吟声越发清晰了。
“前面带路吧。”
李攀吩咐了一句。
平南城大牢占地颇大。
穹顶呈深拱形。
鸽子牢房紧挨着。
甬道能供六人并排行走颇宽裕。
厅边的鸽子牢房。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内置有棉被小床。
矮小桌椅茶壶
净手的水桶兼夜壶。
剩下的后七号至一百号鸽子房也分置有一块床板和夜壶。
剩余一百号牢房至二百多号牢房只备置有一窝垫背的稻草兼一只看不出颜色~年代久远的夜壶。
“……男人,是男人。”
“老娘要男人。”
李攀掩鼻走进牢狱深处。
两旁鸽子房披头散发的女犯人疯狂叫嚣。
手伸出窗外抓去。
更有疑似失去痛觉的女精神病犯人。
用衣不蔽面的下体和满面污血的头颅疯狂撞击木门。
那力度震得手腕粗的木门‘咣咣’作响。
李攀咬着下嘴唇。
看得触目惊心。
女疯子癫狂的样子有些唬人。
领路的女牢头对手下使了个眼色。
狱卒会意。
挥起带褐干血的倒刺长鞭。
对胆敢伸出门缝的脓疮烂手手噼里啪啦~毫不客气抽打过去。
鸽子房内顿时一片惨嚎。
机灵的犯人忙不迭收回手。
迟钝的血迹洒落鸽子牢笼。
星星点点。
李攀撇了眼牢头。
没有说话。
“这些犯人对贵人不敬。”
“冒犯该打。”
女牢头讨好道。
她身子矮了些。
脸上肥肉跟着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