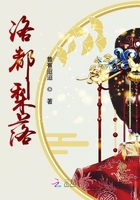纵使是百般的不愿,但面对现实的时候,人们还是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颅,很多人逃避似的闭上眼,似乎是不愿看到这件预料中的事情的发生。
其实,村长说的是对的,花钱买命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交易。
毕竟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是如果命没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可即便是这样,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就这样付诸流水,心里还是很不甘,强咬着牙,歇力地令自己不要发作,无论如何,这都是村长的决定,是他决定了用钱保住全村人的性命,这可能是这个老头儿为数不多的愿望了,难道就真的不能再忍一下么,难道就真的要把他的这点愿望也要夺走么?
噗呲的闷响了一声,就在男人贪婪地凝视着那一袋银钱,准备迈开脚步将它据为己有的那一瞬间,一只瘦削的手臂忽然间出现在众人惊愕的视野里。
一条生命就这样开始走向了凋零。
那一只手,一只沾满人血的手,犹如长矛贯通那般,横空而来,陡然没入男人的背后,破开他的胸膛,随手摘下了他的心脏。
那颗硕大的心脏在昏暗的光线中微微战栗着,鲜红色的血液流过那一只仿佛种植在男人胸口上的手,滴答滴答,一滴又一滴坠落在灰色的地面上,悄然无声地溶化在粉尘下的土地里。
没有征兆的,世界渐渐开始失色,男人艰难地歪过头,想要看清背后的那个人,可是不知道是由于天色太暗的原因,还是大脑缺血缺氧的缘故,无论他再怎么拼尽力气去凝视那个杀害他的人,可是看不到真切。
什么都已经晚了,什么都要走向结束了,在浩瀚的死亡面前,人类总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能为力。
他的脑子里,他的视野里,尽皆模糊一片,混沌的物质像是脑髓,不断地翻腾着,就像是在做濒死的挣扎,而在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混沌都被拉成一条长长的直线,所思所想,一切都于此归零了。
他到底没有看到这个杀害自己的凶手,然后就死了。
“一个人一百银...”那个手里滴着血的少年隐藏在侧影里,似乎在微笑着说。
他的声音嘶哑而又飘忽,就像一头迷失在荒野里的孤魂,空洞的嘴里流动着寂寥的风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眼神惊愕,猝不及防。
血继续滴答滴答地流,少年抽出了那只染血的手,男人的尸体顿时失去了支撑,坍塌地跪倒在地上,苍白的眼瞳同样失去了焦点,僵死一样地注视着身后的地方。
那扇老朽的大门外面,那些嚣张跋扈的土匪们全都死了,死相出奇的一致,胸膛被洞穿,跌落马身,横七竖八地瘫倒在地。
血无声无息地流过他们胸口的空洞,但无论是地面上,还是尸体凹陷的窟洞内,或者是此刻少年的手上,都找不到心脏的影子里,那些半刻之前仍旧在旺盛搏动的器官仿佛蒸发了一般,凭空消失在浓烈的空气里。
月亮缓缓浮露在云间,清色的银辉下,弥散着一股仿佛洗不去的血腥味,少年转过身,仿佛失去兴致般地朝向门外走去。
“但土匪不是人,是垃圾,垃圾不值钱,统统杀掉就好了,不用收钱。”他对着天空嘶哑地说,然后转身离开。
“慢着!”沉默了很久的老村长忽然说。
但是少年没有回头,似乎是没有听到老头儿的话,一步不停地朝门外的尸场走去。
微末的冷风里,他半步跨过那扇门,瘦削的背影被夜光照得漆黑而又迷离,就像是恶鬼重返地狱。
“恩人,请你尽快离开,”老村长还在说,“这些死掉的土匪全是沙达的人,如果让他发现是你杀掉了他的手下,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趁现在,麻烦您赶紧逃吧,离开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他又一次重复地说,“沙达是不会放过你的。”
夜色愈发清冷,老人的声音发散在风里,少年即将落地的前脚忽然顿住了,滞留在风中半刻,随后缓缓地收回。
他就像是被挑起兴趣那样转过身,阴冷地直视老人,“沙达?也是土匪么?”
那是饿狼般的眼睛。
深藏在体表下的杀戮杀意似乎被老人的一句话唤起,迅速地从僵死的机体里醒来,涌向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他是那样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老人,就像野外凶兽的威逼感,仿佛是在无声地威胁着老人,告诉这个老不死的男人,如果不说出那个叫做‘沙达’的土匪的老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掐断老人的咽喉。
为了杀戮,他可以不择手段。
“不能告诉你,”老人缓缓地摇头,“你是打不过沙达的,沙达是神师,手里拥有通天的手段,你还是太年轻了,去了就是找死,不可能战胜他的。”
少年歪着头,依旧直视着老人浑浊的双眼,目光越发冰冷。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老头儿还是面无惧色地说,“我们不能恩将仇报,指引你去犯险,这是老祖宗们留下的规定。”
“无所谓的规定,”少年嘶哑地开口,残忍地笑,“难道把你们全部人都杀了,也不愿说么?”
老人摇摇头,寂然地开口,“请你放过他们,他们是无辜的。遵守祖宗立下的规定的人是我,仅我一个,也是我令得他们不能开口。”
“如果你真想知道沙达在哪里,麻烦你杀了我吧,”老人说,“杀了我之后,他们就不归我管了,带不带你去那里,任凭他们自己决定。”
“食古不化...”少年冷冷地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苍老的男人。
淡漠的月光下,他的眼睛忽然睁到了最大,血丝条条地绽放在他的眼白里,他就像是一头自浓墨之中冲出的猛鬼,对着这个愚昧无知的世界发出烈火一般的爆吼,“简直不知死活!”
逼迫神经的杀机骤然降至,老人平直地注视着那个发狂的少年,面色从容,仿佛在赶赴一场久远的飨宴。
那里并排坐在无数张被时间冲洗到仅剩下大致轮廓的面容,一个个被镌刻在木牌上的名字。
他忽然笑了起来,开心地笑了起来,就像是个刚刚放学的孩子,快乐地跑向大人们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