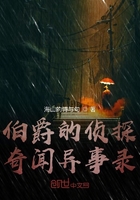第三十五具
.
“福州这也有啊,有一家离我们特别近,就在我们医院后面那条街你知道吧?”
陈哥在下铺探出头对东仔说。
他说的是嫖I娼的地方。
当东仔问他为啥不出去玩,每次下班都回宿舍躺着。
“真的,不是我不想玩,已经没感觉了你知道吧。”
陈哥说。
“什么酒吧网吧那些,基本你们现在玩的东西我都玩腻了的,一点感觉没有。”
“也不是说我一直躺在这。我也是会跟朋友出去玩的。”
陈哥阴笑道。
“就是去,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你还比较小。”
陈哥欲言又止。
“打炮?”
东仔听到这问他。
“对,哎看你也不老实的那种,要不下次带上你?”
陈哥看被东仔猜中,他冒出脑袋兴致勃勃问道。
“福州以前很多这种店的,好多给封了,但还是有剩几家。”
“不过那几家我都去腻了,我们几个人现在都是去泉州。那边更多,到处都是。”
“下次带上你?”
陈哥对他问。
东仔有些犹豫,毕竟他这意思是请客。
想到前几天跟猴子走在路上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快二十了。
二十岁我在干嘛?
“不贵的,就五百,快餐。”
陈哥接着说。
“你们几个人去的?公司肯放你们?”
东仔不理解问,因为公司的就这几个人,都是轮休,怎么会一起去。
“我朋友,又不是公司的,再说去的时候,直接请假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样。”
陈哥回答。
“请假?不是很难同意的么?”
公司人就这么点,除了大事都不允许请假,甚至过年,除了外省的员工外,都不能放假。
陈哥是五年一直呆在公司里,没回过一次家了。
“就说回家相亲,我跟你讲公司这些人,谁说请假相亲,百分之八十都是去泉州那里嫖,我告诉你。”
陈哥回忆着人数,笑着说。
碰巧这时候吴哥推开门。
“来单了,来单了。”
他站在门口说。
“你是处男吧?处男人家会给你一个红包的。”
陈哥问东仔。
“操,我记得你是东莞的,那没事了。”
陈哥起身穿起裤子自问自答道。
“你们,你们这是在说什么?”
吴哥满脸懵逼,他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劲爆的话题。
“没什么,说下次去泉州,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陈哥利落的套上鞋子。
“别带坏人家。”
吴哥愣了愣对他说。
“我带坏个毛啊,人家可是从东莞来的,估计比我还早破雏了。”
陈哥辩解道。
“别污蔑我,我还是处男。”
东仔答。
“对,我也是。”
陈哥阴笑道。
“那刚刚谁在跟我讲破雏的事?”
东仔对他笑问。
陈哥那时也是实习时候,被老员工带去店里,完事后小姐还给了他一百块的红包。
“唉。洗一洗,还是处男。”
陈哥憨笑着,说出了这句经典名言。
东仔听的埋在被子里笑。
“小伙子,你要不要上手。”
陈哥对床上的他问。
东仔看了眼时间,已经十二点半了,快一点了。
“走吧。”
东仔下床回答。
“你就别去了吧,这么晚。”
吴哥看了眼手表,劝东仔休息就行了。
“没事,我想多上下手。”
东仔穿上外套。
“人家小伙子有上进心,让他去嘛。”
陈哥笑道。
“你这叼毛。东仔你确定要去么,你实习上手的话没绩效的,而且这么晚,你明天还要上班。”
吴哥对陈哥骂了句,对东仔说。
“没事的,哪里的单。”
东仔准备好了问。
“OK,家庭单这个。”
吴哥见他要去,点点头就一同走出去。
三人坐上出租车。
“东仔才多大,你别带坏人家。”
吴哥说。
“毛啊,他有十八成年了吧。我那时才十七就被老周带去了。”
陈哥不满道。
“你这时候还在实习,别去那种地方,好好工作先,这种事情,你以后结婚又不是没有。”
吴哥对东仔说。
吴哥表面虽然浪荡,但是个很负责的男人,没沾花惹草,努力赚钱还房贷车贷,有个老婆和女儿,每天都准时接她们放学和下班。
他唯一消遣就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喝酒。
“不是,别把我说的那么饥渴啊。”
东仔一头黑线,他都快二十了,是在想这个年纪都没什么作为,又浪费一年。
“是是是,以后别半夜给我发现你在摇床。”
陈哥听的敷衍点点头说。
“你他妈。”
东仔一下听懂,笑的在他大腿上拍一下。
半夜车开的很快,东仔他们到了目的地。
这是个破旧小区。
吴哥打电话,得知位置后,几人在等公司的灵车开过来。
灵车放着棺材和干活的工具。
三人就在门口抽烟。
“我现在才知道入殓师是第四声,不是第三声。”
东仔想着他以前的叫法,才知道这个字都说错了。
“其实我们国家是没有入殓师这个名称的职业的,我们是算归类在殡仪服务员这个职业里的。”
吴哥说。
“入殓师那个是小日本他们的叫法,台湾那边是叫礼体天使。”
“别看我们很多人,实际上专门做入殓的,很多殡仪馆都没有,尤其是县级的那种殡仪馆,他们都是家里人做,要么就是直接拿去烧,专门做这个的很少。以前公司跟**殡仪馆合作时候,就是我们做。”
吴哥告诉东仔。
“**殡仪馆那地方还是人的?”
陈哥听到着说。
“真的,离那些殡仪干久的人远点,真的。”
陈哥对东仔说。
“没一个正常,我在殡仪馆那些就是,哇,真的不是东西这些人,心理有毛病的。”
陈哥摇摇头道。
“别这样说。”
吴哥突然劝了一句,似乎他这样讲不太好。
“他们不是心理有毛病,他们是短命鬼而已”
吴哥笑着解释。
“哈哈哈,精髓!”
陈哥跟着大笑,竖起大拇指。
“短命?因为肺尘么?”
东仔问。他在想是不是骨灰那些,由于火化工长年呆在车间里,吸入了太多粉尘。
“什么肺尘,那叫补钙。”
陈哥吐出口烟,指正道。
突然一辆出租车猛的在三人面前停下。
出来了里面的司机和年迈的客人。
两人在半夜里大喊大叫,互相指着对方骂。
说着当地的话。
“听的懂他们讲什么么?”
东仔问。
“这是福州话,我怎么知道。”
陈哥回答。
“等等忙完了,先别把担架推走。”
吴哥看着眼前越吵越凶的两人,吵到双方都开始撸袖子。
他说:
“估计等下还要做这单。”
两个吵架的人,不知道蹲在旁边看戏的是三个入殓师。
他们在等这两人最后是谁躺在地上。
碰巧的是后面小区保安,从亭里走出来。
叫他们别影响楼里的业主睡觉。
把两人呵斥离开后。
保安望向看戏的三人。
“你们在这干嘛?!”
保安问。
这时灵车刚好开过来。
吴哥叼都没叼他,起身就去车里搬棺材。
“诶!你这车不能开进去!”
保安走前大声道。
“我们是太平间的,给里面**楼***号的老人家做后事。”
蹲在他背后的陈哥丢掉烟头平静道。
保安一脸震惊转回头看向说这话的陈哥。
“东仔过来帮忙。”
吴哥打开后车门,他拉出棺材一角说。
保安这才看见车上写着殡仪服务**公司的贴纸,和里面鲜红色的棺材。
“现在能进去吧。”
一米七八,身材胖壮的陈哥看着他问。
“可以可以。”
大半夜下,漆黑的破旧小区里寂静的没有声音。
保安连忙走回亭去。
“不用登记么?”
陈哥还站在后面纳闷的问,想继续逗这个保安。
那人在里面连忙摇摇头,摆摆手。不敢继续看过来。
他们搬下棺材和干活的工具。
吴哥和东仔穿上防护服,准备上楼。
陈哥坐在一旁,悠闲的抽烟。
“你就这样坐着,让人家帮你干活?”
吴哥冷眼看着他。
“我又没有逼着他来啊,他自己要来的。”
陈哥生气的回呛。
“你是捅女人把脑子捅傻了吗?”
吴哥站在那问。
陈哥低下头,一脸不爽。
“算了算了,我是真想学东西,自己要来的。陈哥肯给我来,我就挺开心的了。”
东仔解围拉着吴哥说。
“几楼?”
东仔转开话题问。
“三楼,走吧。”
吴哥转身往楼上走去说。
“陈哥我们先上去啦。”
东仔回头道。
“嗯。”
生闷气的陈哥低头应道。
到了三楼,大门敞开着。
里面的光散发明亮的橙黄色,估计一百平左右的老房子。
周围的装修都是红色木制的,那种旧时的中式风格。
连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柱子都是木头做的,里面有很多人。
其实这个装修放在二十几年前,是有钱人才有的。
哪怕现在看的过时,但还有那种庄重温馨的气息。
门口的厨房,坐着客服经理和几个中年人。
吴哥带头对家属打了声招呼,问了遗体在哪。
“就这就这。”
得知他们是来做服务的,一个中年女子指向一旁。
客厅上有个折叠床,铺了许多被褥和被子。
一个死人躺在那。
男性,年迈。
逝者张着嘴,上面有凝固很久,变干了的血痂,很大一块。
粘到人中和上嘴唇都是。
东仔看着,这给他清洁会很麻烦。
这血痂应该撕不掉了,强行撕开的话,嘴唇和人中上的皮都会给一同撕下来。
而且这逝者死时应该很痛苦。
他鼻子上插着鼻管,喉咙上也有一个洞,露出水管一样的胶管口。
“他这..这些东西都要拿掉么?”
吴哥见着他身上的东西,对家属问。
“对,要拿掉,那个医生说可以拿掉。”
家属点点头回答。
“确定么,就这两个对吧。”
吴哥贴近看着逝者的喉咙和脸问。
“他胸口那里还有一个。都拿下来,你们洗的时候能不能把他嘴巴上的血擦干净?”
家属接着问。
“这个难度很大啊,已经很久了的这个样子。我们尽量吧。”
吴哥看着逝者的嘴巴皱眉道。
家属有很多人,甚至有个小孩。
已经半夜一点多,小孩也没睡觉。
在一旁打闹,见着吴哥东仔两人准备上手干活了,他跑来站在一旁好奇看着。
这是东仔第二次遇到家庭单。
和太平间有专门的入殓室不一样,就在客厅上做。
哪怕第一次时候,那次的家属都专门腾出房间给他们使用。
因为大庭广众下做这些,多少有些不合适。
何况这次的逝者死去的模样有些吓人。
“咱就在这做么?”
东仔打湿好毛巾问。
“对,家属他们不介意就行。”
吴哥给遗体盖上福寿被道。
“他身上的这些管子怎么办?”
这是东仔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遗体,他不知道这些医疗的东西该怎么拿下来。
“没事,我来就行。”
吴哥小声道。
“他这是做了微创的,医生说把管子拔出来就行。”
一旁的家属听到东仔问的话,连忙回答道。
东仔转回头。
三四个家属都站在那插着手,目不转睛的看向他们干活。
六七岁大的小孩甚至走来,靠在东仔身边看向逝者。
“他死了么?”
小孩指着躺在那的逝者,对身后的大人疑惑问。
声音洪亮充满朝气,没有一点害怕。
“对,死了。”
大人应了声。
“小朋友,你先去房间玩。”
东仔听的皱眉,忍不住对小孩劝道。
“过来过来,哥哥说别过去,别打扰哥哥他们干活。”
一个中年女子拉着小孩站回后面。
开始干活了。
东仔仔细的给逝者擦脸,一旁的吴哥撕掉粘住气管的胶带。
拔出了鼻子上的气管,短短一截,只有五六厘米。
开始解开脖子上的管口。
撕掉旁边的胶带,露出皮肤上的线。
拿起剪刀,拆管口周围缝好的线。
咔嚓咔嚓,黑色的线给剪开,露出一条条线头。
吴哥抓起白色的胶管口,慢慢拔出来。
没有一点阻碍和卡住,极其顺滑。
东仔看着这一幕,他完全没想到管子这么长。
二十几厘米的管,从喉咙里拔出来。
管壁上有层反光的粘液和血迹,吴哥连忙丢到垃圾桶。
“咦~”
东仔听到背后家属发生的厌恶声。
开始给遗体脱衣。
上衣打开后,看见了右胸口上的白管。
同样是线条缝好,一个管口露出来。
同样拔出来后特别长。
每当吴哥拔出气管,东仔都觉得好害怕,那感觉像他们在杀人。
那延续逝者生命,遗留下的东西。
东仔看着剥离扔掉的气管和胶带,都感觉遗体死前是多么痛苦。
右胸口的管子给拔出来。
很长很长,像嵌在极深的肉里。
但管子拔出来,两厘米大的伤口开始冒血。
涌出来,真的是涌出来。
像温泉的水一样,往上冒出血头。
预料这一幕发生的吴哥用手术钳夹起棉球塞进伤口里。
再打上十字胶带。
“准备穿衣吧。”
吴哥连忙道,他知道这血止不住了。
伤口太深了,里面的动脉血管肯定破了。
但五秒都不到,当吴哥话没说完。
那血浸湿了整块胶带,血从胶带的缝隙疯狂流出来。
“咦~你能不能把血给止住啊?”
后面看着的家属见着这一幕问。
“我们尽力吧,这伤口里面肯定是血管破了的,你们又说医生可以拔。”
吴哥吸了口气,忍住脾气道。
开始时候,就跟家属交谈过,这种手术留下的东西,尽量不去动最好。
但他们执意要都拿走。
吴哥说完,后面的家属没说话了。
撕开已经没用的胶带,伤口里的棉球早给染红。
见没办法的吴哥多贴了三四个胶带,每当他贴上一块,一块就发红。
“快,穿衣。”
吴哥见血暂时缓住,他连忙道。
“等下,等下,我们能打开被子么?”
看到遗体衣服脱完,准备穿上。
一个家属举着手机问,他在录像。
东仔这才注意到这个人,这个傻逼一开始就在一旁举着手机。
东仔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才发现他在录整个入殓过程。
“你要干嘛?”
吴哥对着这个看着手机屏幕的人问。
“我们要拍下来。”
那人依旧盯着屏幕,尽量把画面拍到整个遗体模样。
“你拍吧,别拍到我们就行。”
吴哥说。
那逼人没说话,因为肯定拍到他们两个的脸了。
东仔看着这慕,深吸了口气看着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拍照的家属走前,拉开了遗体身上的福寿被。
露出了逝者年迈裸露的身子。
一旁的小孩,好奇跟着走来看向近在咫尺的画面。
遗体身上全是死皮和角质层,一大片一大片白花花,瘦弱的四肢露出骨相,生殖器外露着。
右胸口的胶带彻底给染红,喉咙中间有个深不见底的肉洞,人中和嘴唇上的血痂粘成一块。
老人歪着头,躺在那张着嘴巴,死相痛苦。
东仔不理解家属为什么允许让这么小的孩子看这个画面。
等家属对遗体从上到下拍完后,收起手机。
吴哥示意连忙盖上被子,然后穿衣。
东仔回头看了眼那个拍视频的人,他正发微信说着语音。
周围的家属面无表情,依旧在看他们干活。
“真他妈的奇怪。”
干完活后,东仔和吴哥走下楼。
东仔不理解说,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属。
“好像我们在耍杂技搞魔术,他们站在那跟看表演一样。还让小孩在一旁看。”
东仔说。
“正常的,一般人很少能看见这样的事情。”
吴哥说。
“那个血一直流。”
东仔想到拔出管子后,右胸口冒出的血。
“没办法的,里面动脉破了止不住的。”
吴哥回答。
“估计现在在棺材里还在流,寿衣应该湿了。”
东仔看了眼背后的楼。
“所以当时就弄快点,早点下棺就不会流出来。”
吴哥想起刚刚的决定。
“你说先用棉球堵住,然后滴蜡,再贴上胶带这样会不会止住。”
东仔思考着说。
“蜡?”
“就蜡烛滴下的那种,不溶水而且这天气会很快凝固。”
“公司没这样教啊,按要求来就行。”
吴哥不赞同东仔这个想法。
几人坐上灵车,东仔顺手丢了垃圾袋。
不要乱碰和乱捡路上的衣服,因为说不定不干净。
倒不是鬼魂,就是说不好是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
要碰巧因为传染病死的呢。
两点了,东仔坐在车上,跟在学校的英芳微信语音。
“忙完了么。”
她在手机里问。
“嗯”
东仔看了眼手机,显示通话时长快两个小时了。
“你回学校怎么不告诉我。”
英芳不解道。
“我以为你知道我回去了。”
东仔回答。
“好吧我知道了。我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英芳停顿了会说。
因为明年她就要去美国那边和爸妈生活。
“以后还能跟你打电话么。”
手机里传来声音问。
她为了不吵到室友,躲在厕所里等了东仔两个小时忙完。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哪天想打给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接。”
东仔回答。
旁边开车的司机无声笑的脸都快变形了。
安静中,背后的陈哥吴哥两人默默把拇指伸过来。
东仔看到竖在脸上的两个大拇指,忍住的憋笑。
但实际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
哪怕在暧昧的男女关系里,也从来没骗过谁。
因为这叼毛没谈过恋爱。
一次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