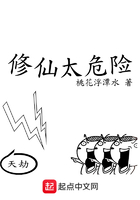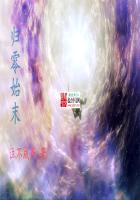薛为忠又淡笑道,
“再者,朝廷也不容易,咱们大明疆域辽阔,哪年没有个水旱虫灾的?”
“皇上虽是真龙天子,但也不是真的能呼风唤雨,为了北方的这场大旱,前年皇上亲自从午门步行去南郊天坛祈雨。”
“依我看,咱们的大明天子做得也够可以的了,皇上如此诚心地祈雨,但老天爷就是不给面儿,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咱们皇上一人不是?”
佟正钊大开眼界,有生之年头一次听见受害者为加害者打抱不平,又暗道这阉割作为中医外科的一项传统艺能,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被正式废止了还真是可惜。
如此优良的一项光荣传统,不但能轻轻松松地让无耻赌徒戒了赌、色中饿鬼戒了色,激发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航海家,还能连绵不断地炮制出一大批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大明百姓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可真是教孛儿只斤氏看了沉默,爱新觉罗氏听了流泪。
“薛叔,您这话我就不同意了。”
佟正钊沉默了一会儿,想来想去还是没忍住,张口便道,
“朝廷救灾,那是应当应分的,自古只有老百姓埋怨朝廷救灾不力的,哪儿有反过来体谅朝廷不易的呢?”
“薛叔,您从前在处州时,你们薛家种地,也勤勤恳恳地为朝廷交过不少税罢?”
“咱们老百姓既然交了税,那朝廷救咱们还不是应该的?咱们现在怎么还要反过来感谢朝廷救灾呢?”
薛为忠一怔,顷刻之后又恢复了方才淡然从容的神情,
“可做人总要知恩图报啊,皇上为咱们老百姓操了这么多的心,咱们总不能还说皇上做得不够好罢?”
佟正钊认真道,
“救灾不力,咱们老百姓为甚么不能说?倘或咱们老百姓动不动就感谢朝廷,觉得皇帝对咱们恩重如山,那朝廷还会反过来替咱们老百姓惜命吗?”
“依我说,朝廷救灾不力,或者说咱们老百姓觉得朝廷救灾不力,那咱们就应该想办法向朝廷‘问责’,一个朝廷连灾都不救了,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薛为忠看了佟正钊一眼,淡淡地笑道,
“你这想法,就快同那妖言惑众的白莲教一样了。”
佟正钊心道,这白莲教从唐宋一直延续到晚清,还真是专业反贼一千年。
“可元末的红巾军中,也不是有不少的白莲教教徒吗?”
佟正钊反问道,
“太祖爷当年,不是也借用了‘明王出世’的白莲教口号吗?”
薛文质在一旁回道,
“这口号早不算数了,太祖爷一称帝就把白莲教打成‘邪教’了,甚么老百姓向朝廷问责,这话就是天方夜谭。”
薛为忠笑了一笑,道,
“朝廷虽然有许多不是之处,但没有太祖爷就没有咱们大明朝,没有大明朝就没有咱们汉人今天的好日子。”
“我虽身为宦官,但不得不说,如果咱们大明没有皇帝,任谁都可以向朝廷问责,那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结果。”
“咱们才过了两百多年的好日子,可不能就忘了元末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悲惨情形啊。”
薛文质附和道,
“正是这理儿,俗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咱们大明就是有千般万般的不好,但咱们老百姓也不能就为了一己之快而诋毁朝廷啊。”
佟正钊瞠目结舌,片刻后方道,
“……我看咱们汉人现在和元朝时过的日子也没甚么区别。”
薛文质面色一紧,厉声诘问道,
“佟兄何出此言?”
佟正钊认真回道,
“我听闻蒙元时,成吉思汗尝颁布过一项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按道理说,这项法令极为不公且大有漏洞,咱们汉人虽不是很能打,但还不至于像驴一样好杀。”
“蒙元治下的汉人们听到这项法令,理应群起反抗,向蒙古人证明咱们汉人和驴有着重大区别才是。”
“可事实并非如此,自成吉思汗之后,蒙元不仅一统天下,对咱们汉人的种种限制甚至还变本加厉。”
“昔年蔑儿乞·伯颜得势之时,还奏请元顺帝杀尽‘张、王、刘、李、赵’之五姓汉人,但即便如此,蒙元依旧统治了咱们汉人近百年。”
“元朝灭亡之时,竟还有不少汉人随之而殉,连一向趋炎附势的曲阜孔氏都一反常态,在元顺帝北驱草原之时竭力挽留。”
“薛兄你说,从前蒙古人将咱们汉人当驴,现在咱们大明将汉人当人,可为甚么元末有很大一部分汉人,宁愿在蒙古人治下当驴,也不愿跟着太祖爷作人呢?”
薛为忠靠在座位上,懒懒地附和了一声,淡笑着问道,
“对啊,这是为甚么呢?”
佟正钊道,
“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智慧了,成吉思汗知道,将汉人直接当驴,是很难被汉人接受的。”
“因此他先不把汉人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一头驴——等到咱们汉人开始自行羡慕蒙古人的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窝阔台和忽必烈的时候,再给咱们汉人略等于驴的价格,咱们汉人便能心悦诚服了。”
“因为这时咱们汉人虽还不算一个‘人’,但究竟已经等于一头驴了。”
“所以仔细想想,咱们汉人在蒙古人治下当了将近一百年的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蒙古人,毕竟咱们老百姓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争取到‘人’的资格。”
“甚么样儿的朝廷都能体谅,甚么样儿的人做皇帝都能宽容,无论谁来都是一样,都是服役、纳粮、磕头、颂圣,无论谁来都可以拿咱们老百姓不当人,这样怎么能获得蒙古人的尊重呢?”
“因此元末那些不愿归降大明的汉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在蒙古人治下已做稳了‘汉驴’,甚至有一部分人,譬如曲阜孔氏,必定是要比其他‘汉驴’更受尊重一些的。”
“这时忽然不让他们作‘汉驴’了,反过来又要倒回去作不安稳的‘乱世人’了,他们又如何甘愿呢?他们若是答应了,那之前‘不被当人’的那段苦不是白吃了吗?”
“所以我觉得,咱们老百姓要想被当人,就一定要先自个儿尊重自个儿,把自个儿看作是个‘纳税人’,而不是天天对朝廷感恩戴德的‘汉驴’。”
“太祖爷当年以布衣之身定鼎天下,就是想把‘纳税人’的权利还给咱们汉人。”
“倘或咱们还跟蒙元时一样,把现在的汉人皇帝等同于将百姓不当人的蒙古人,那咱们汉人现在过的日子,和元朝时又有甚么区别呢?”
薛为忠盯着佟正钊看了一会儿,忽而开口道,
“可秦王的岁禄也是来自于百姓们纳的税啊。”
薛为忠淡笑道,
“你这么说,就不怕我将此悖逆之言告诉秦王吗?”
佟正钊微微笑道,
“薛叔但说无妨,我相信薛叔绝不是那种会在人背后添油加醋的奸佞小人,也相信秦王爷绝不是那种能将人不当人的跋扈宗室。”
薛文质插口问道,
“那万一秦王爷是呢?”
佟正钊笑道,
“若当真如此,秦王便不值得我为其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