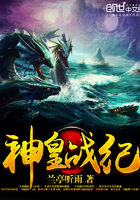任红牛投靠范天门下,纯粹是闲人一个,却领着一份不薄的薪水。他解决了妹妹任红霞的学费,打算到年底翻盖老家的房屋。到白马监狱接一位刑满的同案回来,他对范天说:“范总,我想做点实事。”范天起初与任红牛并不认识,因其麾下力荐,才出手将其狱友任红牛提前弄出监狱的。范天豢养类似任红牛的人不在少数,也不是白养他们,只是没到用人时机。“红牛啊,你每天在公司就是在干实事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啦!”“范总,我个人认为我的价值不在于跟班。”任红牛在卑微之中张扬着个性。“哦!有理想,有前途!”范天饶有兴致地听取了任红牛的思路。那天,任红牛驾着一辆雪佛兰车接到了同案,点了一大盆刚上市不久的十三香手抓龙虾,另加冷盘和小炒共十二道菜。同案瞪圆了眼睛垂涎那通体鲜红的大龙虾,迫不及待地抓着龙虾啃起来。风卷残云,一顿大吃大喝后,他们到洗浴中心泡了澡,散了架地躺在软榻上,贪婪地吸着香烟,面对同案羡慕的眼神,任红牛羞愧地说:“惭愧啊!兄弟我是寄人篱下,光蛋一人。”“牛哥,有车玩有饭吃日子过得舒坦啊,哪儿找去?”同案说得眉飞色舞的。“看你那点出息。”任红牛破口大骂。
“牛哥,你还想做几票么?”同案凑上来,神神秘秘地问道。“如今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去抢劫。”任红牛不屑地望着同案。“一没路子二没本钱,牛哥你说怎么做生意啊?”同案眨巴着眼睛,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发财的招。“我找到财路了,白马监狱。”任红牛得意地仰望着天花板,吐着烟圈。“和白马监狱做什么生意啊?”同案伸长了脖子。“你别问那么多,跟着我,有财大家发。不用资本不要脑筋也可以挣大钱。”任红牛沉浸在发财幻想之中。“我早就知道跟着牛哥就是有财发。”同案乐得要叫任红牛亲爹。和同案歇息了半天,任红牛才赶回家里。任母挑着担子拎上锹,艰难地穿过围观的乡邻回到自家院子,对着接担子的儿子说:“劳改队来过两次了。”“他们是走过场,不会动真格的。下次劳改队来人你们不要理他们!”任红牛放下担子,掏出三千元钱塞给母亲,抬头仰望低矮的屋子,说,“妈,我打算到年底盖座新楼。”“好哦!”任红霞拍手欢快地说。“你在外面少惹事我就阿弥陀佛了。”母亲小心翼翼地揣好票子,平静地说了儿子一句就要去厨房,“喝水自己倒啊。”“妈,你放心,儿子再也不会吃官司了。
”任红牛心里酸酸的,像只温顺的小绵羊,轻言细语地回答。“你走正道我才放心,不跟你说了,我要做饭了。”母亲推开破旧的茅草屋顶厨房门。如今的任红牛却再也咽不下家中一日三顿不见荤的饭菜了,找了借口就走。上车前,他摸着妹妹的头叮嘱:“好妹妹,好好学习,争口气啊!”趁着夜色往回赶的路上,任红牛琢磨着怎么向老板范天开口。案发前,任红牛曾经打劫过一个药材商。打劫之前,他在掌握了打劫对象行踪规律的同时也了解到药材的巨额利润空间。入狱后,他在刑满后继续干老本行还是走正轨的抉择中多次考虑过药材生意。出狱跟随范天的日子里,受范天公司贸易交易方式的启发,联想到白马监狱浩瀚的土地面积和监狱系统为生存饥不择食四处出击寻求合作的窘境,他认为监狱的钞票最容易赚,至少能捞到白马监狱的钞票。于是,他决定再次走一次打劫路线。征得范天首肯,任红牛将同案约到省城,买了一款崭新的诺基亚手机送给他。“谢谢牛哥!”同案贼眉鼠眼地背着任红牛玩弄起手机。任红牛不由得皱起眉头:谁会相信同案是生意人?更蒙不了监狱人。他领着同案出入正规场所,训导他的言谈举止。
他自己呢,站在镜子前,努力地用微笑挤走凶悍。培训了几日,任红牛将同案引荐给范天。范天文质彬彬,却有股无形的震慑力,刚才还是昂首挺胸的同案忽地哈下腰,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就是不敢正眼瞧范天。因为中午喝了几瓶百威啤酒,憋不住了,同案一溜烟地去上厕所了。“你带他做生意?不是打劫,也是诈骗。”范天笑着说。“范总,他……”任红牛尴尬地要解释。“红牛,你别说了,我给你装点门面。”范天安排了一名资深业务经理听候任红牛的差遣。业务经理面相斯文忠厚,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让人看得踏实。春末,骄阳似火。站在大街上的任红牛被摩天大楼幕墙玻璃的强烈反光刺得睁不开眼,便走进一家眼镜专卖店,为自己挑了一副范思哲眼镜,同案戴着花花公子太阳眼镜对着镜子是志满意得。途经一家茶社,同案说口渴。“先生,请!”迎宾小姐殷勤地招呼着客人。农云红见有客人来,便立刻停止了与弟弟农云东的谈话,招呼客人。此时的农云东已经如愿地调任副教导员了。“兄弟,你喝点什么?”任红牛选择了一个靠近窗户的台子坐下。“小姐啊,给我们来两杯碧螺春。”同案说。“建议先生上一壶碧螺春。”小姐殷勤地介绍。
“什么价格啊?”同案摘下碍事的眼镜。“二十八块一壶,加一只杯子十块。”望着贼眉鼠眼的同案和皮笑肉不笑彪悍的任红牛,小姐的声音不太自然了。“小姐,这是碧螺春?炒青差不多,蒙我们呢?”同案凑近送来的玻璃壶,唤回小姐。任红牛也觉得茶叶质量很差,冷眼观看小姐。“这就是碧螺春,没蒙您。”小姐赔着笑脸。“骗人骗到老子头上了?”同案抬高了嗓门。“先生,要是认为茶叶不如您意,我们可以为您更换,或者,您认为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别看任红牛两人一身名牌,自打他们进门起,农云东就一眼看出他们不是善良之辈。再看发型,那分明是犯人刑满前留下的痕迹。现在该他出场了。“我问你,这是不是碧螺春?”同案没买农云东的账。“到此为止!你在里面还没得喝呢。”任红牛觉得老板态度不错,对同案说道。“要不是看在牛哥面子上,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同案余怒未消。“你少给我惹事!”任红牛低声呵斥了同案,对农云东说:“老板,我兄弟不懂事,别见怪啊!”谁知同案嘴皮还硬朗着:“怕什么!”农云东听得真切,果然是刑满释放人员,对于同案的蛮横,怒从心头起:“你是哪根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刚出来是不是?你睁开眼瞧瞧,老子就是管你们的!”同案立刻被唬住,用眼神向任红牛求援。血管开始扩张,肌肉在跳动,任红牛攥紧了拳头,问:“你是警察?”“正是,监狱警察。”“啊?”同案一哆嗦,为自己刚才的鲁莽后悔不迭,将头埋下。任红牛将眼镜摘下放进上衣口袋,卸去笑意,挂上往日的杀气:“劳改队破警察神气什么?我立马将你的店砸了,你信不?”农云东想他今天遇见了难剃的刺头了,刚才的优越感一下子全没了,既然报了名号,不能虎头蛇尾,便硬着头皮回击:“小子,你敢!”“是吗?”任红牛突然怪笑,缓慢地提起玻璃杯,在农云东眼前晃晃,一个抛物线,茶壶飞向吧台酒柜。立刻,哗啦声一片。一直坐在吧台里的农云红早看出不妙,正准备报警,头上玻璃酒瓶的破裂声吓得她扔掉电话缩到吧台下面。侍应人员纷纷往外溜。任红牛又抄起杯子,呆愣的农云东一朝醒悟,本能地上前夺杯子。任红牛左手一划拉,农云东一个趔趄,杯子又砸到酒柜里林立的瓶子中,又是一阵叮叮当当声。农云东站立身形,扑向任红牛。任红牛一个侧身,顺手一带。“扑通!”农云东一头栽进桌底。“还不快逃!”任红牛拉着呆若木鸡的同案挤进狼奔豕突向外逃的客流中瞬间窜出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