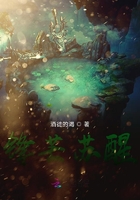“奉太子殿下教令,因刑部工作日渐繁重,刑部右侍郎年久空缺,今特将兵部右侍郎宋滢方改任刑部右侍郎。”
虽然滢方早已从萧旻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但直至此时教令下来,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慢慢地,慢慢地融入这个朝堂。
不过,她还是摸不透萧旻的意思。
萧旻当时只说了,皇上当初任她为兵部右侍郎,如今他将她改任成刑部右侍郎,也算是六部间平调,不会有人提出意见。至于其它,萧旻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滢方还是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刑部另有玄机?
滢方被宋枭抓着问了一番,她老老实实地把萧旻的原话复述给他,他听完之后也没说什么,就让滢方退下了。
滢方从宋枭的院子里退出来,立刻吩咐跟在身后的宋启,邀刘子异来府中一趟。
当初她请刘子异做幕僚,为的就是这一刻。
滢方走在廊檐下,忽闻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声笑语,宛若莺啼。她转了个弯,迎面看到了正在和丫鬟说话玩笑的宋湘,不同于那日在宋枭面前的安静乖巧,她的声音清脆,笑声爽朗,拥有着她这个年纪与生俱来的朝气与活力。
其实说来也稀奇,明明身处同一屋檐下,除了之前在正厅里的匆匆一面,这是滢方重生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与宋湘正式会面。
滢方率先看到宋湘,等到宋湘不经意间抬头,忽然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滢方,顿时慌乱了神色,忙假装没看见准备折返回去。
滢方哪能如她所愿,扬声问道:“妹妹这是要去哪里呀?”
因为无法忽略掉滢方的声音,宋湘遂装做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慢慢向滢方走过来。
她今日穿了件桃红间银白吴棉衣裙,梳着双平髻,头发上别着绯色绢花,娇俏可爱,脸虽还青涩,但已经能看出来长开后定是个花颜月貌的美人了。
面对滢方,宋湘又恢复了在宋枭面前怯怯诺诺的模样,微微福身做礼,继而腼腆笑道:“父亲说今日要查我的女工,因此连着做了三天,缝了几双冬日穿的足衣,也不知道父亲穿着是否合适。”
滢方心中怪异,检查女工这种事情一贯不是赵氏做吗,宋枭一个大老爷们,对女工一窍不通,为何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
滢方把目光投向丫鬟阿岚手中端着的木托盘上,她拿起来看了看,三双白色的羊绒足衣,里侧绣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宋”字,用针细密,针脚处也不见线头什么的。
滢方自小在女工上没什么天赋,显而易见,宋湘绣得比她好上许多,这倒让滢方有些意外了。
把足衣放回托盘,滢方见宋湘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故意逗弄她道:“你绣工既然这么好,得空了便帮我也做几双吧。”
“啊。”宋湘愣了愣,像是真的被吓到了,随后扯了扯嘴角,道:“自然是可以的。赶明日哥哥让小厮告诉我尺寸来,我立马帮哥哥做。”
“那便谢谢妹妹了。”滢方心里直发笑,宋湘还是太小了,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心里想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看出来了。
“哥哥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宋湘指了指滢方身后的方向,不好意思地笑道:“父亲还在等我,就先与哥哥告辞了,若是有空改日再聊。”
滢方点点头,嘴里的再见还未说出口,宋湘就逃也似地从她的身侧绕过去了。
滢方回头,看着宋湘慌慌张张离开的背影,笑着叹了口气,她又不是豺狼虎豹,怎的跑的这样快!
她回静心院的时候,刘子异已经候在了书房门口。她忙邀刘子异进去坐下,沏了上好的茶叶伺候着,她实在是有非常紧要的事情问他。
目光不经意间地一瞥,滢方看到了刘子异玄色袖袍上的一滩污迹。
刘子异也意识到了她的注视,脸微微有些红,拂了拂袖子,道:“李员外新建宅邸,适才邀子异帮其院落题写对联,一不小心沾了些污迹,见大人叫得急,也未来得及回家换套衣服便赶来了,实在是失礼。”
滢方忙摇头道:“这有何失礼?刘先生学识渊博,能得刘先生相助,滢方之幸也。”
有官员专找刘子异写对联,不就说明了她的眼光没错,刘子异是有才之人吗?
“能为大人所用,才是子异之幸也。”刘子异的目光真诚,虽然一开始他因为京城流言轻视于滢方,但从这些日子的相处中,他看到了滢方身上的谦虚和好学,也从滢方身上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体谅和尊重,他为自己之前的浅陋感到惭愧,也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听信坊间谣言。
滢方被刘子异盯得有些不好意思。自她成为了宋滢方,方方面面受到男子碾压,她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如今每日都自怨自艾,刘子异的这句话让她多多少少受到了鼓舞。
她轻声咳了咳,言归正传,将自己改任刑部右侍郎的事情告与了刘子异。
果然,刘子异沉吟片刻,黑眸在某个瞬间犹如流星划过天际。
滢方忙问:“先生可是想到什么了?”
刘子异并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反问道:“大人,今日您上朝,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又或者说,不能理解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或者不能理解的事情?”滢方喃喃道,她撑着脑袋想了好一会儿,才踌躇着说:“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太子在朝中的威望好像……并不是很高。”
“怎么说?”刘子异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滢方纠结了一阵,妄议太子可是要杀头的。但刘子异向来性格孤傲,应该不屑于做出那些等小人行径。况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在刘子异似是鼓励的目光下,滢方索性心一横,将今日所见所感全都说了。
“我不明白,在这种皇上不理朝政,太子总揽政务的情况下,不当是太子的威望最高吗?但今日诸臣谈及逐流民出城的事情,摆明了是想打太子的脸。而且这个提议如此不仁不义,却有一大帮的人支持,站在太子一方为他说话的却寥寥无几。若不是魏清野最后拿出的那份奏折,恐怕太子就真的会向他们妥协了。”
刘子异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道:“那大人觉得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打太子的脸呢?”
滢方心一惊,她没想到这样的话会从刘子异的口中问出。她一直以为,刘子异虽然满腹经纶博学多才,但他骨子里还是个规规矩矩墨守成规的文人,这一问,倒让滢方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但这样的惊讶并没有持续多久,滢方的思绪就被正事拉了回来。究竟是谁想让太子下不来台呢?
她记得自己曾向刘子异讨教学识时,刘子异说过的一句话,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人们总是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所以归根究底,还要看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是谁。那么,这件事究竟对谁有利?
二皇子萧珏!滢方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这个人。上朝时她就觉得萧旻问萧珏的那句话很不一般,萧旻心里肯定是明白的,所以才有此一问。
她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脑袋转得飞快。
这件事定是跟夺储之争有关!
当初皇上册封太子时,皇后还是萧旻的生母曲涟漪,萧珏的母亲蓝溯光是当时的贵妃,曲涟漪去世后,蓝溯光过了两年才被册封为皇后。但不同于曲涟漪出自小门小户,蓝溯光父家和母家均是江南一带的豪门望族,势力极大。萧珏本就年长,其母又是当朝皇后,势力滔天,怎会不生异心!毕竟一切还没有盖棺定论。
滢方只觉得瞬间柳暗花明。
她并没有说出那个名字,只是问刘子异:“看目前的形势,太子处于劣势,可这和我调任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太子想让我为他所用,但为什么不让我仍留在兵部,而是选择了刑部?”
她隐隐觉得,刑部没那么简单。
刘子异笑着摇头,“大人此言差矣,太子并非处于劣势。”
“哦?”这倒让滢方不懂了,难道太子身后有什么隐藏实力不成?
“大人,你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吗?”刘子异浅笑,有种谋士的运筹帷幄。
滢方摇头,“自然不是,黑白相交即为灰。”
滢方刚脱口而出,瞬间一点就通。她看向刘子异,对方轻轻地点了点头,似是印证了她心中的那个想法。
朝堂之上,并非所有人都会站队,相反的,在局势如此不明朗的当下,大部分人都是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只要不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仍旧会本分地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为正统的当权者——太子办事。
刘子异见滢方倒也不算愚笨,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为滢方解释道:“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被合称为‘三法司’,凡有重大案件,皆由这三法司共同会审,俗称‘三司会审’。杜明庭掌管刑部,钱恪和李守义掌管都察院,秦伯渊掌管大理寺。”
“秦伯渊和钱恪都是二皇子的人。”滢方道。今日上朝,提出要逐流民出城的就有他们二人!
刘子异颔首,顿了顿,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李守义虽才华斐然,但行事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所以都察院的大小事宜还是要经过钱恪。至于杜明庭,他也算是两朝元老了,为人倒是正派,光明磊落,铁面无私,但其下的刑部左侍郎廖元也倾向于二皇子一派。”
“所以你的意思是,除了刑部,其他二法司均被萧珏所掌握?”
刘子异再次点头,“杜明庭年迈,不知何时便会告老还乡,太子很有可能就是怕杜明庭一走,整个国家的司法全部落入萧珏手中。”
“可是左侍郎的权利向来大过右侍郎,即便杜明庭走了,也应是廖元接替他,又何来我的事情?”
纵是萧旻想让她当这个刑部尚书,也没那么简单。
刘子异捏着梅子青茶杯,鲜绿的茶叶在清水间微微荡漾,他幽深的眸子投向了窗外,声音有些缥缈:“要是这廖元不在了呢。”
滢方发现,刘子异虽然平时看着一本正经,但谈及朝政时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清瘦的脸上绽放着异样的神彩,让人挪不开眼来。
她有些好奇,不自觉地问了出来:“刘先生如此有才华,为何屡次考试不中,难不成是因为没有银钱打点?”
假若真是如此,她不介意帮扶他一二。
刘子异刚刚还和颜悦色的脸瞬间冷了下来,他敛下眸子,“不是。”
滢方见刘子异这副态度,知道自己问错话了。或许这件事背后另有隐情吧。只是刘子异不说,她也没必要自讨没趣。
刘子异本是滢方突然间叫过来的,他还有事在身,滢方也不好再拖着他的时间问些其他的事情,于是亲自送刘子异出府。
刚出静心院没走几步路,滢方迎面便撞上了一个模样有些熟悉的婆子,她神色匆匆地说:“少爷少爷,不好了,姑娘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滢方的心登时提了起来,刚才她见宋湘的时候还不是好好的么?一眨眼的功夫,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婆子看了滢方身侧的刘子异一眼,踌躇着不知当说不当说。这都是些府里的内宅之事,如何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去。
滢方会意,转头对刘子异道:“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府里还有要事处理,就不送先生出门了,望先生见谅。”
刘子异自然懂得这些高门大户的规矩,躬身作礼,“那便与大人告辞了。”
滢方遣了宋启,让他把刘子异送至府外。遂跟着嬷嬷一起去宋枭那里了。
在路上,滢方仔细向嬷嬷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下了然。
宋湘原有一奶娘,叫做苏妈妈,孤儿寡母,三年前去世了,留下孤零零一子,名曰苏臣,与宋湘年龄相近。宋湘常借了由头出府见他,前几天东窗事发。当时宋枭忙,没时间收拾她。他也怕事情流传出去坏了名声,所以故意拿女工这事开刀。宋湘也是脑子糊涂,本不擅长女工,为了应付宋枭,让屋里的丫鬟替她做,正撞在风口浪尖。
滢方了解宋枭的脾气,他现在正在气头上,谁撞上去谁就倒霉。但赵氏适才用过饭便回了娘家,明日才可回来。这府中能为宋湘说话的,也唯有她一人了。虽说她与宋湘并没有多少感情,但就算看在赵氏的面子上,她也要为宋湘争上一争。
滢方到了院外,好几个身形粗壮的护院挡在门口不肯让她进去。好在她是主子,即便是硬闯,也没人敢伤她。
“你这个孽障!”
宋湘跪在地上,只听一声怒喝,一个巴掌就从上方落了下来,她下意识地脖子一缩,闭上了眼睛。
没有预想中的疼痛。
“父亲这是在做什么?女孩子如何能够伤及到脸?”清亮的声音出现在上方。
宋湘抬眸,只见滢方站在她的身前,一只手将父亲的手给挡了下来。她的身形并不算大,甚至在宋枭面前显得极为瘦小,但有那么一刻,宋湘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就像从天而降的神祇一样,身形无比高大。
“谁让你来的!这里没有你的事,快给我滚开!”宋枭勃然大怒,竟然敢违逆他,谁给她的胆子。难不成是因为今日上朝了就胆大了不成!
滢方缓和了语气,试图抚平宋枭的怒气:“父亲,湘儿还小,做什么事情心思单纯,您就消消气,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找您商议。”
“能有什么事情,你不就是想帮她开脱吗?”滢方难得的妥协让宋枭的怒气缓了缓,但脸色依旧青黑。
“湘儿做错了事情,父亲罚她是应该的。要我说,就让她跪上三天祠堂,三个月不许出门!”滢方先是故作恼怒地瞪了一眼宋湘,然后对宋枭继续道:“父亲,孩儿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找父亲商议……是关于太子殿下的。”
最后几个字,滢方压低了声音。
闻言,宋枭看了滢方一眼,果然冷静了不少,他转头对宋湘道:“你就依你哥哥所说,去祠堂跪着吧,要是以后还让我发现你跟那小子来往,我就把你打死在宋家的祠堂上!下去吧。”
宋湘立刻抹了抹哭得通红的眼睛,起身离开了。
滢方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她将刚才和刘子异所说的又说与了宋枭,宋枭面色平静,应是早就想到这一层了。他虽是武官,可也不是那种无谋无略的,很多事情他都看在眼里,只是选择置身事外罢了。
刚才刘子异走得匆忙,有些事滢方还没来得及问,如今和宋枭敞开了谈,她索性问他个明白:“父亲,如今太子似乎是有意扶持孩儿,孩儿已被视为太子那边的人,孩儿既不敢忤逆了太子,又不想连累父亲和宋家,以后该当如何自处?”
“这有何妨,太子本就是正统,为太子办事是我们的本分。不过……”宋枭沉吟了片刻,道:“在外你我仍旧要像京城传言那样父子不和,要把这个传言坐实了,这样即便太子登基失败,你也不会累及宋家。”
滢方心里冷笑,宋枭根本不担心她的安危,只怕她累及了自己和宋家!
回到静心院后,滢方马上问阿毓:“我和湘儿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滢方早就发现了,宋湘看她如同豺狼虎豹,走路都要躲着走,若是中间没什么故事,她可不信。
阿毓望着滢方欲言又止。
滢方叹了口气,道:“我的好阿毓啊,你也知道,自我伤好之后性情大变,我想对湘儿好一点,肯定要先弄清楚,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她吧。”
阿毓看了一眼滢方,慢吞吞道:“也不是什么大事。”
滢方坐在罗汉床上,悠悠地倒了一杯茶水喝,静等着阿毓的下文,怎知她的下一句话,直接让她将嘴里的茶水吐了出来。
这还不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