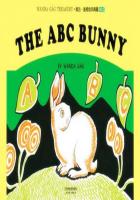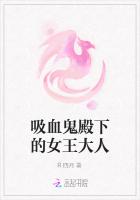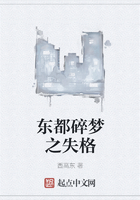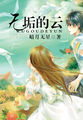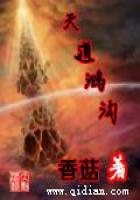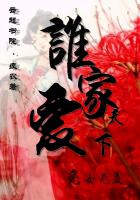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远行。第一次坐卧铺。第一次吃碗面,之前的方便面都是袋装的,三鲜伊面、华丰伊面,从没见过带碗的这么方便的方便面。
1994年9月,我去南京上大学。
火车上,陪伴我的是暑假刚刚买的黑皮箱,我睡一会儿抬头看一下,怕被小偷拎走。箱子里有我从家乡带的一包黄土,是从老家院子里挖的。闻着它,我想起了门前高高的白杨,想起了用嘴含我们裤子和我们撒娇的大狼狗,想起了每天中午的袅袅炊烟和油泼辣子声,想起了房子前后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想起了爸爸妈妈妹妹弟弟,他们此时在做什么呢?
衣服、裤子和皮鞋都是新买的,上衣别了好几个别针,家里人只要出门,妈妈都会在衣服上别一个大大的别针,说是辟邪。短裤是红色的,期望大吉大利,缝有口袋,装着报名的学费。
时间走一秒,离家远一步。
要见到他们,得等到寒假,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过家。
窗外下起了雨,打在车窗上,像无数行眼泪。坐在车窗里的我,眼泪流下来,像打在车窗上的雨。
到南京是第二天下午5点多,到浦口校区天已经很黑很黑了。夜里,想着千里之外的家人也在想着我,眼泪弄湿了被角。
每周给家打一次电话,每一次打电话都想哭,每一次电话几乎都是妈妈接的,她和我说一会儿,然后让爸爸和我说,接下来是弟弟妹妹,每个人都要说上几句,妈妈最后总结。我一封接一封地给家里写信,给老师和朋友写信。妈妈认字不多,也许从来没写过信,但她还是拿起笔,一笔一画地给我写,好多字她都不会写,我弟弟妹妹写在另一张纸上,她誊抄下来。妹妹在信里说,她最恨火车了,火车把她哥哥给拉走了,她又对火车充满了希望,希望火车早日把哥哥拉回来。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阅览室,我可以在里面连续坐6个小时,不吃一块饼干,不喝一口水。我还喜欢逛学校门口的小书店。我喜欢看怀念故乡的书,把怀念故乡的古诗抄写在日记里。每天下午我都要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从西边落下去,西边是我的家乡,我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他们还在外面忙碌着,还在一点点儿地挣着钱,而我们已经开始吃晚饭,有人在楼上喊要去洗澡了。
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周年,老乡会组织游览雨花台、夫子庙,有的景点有的人去过,不想再去,后来就分手了。我一个人去这几个景点照相,这是我来南京第一次照相,面对镜头,我对自己说,终于上大学了,一定要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把学习搞好。我把拍的所有照片都寄回家,我妈妈看到后,一定更想我了。
我没想到我会被评为“全国十佳文学少年”,上了大学,觉得这个奖已成为过去。母校老师来南京,是我去火车站接的,说了近两个月的普通话,突然又要说方言,少了在家乡的流畅和亲切。那是我第一次吃那么好的菜,第一次住那么好的宾馆,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南京西站,我送老师上火车,感到愧疚的是颁奖期间,我和老师说话不多,但是他送我的笔记本我一直没舍得用,上面写着:学五车书,储八斗才,凌千载志,成一家言。
这四句话,若能实现其中任何一个,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张巡天和我同屋,我们两个经常结伴去城里买书,两个人都不喜欢说话,为了打破沉寂,我经常没话找话,可是没说几句又结束了,还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新街口,我们买哈密瓜,说好一元一块,交过钱,刚咬一口,老板说,过来过来,我们很纳闷,他指着木板上的字说,你们吃的是大块,大块3元。原来他用一个小箱子把“大块3元”这几个字盖住了,我想跟他理论,张巡天说算了算了,我们只好再给他4元。我上学期间,《扬子晚报》多次披露这一欺诈行为。但是,听南京的人说,到现在也没彻底解决,这些人真给南京丢脸。
我经常穿着黄军装,穿着妈妈给我做的布鞋,背着仿军用书包。我喜欢吃辣椒,食堂里再辣的菜我都还要放自己从家里带去的辣椒。我在学生会里有很多职务,因为要学英语,我一一辞去。我想自费办《新南大》报,我口袋里并没多少钱。南京也下雪了,南京的雪和家乡的雪并没什么区别,我想起了小时候堆雪人。南京的冬天很冷很冷,也没有暖气。我和同学坐公交车去很远的一个服装市场买军大衣,想晚上盖在被子上,钱没带够,空手而回。
终于盼到放寒假。
在火车上,高我们一级的系友兼老乡从另一节车厢过来看我们,谈着系里教授们的掌故,说着一些很好玩的话题。我们应该说家乡话的,我们却没有说,好像。
那天,我穿着西服,系着一条10元还是15元的领带,我觉得挺傻。西服我再没穿过,领带我也再没系过。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少妇,她怀里的孩子一直看着我们说话。孩子现在该有十多岁了吧,再过几年,也是大学生,也会在回家的路上和他的老乡说话。
我们同学中有不少人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小孩子开始叫我孙叔叔了。我一边答应,一边感叹,时间哪,你能不能慢一点儿走。
写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