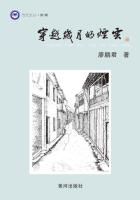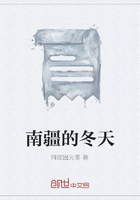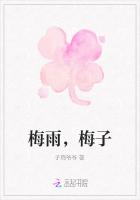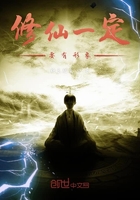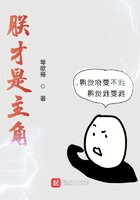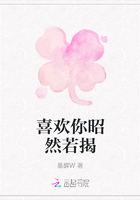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不只是纪念那场激情飞扬的学生运动,更不只是纪念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回首90年前的历史脉络,时代的足迹清晰地呈现出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为完成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变革。可以说,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运动,而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谈论五四,就不能不认真考量陈独秀作为一名文化先驱的价值,在这场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创办《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就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派也大异于别路人等。
1916年,自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更注重它的格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新青年》对域外文化思潮十分敏感,在引介上问题意识很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这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陈独秀得二人推荐,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这一年,陈独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劝胡适归国;二是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当时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等。到了1918年,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欧阳予倩等人加入进来。
《新青年》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舞台,胡适趋之于前,鲁迅急行于后,陈独秀自己,则在前后间摇旗呐喊。中国旧学的陈腐东西,在这里崩塌了;而许多新观念、新思维,许多精神上的新题,都在这里登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由此开始。
所有照片都没有笑的
1879年,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他生活在一个家教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仍依稀可以辨别出来;至于大哥传给他的,大概可以说成是中国人的良知。
陈独秀很小就中了秀才。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写到了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段,文中描写了一位“今科必中”的先生,结尾处这样写道:“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十几年后的行动。”这一次落第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
陈独秀没有留下多少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少之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同时代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也都很简单。
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了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
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也是朋友们的共识。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写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先生本来是旧时代的子弟,少年时就名声在外,言辞犀利冷峻,且喜欢独断专制,性格狂狷不能包容他人,旁人也难以包容他。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和章秋桐、张博良、谢晓石等人办《国民日报》时,和章秋桐蜗居在昌寿里的一栋偏楼上,两人共同执掌文笔,足不出户,不拘小节,不洗头不洗脸,没有衣服换洗了也不管。有一天早晨起来,章秋桐见陈独秀黑色上衣敞开着,胸口有星星点点的东西,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章秋桐惊骇问道:“你怎么了?”陈独秀先生自己看了一眼,平静答道:“虱子罢了。”他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竟然如此。
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笑的,全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他其实也有很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中动人的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
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台静农、胡适等,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
开启文化的新路径
陈独秀不仅关联着沉重的中国政治史,也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他在中国写下了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其作用只有鲁迅可比。
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已近中年,然而他所写的文字却毫无暮气。在陈独秀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很多,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其重要特点是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都锋芒毕露,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评议》《偶像破坏论》等,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至引起激烈争论。
细看陈独秀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也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颓废黯然的文章。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
不过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有情调,气韵有唐诗的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具文人本色的。如《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可清晰地感到他内心的柔情。这也让我联想起他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
我有时读陈独秀的书,常会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可是后来我才恍然感到,用单一的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挑战的。(撰文: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