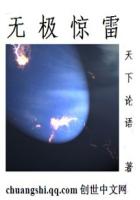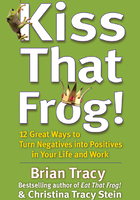宣启二十六年,北禹国主齐继远病入骨髓,已是无力回天。
皇榻旁,一锦罗玉衣的女子坐在榻边看着齐继远,柔声轻唤到:“圣上……”
齐继远微微睁眼,看到眼前的女子,有气无力地说到:“是幻儿啊……”
这女子名为幻玉,是齐继远的贵妃。生得玉软花柔,耀如春华。
幻玉乃是宣启十八年入的宫,那时,她正是娇艳如花的年纪,齐继远亦未曾如现在这般病痛缠身。
齐继远心中,总觉每每与幻玉在一处时,自己也仿佛就似少年一般,所以,对幻玉可谓是爱不忍释。
如此,这幻玉虽进宫没几月,便已是宠冠后宫荣耀加身。
幻玉将齐继远扶起,为着让齐继远靠的舒适些,便将软垫置于齐继远腰后。
齐继远长出了一口气,道:“还是你细心些。”
幻玉清喉娇啭:“臣妾能侍奉圣上,便是三生修来的福报,不敢不细致的。”
皇榻侧边,一直有一小侍女端着托盘,托盘上放着一精致的小碗,紧挨碗边的,是一汤匙。
幻玉伸手,小侍女立即将那碗递到她手中,见幻玉将碗换了手,又赶忙递上汤匙。
齐继远说:“幻儿,这药本就苦涩难咽,这一勺勺喝下去,倒不如全部灌下得痛快。”
幻玉听罢,面容虽忧虑,却还是将汤药碗递与齐继远。
她怕齐继远端不稳,便一直将手放在齐继远端着药碗的双手下方护着。
齐继远服罢药,由幻玉扶着,缓缓靠在了软垫上,幽幽说:“这边境战事终是停了。”
幻玉道:“圣上,这南麒新任的国主,倒是要比那老国主精明许多。谁曾想,他竟提出半月后要来我北禹。这南麒与北禹,终于可以尽释前嫌了!”
齐继远说:“若北禹能与南麒重合于好,那便真真是幸事一桩……咳咳咳……”
说到此处,齐继远咳了起来,幻玉赶紧上前用手反复抚着齐继远的后背,神情很是忧心。
齐继远以手掩唇:“寡人……咳咳……怕是……没几日了……咳咳咳……”
幻玉听罢当即梨花带雨道:“圣上怎能讲这样的话?幻玉深信圣上定会寿与天齐!若是这苍天真想将您收去,那便让幻儿替圣上……”
齐继远摆了摆手,打断了幻玉:“幻儿莫要说这些浑话,寡人答应你,定好好活着!”
幻玉听罢,当下破涕为笑。齐继远吃力地将幻玉抱在怀中,心内却很是欢喜。
三日后,便是易王齐镇辰的生辰,此时齐镇辰,正牵挂着自己的母亲,食不知味。
齐镇辰的母亲,是北禹国主齐继远的贵仪,名叫元菱。
元菱其人,人淡如菊,事事不争。虽进宫数年,恩宠却极少,仅育有一子,便是齐镇辰。
这件令齐镇辰心揪的事情,需从半年前讲起。
半年前的一日,不知齐继远怎的了,竟去了元贵仪的怜双殿。
元贵仪本以为只是国主一时念旧,才来了自己住处。哪知这齐继远日日都来,一住便是七日。
元贵仪很是不解,为何这圣上日日都来,却是鲜少与自己交谈,可是又不走。
直到元贵仪被诬陷偷了幻玉宫中的碧玺花簪,才知晓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某日清晨,齐继远醒来后,便习惯性地,在睡在身旁的幻玉额头上轻轻一吻。
日日如此,只那日不同。
齐继远吻罢幻玉后,幻玉似是还在梦中,娇嗔地说了一句:“好元儿,别闹了!”
齐继远大惑,心想,这幻玉日日与他在一处,未曾听说过这元儿是何人。
难不成是这贵妃对他做出了不忠贞之事?
可是当他正想叫起幻玉对质时,却又怕了。
齐继远已是将所有的真心都系在了幻玉身上,若确有其事,难不成要亲手治爱妃的罪?
齐继远心乱如麻,无所适从。想起元贵仪处最是清静,便去到怜双殿一住就是七日。
国主七日未踏进过贵妃宫中,下人们纷纷在背后议论,猜测定是贵妃与国主离了心,所以不再受宠。
幻玉听闻此事后,甚是不解,却奈何宫中女子若是嫉妒争宠乃是失德,也不好发作。
第八日清晨,终于耐不住性子的幻玉佯装染疾,差人去请了圣上。
齐继远这情种听闻后,衣都未更,披了件挡风的斗篷便急急去了贵妃宫中。
齐继远来到贵妃的寝殿中,见到贵妃珠泪涟涟的模样,好不心疼。
“圣上,幻儿不知犯了何错,竟让圣上如此厌恶?”
齐继远终是没忍住,问到:“元儿是谁?”
“圣上怎知晓元儿?”幻玉听罢很是疑惑。
“那日晨起,幻儿在睡梦中,就唤了这'元儿'。”
“圣上,元儿是臣妾孩提时,母家园中豢养的猫儿的名字!那猫儿憨态可掬,甚是惹人怜爱。它时常会趁幻儿熟睡时,跳上榻来!”
齐继远听罢后大喜!一把将幻玉揽在怀中,口中不停道:“竟是这样!竟是这样!原是寡人错怪你了!”
如此,贵妃便轻而易举地复了宠。
第二日,贵妃请了元贵仪到自己宫中一叙。
元菱方踏进殿中,幻玉连忙上前相迎,似是见了故人一般,一见面便握住了元菱的手,满脸欢喜地说:“姐姐,你终于来了!”
元菱稍显局促,连忙行礼:“臣妾给贵妃娘娘请安。”
幻玉将元菱搀起道:“姐姐这几日照顾圣上,定是辛苦坏了!”
“娘娘,嫔妃侍奉圣上乃是应当,臣妾不觉辛苦。”
幻玉转而对小侍女说:“呈上来吧!”
只见那小侍女往殿外去了一小会儿,回来时,手中拿着一锦盒。
幻玉起身,从小侍女手中拿起锦盒,打开后,从内里拿出一支碧玺花簪。
这花簪做工精细,上面镶嵌的五彩晶石更是光艳夺目。
“姐姐,这碧玺花簪,是我专门命工匠为姐姐打的。姐姐,你瞧瞧,可还称心?”
元菱赶忙起身,边行礼边道:“贵妃娘娘这赏赐太过贵重,臣妾无功受禄,心内甚是惶恐!”
幻玉倾身,将那碧玺花簪插在了元菱发间,笑着说:“姐姐侍候圣上有功,只得这花簪,倒是委屈姐姐了呢!”
说罢,幻玉将元菱扶起道:“姐姐,咱们同为姐妹侍奉圣上,自当是互相照拂,姐姐勿需如此客气的。这日后,常来常往才好!”
元菱从贵妃宫中回到怜双殿后,将那碧玺花簪取下后仔细端详,心中很是欢喜。瞧得入神,连齐镇辰何时站在身后都未曾察觉。
“母亲!”
元菱惊愕失色连忙转身,看到来人是齐镇辰后,赶紧将手敷在心口,轻拍了几下定了定神,随后便微嗔道:“你这孩子,非要将为娘吓坏不可!”
齐镇辰调皮地笑着道:“母亲,我见您得了宝贝爱不忍释,嫉妒得紧呢!这花簪如此精致,可是父君赏赐?”
“哪里,这是那……”
话未说罢,便见齐继远带着不少侍卫精兵进了怜双殿。元菱见状,赶紧拽着齐镇辰上前行礼。
“臣妾给圣上请安!见过贵妃娘娘!”
齐继远双手拂在身后,道:“贵妃陪嫁的碧玺花簪遗失了,听闻,今日你去了贵妃宫中,你可有见过?”
元菱瞬时间已是明白了七八。她虽心内已如明镜,知晓此事齐继远定会偏袒幻玉,眼底却是藏不住得委屈。
元菱自知,这花簪拿不拿出来,自己现下都已是个罪人了。
若拿出来,便是人证物证俱在;若是不拿出来,等到那花簪被搜出来,那便是欺君;若是分辨,也只会被看做是饰非掩过吧。
元菱从袖中将花簪取出,幻玉当即上前夺了下来,声泪俱下:“姐姐竟连这小小花簪也要占为己有么?!莫不是仗着圣上宠幸了姐姐几日,姐姐便恃宠生娇,连我母亲留与我之物也要巧偷豪夺么?!”
齐镇辰见自己母亲如此被人羞辱,身为父君的齐继远竟一言不发,忍不住直言:“贵妃娘娘,我母亲定不是你口中那般不堪之人!”
齐继远听罢,厉声斥责齐镇辰:“你不思进取,整日待在这怜双殿中游手好闲!此刻,竟还有脸为这贱妇辩驳么?!你现下立刻去园中跪着反省,月亮不升起不准起来!”
元菱见此景,冷冷说到:“圣上,您真的不愿听臣妾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与圣上听吗?”
齐继远道:“这花簪即在你手中,你还有什么可分辨?”
元菱轻叹道:“元菱自知罪无可恕,但请圣上饶了辰儿,辰儿少不更事……”
齐继远叹了口气,说道:“少不更事?那便是你教导无方!来人,传我的令,元贵仪失德,禁足怜双殿!易王不思进取,罚跪已是无用!着,罚其离宫,去听云居反省过错!无召不得回宫!”
齐继远说罢,不顾元菱的哀求,携幻玉离了怜双殿。
幻玉回眸看了看元菱,眼中的得意已经满溢了。
元菱现下顾不上恨她,只想拦下被侍卫请出殿外的齐镇辰,她想追出去,亦被侍卫拦了下来。
同被侍卫挡在殿外不能入内的齐镇辰心焦火燎,无计可施,只得大声对殿内的元菱喊到:“母亲!母亲!”
元菱怕齐镇辰再惹出事端,强忍着泪水,平了平心绪,缓缓说:“辰儿,离宫后,定要日省月修,莫要再行差踏错!母亲在宫中不会有事,你安心去,不必挂牵!”
齐镇辰听罢后,“扑通”一声跪在殿外,叩首三次后道:“母亲,孩儿定不负母亲教诲!母亲且安心在此等候,孩儿定会回来为母亲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