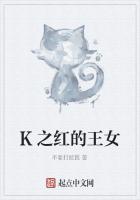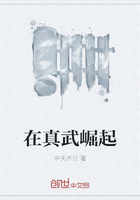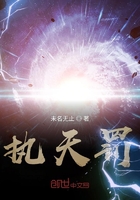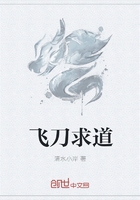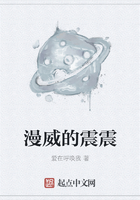贾:我身体不好,一直担心路上累倒,但还好,只是犯过几天的牙痛和一次拉肚子。我带了一大包药,反正没事了就抓紧休息。一路很辛苦,但我幸运地完成了预期的计划。
孔:您的《西路上》与西部大开发有联系吗?
贾:当然有联系了。去亲身看看西路上的山川地貌、人情风俗和现在的变化,一直是我难以释怀的念头。
孔:和您的毛笔字一样,您的《西路上》的手稿显示了您的硬笔字也有着个性化的魅力。您的字体风格是在自然写作中形成的,还是刻意练写出来的?
贾:当然是在自然写作中形成的。我从未想过要当书法家,书法是我种麦子而在收获到麦粒外又收获了麦草。老实说,我的钢笔字不如毛笔字。从书中可以看出,有些篇章写得还可以,有些篇章就潦草不堪。那时怎么能想到会出个手稿本呢?
孔:在电脑写作已经普及的今天,您为什么还不换笔呢?
贾:我喜欢用笔写作,也习惯了。用电脑快,但一个作家一生能写多少字呢?写不了多少的,何况手擀面条总比机器压出来的面条好吃。
高立民还编辑有笔者著的《书友贾平凹》和朱文鑫编著的《收藏贾平凹》等优秀图书,陕西师范大学王志武教授曾以《对社会对读者负责》为题著文刊发在《中国编辑》上予以称肯。
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金平先生说过:贾平凹是出版界的金饭碗。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贾平凹是当代当红作家,他的著作尤其是长篇小说部部畅销,一般起印数字在15万册,累印数字高达30万册,多种版本的《秦腔》已超过30万册。但在出版社做过编辑如今还做着《美文》主编的贾平凹了解编辑,理解出版人,所以在长期的著作出版过程中,与出版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但愿这种友谊地久天长,如此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幸事,对中国当代出版业也是幸事。
悼贾母
昨日早晨惊悉贾平凹之母——慈爱的贾妈妈仙逝,震惊之际,不仅悲从心来,这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遗憾啊遗憾。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我和妻子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棣花奔丧。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各个部门及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来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副挽联概括了贾妈妈的一生,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由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前多年,平凹与母亲住在西北大学时,我因工作或写作上的事情曾去过多次那里,每次去,贾妈妈都热情地招呼我们,给我们倒水泡茶,当平凹为他人写字或办事时,贾妈妈就会陪我们聊天,有时说到平凹的遭遇,她就轻叹一声说,平的命苦。当说到平凹再婚生女时,贾妈妈又是轻叹一声说:平没那命。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中国乃至世界的读者将会多么寂寞。所以贾妈妈的去世无疑也是文坛和读者的一大损失。贾妈妈虽然走了,但她永远活在平凹的作品中,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07.9.7附录
王新民文学年表
1960年1月7日生于陕西省大荔县汉村乡(现并入许庄镇)义井村,1969年—1978年在村办九年制义务学校相继读完小学和中学。
1978年5月转学到汉村乡中学复习备考,参加当年高考,名落孙山。同年9月—1979年7月到两宜镇中学复读备考,参加1979年高考,榜上有名,被西北大学录取。
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西北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创作古体诗《自述》等,刊发在《西北大学校刊》上。
1983年7月,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同月分配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旅游文学编辑工作。编辑出版《旅游文学丛书》,计有《平凹游记选》、《和谷游记选》等十余种,《陕西名胜古迹传说故事丛书》等多种。业余创作发表了大量书评、书话、游记、散文、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多篇书评获《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和陕西书评学会等单位举办的读书征文奖,游记《太兴山初探》刊发在《西安晚报》(1987年)上;纪实文学《枫叶红于二月花》、《一个女劳模的襟怀》入选《开拓者风采》一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1989年加入西安市作家协会。
1991年11月调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工作,编辑《陕西出版》,编修《陕西省志.出版志》(任副主编)、《陕甘宁边区出版史》、《西北大区出版史》。同年与友杨力民、张选生合作出版《西安旅游大全》,与友孙见喜编选出版《贾平凹游品精逊(前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为该社1992年版)。
1992年,将《陕西出版》改刊为《出版纵横》,任编辑部主任,贾平凹题词祝贺。散文《他们是我的好邻居》、《祝寿》入选《情暖人间》一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1993年,在《出版纵横》陆续编发《陕军东征专栏.陈忠实》、《陕军东征专栏.高建群》。同年策划编选出版报告文学集《贾平凹与〈废都〉》、《多色贾平凹》。
1994年,编选出版报告文学集《贾平凹谜中谜》、贾平凹散文随笔集《坐佛》(均为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同年编选的《贾平凹游品精选》再版(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编选出版《〈废都〉按废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同年协助贾平凹打官司,应诉女诗人告贾平凹“抄袭”其诗作,反诉《创世纪》侵权案;状告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假冒贾平凹之名出版《霓裳》一书,配合官司撰写了一系列报道、纪实文章。
1995年9月28日,在笔者和律师的努力下,贾平凹与女诗人在法院主持下和解。至此,酝酿一年多,历时5个月的《废都》“抄袭”(后又称为“抄用”)案和《创世纪》侵权案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昔日曾为文友,一度反目成仇,几番欲决雌雄的范某和贾平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了。同年12月28日,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随着职务的提升,研究水平也在努力提高。《出版纵横》与《书海》合刊,任编辑部主任。
1996年,一边协助贾平凹继续打《霓裳》一书官司,一边开始搜集资料,创作长篇纪实文学《贾平凹打官司》。《传书》等散文获《光明日报》社等媒体和部门颁发的奖项。
1997年,编修印制《同州义井王氏族谱》,贾平凹题写谱名。编选散文随笔集《行余集》,11月,贾平凹、方英文应邀为该著写序。组织编写出版《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习****应邀为该书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