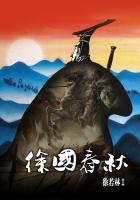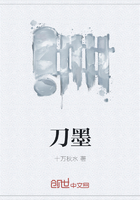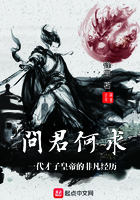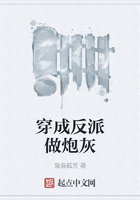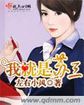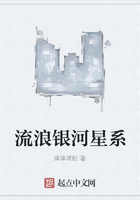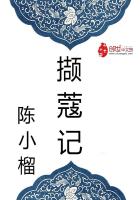2月19日晚,听完江青漫无边际的“谈话”后,总政的4位领导人要回北京了。为了向党委汇报方便,他们商定把江青的讲话整理出几条,由陈亚丁执笔形成了文字。临走前,他们给暂不在上海的江青留了一份。21日刘志坚乘飞机到济南,找到由苏州转到那里休养的林彪,交给他一份文稿,遂飞回北京。
2月21日午夜已过,刘志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的声音很不客气:“我是江青!”
刘志坚答应了一声,便听到江青震耳的怒气:“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怎么搞的嘛!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闯了大祸。现在这个不行,不要扩散、传达!”
对这样的结果,刘志坚、李曼村早有预料。离沪前,为材料送不送江青,刘志坚还与陈亚丁有过一场小小的争执——
“刘副主任,依我看,这份东西应该给江青同志一份。”
“算啦,这是向党委的汇报,又不是正式文件。”
“那怎么行?这些都是关系大局的问题。是江青同志对整个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很有水平。只给党委看看,范围、影响都太小了。”
“你这位老兄,怎么这样敏感?”刘志坚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她讲话的内容危言耸听,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他想想还是不说好。
“林彪同志不是说,今后这些事要多与她通气吗?”陈亚丁这句话倒使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无法反驳,只好默认了陈亚丁的看法。
……
江青在那头反而急了:“你怎么不说话?这件事我已经请示了毛主席。主席指示还由那个评《海瑞罢官》的班子搞,把这个稿子委托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你们那里来个陈亚丁就够了。”
这倒是刘志坚求之不得的:“好好,就让亚丁参加修改吧!”
当月的25日下午,当陈亚丁带着原稿风风火火地奔回上海延安饭店时,张春桥已经在一层客厅里等他了。两人立即乘车赶到锦江饭店,刚要拐进江青住的套间,一名身穿服务员衣装的彪形大汉拦住去路:“首长现在在吃饭,不能打搅。”张春桥眼也没抬,不满地说:“这是事先约好的,有急事,你不要管!”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春桥来了吗?快点进来,进来呀!”
江青正在吃饭,也不管自己的吃相,边吃边说:“你们平时吃什么?我很注意体重,还用食物配合药物治病。中国人太不懂营养学了。听说那个美国电影明星嘉宝,还有香港的那个夏梦,都是饮食专家……”
因为江青在吃饭,张春桥没有抽烟,总觉得少些什么,随口问道:“伯达同志今天来吗?”
“夫子一会儿就来。”江青看了一眼陈亚丁,“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让伯达和春桥推敲了一下,要彻底改,要大改。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请他把关。”
正说着,陈伯达就到了,往中间的位子上一坐,就和江青对起话来。他把一份打印稿放在茶几上,操着一般人不易听懂的福建话说:“我看首先要讲清楚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搞王明路线、搞右倾机会主义的继续。这条黑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夫子你等一下。”江青被陈伯达这吓人的开场白吸引住了,忙叫人把残汤剩菜端走,再叫陈伯达接着说。
陈伯达好显示一点与众不同,或者叫跌宕起伏,他先说“第二个是要用重彩浓墨写一段这几年文艺方面的成绩”,一下子把江青和张春桥都听得瞪大了眼:夫子糊涂了,怎么讲起成绩来了?原来是陈伯达又用了一个写文章的小技艺,变相地捧起江青:“要说成绩,那就是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了许多嘛,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个,啊,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瑰宝。”讲到“瑰宝”二字时,陈伯达的嘴里好像嚼着一段甘蔗一样甜美,使劲地后仰在沙发上,嘴里的话又变得像蹦豆一样松脆:“这才叫推陈出新,才叫创举。江青同志亲自抓试验田,搞出好的样板,是标社会主义的新,立无产阶级的异。我看只有这样改,‘破’什么‘立’什么才会鲜明、清楚。”
几副眼镜在房间里反着光,有的是惊讶,有的是赞赏,而江青的眼神更多的是陶醉。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听见没有?这就是‘党内第一支笔’的厉害,春桥、亚丁你们听清了没有?伯达同志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真是难得,真是金石之言!修改时,一定要加上。”
“不用了,我已经都写在初稿上了。”
江青更是喜上眉梢:“哼,还有人说伯达同志只会写文章,这是偏见,是嫉妒!没有大政治家的水平,哪能写出这样掷地有声的文章?我要告诉主席,一定不能委屈伯达同志!”她又看了看陈亚丁和张春桥,说:“明天请你们代劳了,按照伯达同志的意见,重新写吧。”
张春桥没有多说话,看来他内心里并不十分赞赏陈伯达,因为他们以前毕竟不在一个战壕里,只是“文化革命”才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看不起延安来的这位“第一支笔”,他还觉得自己是“第一支笔”呢。但在江青面前他不好戳老夫子的蹩脚。
他更关心上海,包括30年代的上海。
所以在他们重写《纪要》时,有一天,张春桥突然问陈亚丁:“老陈,你对周扬怎么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亚丁已经弄清搞《纪要》的目的了,顺着说道:“30年代他不断犯错误,我看文艺黑线的根子就在他那里。”
张春桥讳莫如深地摇摇头:“恐怕还不是,他是个代表,一个部长级的代表。他们是一套,下面有,上面还有。”
陈亚丁问:“难道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张春桥不耐烦地回答:“你怎么把问题看得这么简单?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哪个也留不下。”
2月28日上午,江青看完他俩的修改稿,脸上绽出笑容:“辛苦了,辛苦了,我看可以,印出来上送吧!”
就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东西诞生了。它的诞生将意味着许多东西的死去或受难。世界就是这样,有时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后来被证明非同小可。
《纪要》很快送到北京,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做了修改。
3月19日,那真是江青的节日。她在她那些“亲密战友”的簇拥下,飘飘如仙地出现在她临时官邸的电影厅兼会议室里。
“又把你们请来了,这份稿子虽然经过重写,但还是有你们的心血。你们不会怪我‘夺人所爱’吧?哈哈哈……”江青向刚刚到上海的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打着招呼。“当初,你们给我闯了大祸,现在是因祸得福。好了,先看看主席改过的稿子吧。已经是大功告成了。”
刘志坚他们没法随着江青的欢乐而欢乐。他看到稿纸上粗大潦草的毛笔字,知道这个《纪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纪要》了,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字就是最高指示,是不容置疑的。可他毕竟是个老军人,认真而耿直。他还认为有些地方不妥:“依靠部队搞文艺革命这句话恐怕不妥当。地方文艺队伍有80万人,不靠他们自己怎么行?另外,稿子上说要重新组织队伍,是不是改为整顿文艺队伍更好?”
张春桥朝他努努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行了,行了!”
江青喜欢侦探小说一般的秘密活动:“现在形势很复杂。有人听到风声就找张春桥打探消息。你们回去不要把内容告诉任何人,我要打个出其不意的漂亮仗!”她布置陈亚丁:“你来帮我给林总写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转引自林韦:《“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下同)
林彪那时在苏州。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未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还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的信,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并默认了此为他“委托”江青所办。但林彪心里怎么想的,无人能知。
据林彪的秘书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部分时间在钓鱼台11号楼居住。来往于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是叶群。因为林彪的反对,叶群经常是偷着去,偷着回。只要被林彪发现,必然发一顿脾气。有时知道叶群往钓鱼台11号楼打电话也要训斥她一顿。为何林彪对江青如此警惕,不得而知。不过此事林彪肯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包括前面说的《纪要》一事,当初林彪住在苏州,有一天江青不约而至,来找林彪谈有关文艺战线的问题,叶群因为下乡“蹲点”去了,林彪只好硬着头皮接待。江青很不客气地问林彪:“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也很不高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看过。”
“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
江青气呼呼地搬出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吭声。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控制着情绪:“我身体不好。”
这时候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江青一眼瞥见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脸一虎:“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
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林彪在江青面前也不总是示弱,有时也会发作。就在江青指责过林彪不久,有一次,江青不知为什么事,又来找林彪。他们谈了一会儿,就听到林彪冲着秘书喊:“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秘书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不知是执行好还是不执行好。正在不知所措,叶群可能听到动静,自己跑来了。秘书赶紧回避。但还听见在林彪会客室门口传来江青的声音:“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秘书走远了,不知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
叶群不希望秘书看到此类场面。在江青走后,她找秘书“消毒”:“刚才你看到的情况,没对别的秘书讲吧?”
“没讲。”秘书回答。
“不讲好。”叶群说,“如果讲了,传出去不好。其实也没什么,首长和11楼都有自己的倔强的性格,互相之间很坦率,但事过之后就拉倒,谁也不记仇。他们刚才也是由于一点小误会,首长的性子急,就火了。我进去说了说,双方的误会都已消除。11楼走的时候,她和首长又都笑了。”她看秘书点了头,还是不放心,再一次强调:“无论如何,刚才的事不准向旁人传。因为我在场,我不能不向你作些解释,但你不能再向任何人讲了。话到此为止。”(详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自从《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公开发表,前面加了一句“林彪同志委托”,林彪对江青的态度还是明显有变。那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们的信就是证明。但秘书们觉得,这种改变只是表面上的,林彪对江青的戒心依然很重。
顺便说一下刘志坚以后的日子。
江青对他日渐不满。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江青住11号楼,刘志坚住2号楼。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是军队干部,应该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住在西山,常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西山。陈毅元帅经常去西山。江青见刘志坚与几位老帅关系密切,就要整掉他。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位元帅讲话时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把江青气得够呛。于是她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要批斗陈毅,周恩来找刘志坚谈话,要他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康生为此大拍桌子。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的要员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陈伯达则“揭发”刘志坚是“叛徒”,依据就是被敌人抓走又活着回来了。不久,林彪也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于是,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撤销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先在北京卫戍区,后转移到北京顺义县。
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他当了7个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三副组长,4个多月的第二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最终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细”等罪名被打倒,被关押审讯,无情折磨了七年零九个月。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夕,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监护审查”,恢复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