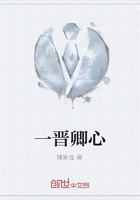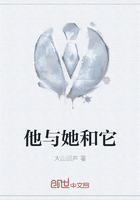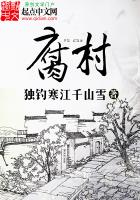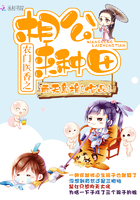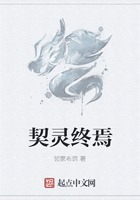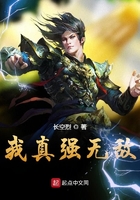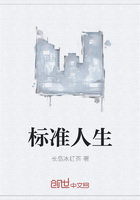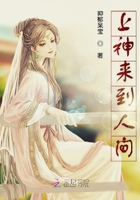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策发生了根本积极的变化。在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来了。这几年全国各地包括农村生产组织在内,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指出,不改革开发,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首先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政治成份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逐渐不再是比较谁更穷,谁是贫农,而是开始比较谁家通过联产承包努力后生活条件更好,社会上开始敲锣打鼓地鼓励“万元户”。同时,国家层面开始倡导计划生育。全国各地的横幅,农村的墙上,写满了“只生一个好”、“发展是硬道理”等标语。人们开始关注生产和经济发展。
其次是计划生育的展开。虽然国家倡导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但在农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没有人只会生一个。刘天臣夫妇在女儿刘玲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刘鹏。同样,张天凤夫妇也在儿子张小军两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女儿张小叶。张小叶的出生,罚款人民币三百元。在当时,三百元可以买一头强壮的骡子。一头骡子是农民财产的半壁江山。
第三是人民开始想办法搞小商品经济挣钱了。张天凤的邻居、张木胜的同族哥哥张木祥,比张木胜大五岁,开始在村里收鸡蛋,一个鸡蛋八分钱,第一天收好,第二天凌晨两点半起来,就向蒲城县挑着一副扁担步行,步行四十里,早早到了小商贩聚集的地方,等待天亮,天亮后,一毛一个,现金交易。当时用票购买鸡蛋大概八九毛钱,但得到供销社。农民们自发的供应和县城人用票购买相比,稍微便宜一点点,一斤鸡蛋大概7个,从农民这买相当于七毛钱,比用票到供销社购买便宜差不多一两毛钱。一个鸡蛋两分钱利润,每天差不多近两百个鸡蛋,差不多三块多钱,一个月就九十块钱,当时我国城镇职工年度平均工资还不到八百块钱。城乡收入差别本身很大,但这每天近两百个鸡蛋,正在悄悄改变供求结构。同时期的安徽,有个人卖瓜子,就有人举报,商量要不要杀。总设计师说:不杀,允许群众致富。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刘天臣领着七岁的女儿刘玲和五岁的儿子刘鹏,从刘家村走到卤泊滩散步。刘天臣和孩子们边走边玩。
“玲玲,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问刘玲。
“我想当老师。我们学校赵老师对我们可好了。”刘玲说的赵老师,是学前班的民办代课老师赵爱玲。赵爱玲的父亲是樊家村的书记,赵爱玲高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教书了。
“鹏鹏,你长大想干什么?”刘天臣问刘鹏。
“当解放军。”刘鹏举着手里的玩具枪,嘴里“砰砰”的配音,对着茫茫的滩地划拉着。
同年同月的一周后,孝通初中举行“六一儿童节”表演比赛,代表孝东村小学学前班的张小军留着口水,在孝通初中的操场上背诵“啊喔呃易屋育……”,一边背诵,一边口水把借来穿的显得特别宽大不合身的白衬衫流湿了一条印子。张小军的表演连同口水,获得了掌声,大人们争相鼓掌,欢笑成快乐的海洋。
但是,大人们的世界随着条件变化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刘天臣本身就是能人,联产承包后,日子很快就过在了上风头,家庭关系相处和睦。王菊花也是勤俭持家的过日子人。家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其乐融融。张天凤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当时婚姻就是冲着政治身份去的,现在改革了,联产承包到户了,不讲贫农身份了,这时丈夫张木胜能力弱的缺点就上升为婚姻关系的主要矛盾了,三天两头有事没事地,张天凤都要表达她的不满。她曾经多次闹离婚。每次闹离婚到娘家,张仲成和王菊香都劝女儿张天凤,不要离婚。王菊香常常对张天凤说:
“好娃哩!妈是离乡人,在陕西没娘家,把你嫁人嫁到跟前,就希望将来对妈有个照顾。再说了,你不看到妈的情面上,你想想你的两个娃,小军娃和小叶娃,没妈的娃多可怜!”
张仲成不说话,但他态度鲜明反对离婚。他是在西安城干过大事的人,读过书。当时的婚姻是看重对方的政治成份,现在社会条件变了,不讲成份了,就离婚,不厚道。这就是张仲成内心的简单的诚信逻辑。做生意,做人,做事,道理是相通的。张仲成少年读书,中年发达,发达时期供他的六弟、七弟、八弟念书,还供自己的大老婆的长子读书。六弟、七弟念书没念成,后来娶媳妇,炕上的毛毯家私,都是张仲成购置的。八弟念书成功,后来到库尔勒市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张仲成和大老婆所生的长子张天顺,延安大学毕业后在陕北当过中学公办教师,文化革命开始后和父亲张仲成断绝了父子关系,后来到西北农林大学担任大学教师,退休后居住在杨凌。由于中年对家庭的贡献,六弟、七弟等都很尊敬张仲成。张仲成排行老三,是他们的三哥。他们见了三哥,如见父亲般尊敬。因为这个哥哥尽了许多父亲当尽的义务。
张天凤还是听从了娘家父母的建议,没有离婚。但是,她心里感觉张木胜没本事,经常破口大骂:
“看你怂本事没有!看人家黑娃、对娃、志娃多能行!跟你简直是眼瞎了!”
但骂人的时候,张天凤根本不提当年自己同意这婚姻的动机。当年就是看上贫农主任家的成份了,作为地主子女想在人面前抬起头了。现在情况变了,不说了。
为了维持家庭,在新的环境下支撑门庭,张天凤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督促儿子张小军念书。二是督促丈夫张木胜不断外出打工,维持家用。
从儿子张小军六七岁开始,张天凤就经常的对儿子说:
“好娃哩!你看你达没怂球本事,家里光景过的不如人,周围人都看笑话哩。你得好好念书,要争口气,改变改变这面貌!”
同时张天凤不断督促丈夫张木胜外出揽工。张木胜人笨,学木匠学不会,学泥水匠学不会,只能当出力气的土工。夏天天热的时候,张天凤对丈夫说:
“木胜,你去到府华村的砖窑出砖去!娃九月开学要缴学费!”
木胜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去府华村砖窑。孝通街道到府华村就三里地,骑自行车很快就到。这是贫农主任的儿子,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后,已经失去了农业社时候的身份优势,变成为了养活家庭和子女的搬砖工。渭北高原的夏季七八月份,天气极为闷热,木胜赤裸着上身,脖子上搭着一条破烂的毛巾,穿着一条满是被热砖火星弄的都是破洞洞的短裤,一双破旧的布鞋,用架子车出砖。每天天黑,木胜骑着破自行车回家,全身都是砖窑渣滓。他是个笨到不会偷懒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可怜的父亲满身疲惫地回到家中,他的儿子张小军眼里都充满了泪水。他想:我太小了,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再让亲爱的父亲到砖窑这样搬砖了,太恓惶了,太让人心疼了!
张木胜中等偏矮,清瘦,一生只能做土工。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他老实干了一辈子!府华村承包砖窑的老板陈栓虎看到木胜老实卖力,每天都要多干,心里过不去,就改革了算账方式,从一天8块钱改成按出砖数量核算,一架子车装满一毛钱。陈栓虎对在秦家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妻子杨腊梅说:
“你看东街这木胜哥,干活太老实了,我心里都看不下去,我改了算工资方式,不想对不起这老哥人!”
杨腊梅说:
“对着哩。木胜哥就是老实,小时候他曾经被送到我娘家佛殿村隔壁的人家,几个月就又送回西街了,说是太笨了。”
每到冬天,张天凤就对丈夫说:
“木胜,过了寒假娃上学报名要钱哩!你到北滩里去出芒硝!”
渭北高原的冬天,刮风的时候寒冷异常。这风像乌鲁木齐的风,吹在脸上刺痛。张木胜和孝东村的王百锁一起,各骑上各自破旧的自行车,就往北滩里去。冬天天短,两人出去是个伴。所谓的北滩,就是孝通街道向北五公里的卤阳湖西段,就是卤泊滩。出芒硝,就是去当苦力,挣点辛苦钱。两人的娃大小差不多,王百锁的女儿王倩铃和木胜的儿子小军同岁。
木胜和王百锁两人说话,都有些口吃。王百锁一边出芒硝,一边给木胜说:
“木、木、木胜哥,你、你、你比我强哩!”
木胜一边出芒硝,一边说:
“咋哩?”木胜说两个字的时候,很少能表现出口吃。
“你、你有儿子,我没有!”王百锁边干边说。王百锁两个女儿,大女儿倩铃和小军同岁,小女儿倩丽和小叶同岁。
承包芒硝厂负责生产供应的,正是刘家村的能人刘天臣。刘天臣一般巡视工作,检查苦工们是否偷懒的时候,都戴个墨镜,穿个黄大军衣,还有新疆流行的大头窝窝(棉鞋),俨然一个芒硝厂的厂长和县里企业的领导派头。
有一次刘天臣检查完毕,没走多远,王百锁就跟张木胜说:
“就、就、就木胜哥!人家刘、刘、刘厂长和咱就、就、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木胜一边劳动,一边跟百锁说:
“话多的很!”木胜有时说四个字,也不口吃,说多了就表现出来了。
“刘、刘、刘厂长的女子,都、都、都说念书念的好、好、好得很!”百锁继续说。
“得、得我军娃念、念书也好!”木胜边干活边说,显然对比较子女念书,他不服气。
张木胜一生都没叫过儿子张小军的全名,一生只叫小名军娃。直到多年后木胜咽气去世,一直如此。
其实生活也未必像王百锁想的那么糟糕。多年后女儿王倩铃招了一个女婿王海军,会开车,会修车,日子过的好着哩。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张天凤逐渐成了这个家庭的领导和主事者。是人生磨练了生活,还是生活锻炼了人生?随着两个娃的慢慢长大,和公公婆婆以及娘家父母的逐渐变老,张天凤逐渐放弃了离婚的念头,转为如何维持和撑起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
这就是生活。它没有按我们预想的脚本,而是按它自身的发展,随机地前行着。木胜和百锁两个人干到太阳落山,就收工了。寒冷的冬天太阳下山后,芒硝滩地上发出逼人的寒意,仿佛带冰的弓箭从地底射出,让人感觉阵阵的恐惧。两人穿上破棉衣,带上厚厚而破旧的**帽,把下巴的帽盖系起来,带上棉手套,骑上他们各自那破败得摇摇欲坠的自行车,从寒冷逼人的白茫茫的卤泊滩,返回孝通街道。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农民中没有手艺的苦力者。在常人看来,他们笨,以至于笨到都不会偷懒。但他们恰恰是最可爱的人的群体之一。他们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劳作在最艰苦、报酬最低的渭北高原各种苦力场上。他们没有偷抢,没有骗,走的端行的正,形成了社会稳定和整个社会阶层金字塔最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是伟岸的山,是家庭的支撑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