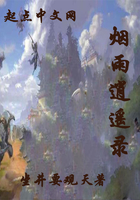清晨,东边日出照过来的晨光挥挥洒洒的照进屋中,秦熠川一觉醒来到平日里作功课的书案前坐下,抬头便见祝秋站在门前,晨光照进屋中羞人眼,让人看不清此时祝秋的面容。
昨夜里村口的打斗处理的十分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晨起劳作的百姓甚至不知晓昨夜里村口有人单凭一人之力诛杀数位江湖一流,更是靠一块金牌逼退一位实力跻身一品天玄境的高手,这倒是很符合那位远在京城养尊处优的公主的手段,一切都是那么的了如指掌,事后不留丝毫痕迹。
秦熠川不仅一次沦为他人棋盘上的棋子,但敢肯定自己独尊二姐的棋盘之外,却不敢肯定那位与自己有婚约在身的公主,是否将自己也作为夺权的棋子。如今嘉宁郡的局势逐渐明了,京城权贵在此地上演的一番博弈也逐渐接近尾声,明面是为崔家而来,实则却是为暗杀潜藏在此地的邵北世子,对于为杀自己而被持棋者作为明棋白白牺牲的崔家,秦熠川感到惋惜,可若是不将崔家牵扯进来,这块记载有大明无相经残章的玉石不知还要蒙尘多久,置身棋盘为棋子,能有意外的收获,这棋子做的也不亏。
“昨夜里那人,在门外待了多久?”秦熠川是当今圣上指定的公主驸马,也算是公主府的半个主子,昨夜里那人满身血迹的来拜见,秦熠川没给他好脸色,倒是好奇他后来会怎么做。
“没待。”祝秋说。
秦熠川忍不住一笑,一个连自家奴才都未必把自己放在眼中的败家世子,还妄想在公主府的头上逞威风,不过也罢,倒省了自己去说那些客套话,若是昨夜是殷清越,想必那个名叫杨轲的公主府下属,此刻都会一动不动的跪在门外。
“新任命的镇北司总指挥,今天就会抵达义凌府,是朝廷钦点,除当今圣上,不听命于任何人。”祝秋站在门外,说道。
听到这等消息,秦熠川嘴角微微上扬。看来这盘棋的赢家已经水落石出了。
“不听命于其他人,这话现在说,有点为时尚早。”秦熠川笑言,从怀中掏出那块玉石,放在了桌上。
祝秋不明秦熠川此举何意,只是静静看着那块玉石。秦熠川道:“嘉宁郡有王府的耳目,你将这玉石送过去,让他们送交到王府。”
祝秋上前拿起玉石,转身便要离开,可身后秦熠川却突然问道:“你应该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吧?”
随后又自问自答道:“就算不知道,猜也猜个差不多吧。”
祝秋走到门槛前,又突然停下脚步。秦熠川见他停下脚步,脸上笑容泛冷,说道:“你猜的没错,是大明无相经。你在王府里不止一次暗中调查过摘月楼里的那块石匾吧?你想让祝嵘帮你,甚至开出各种条件,可你叔叔却对你大打出手,这事被我二姐得知,便要趁这次机会在嘉宁郡内除掉你。”
祝秋站在门前一声不吭,听秦熠川把话说完,便将手中的玉石装进怀中。
见祝秋如此举动,秦熠川冷冷一笑:“要想活命不难,这大明无相经可是江湖上人人觊觎,虽然只是残章,但这残章里的东西,依你的悟性他日里要问鼎江湖不难。本世子帮你想个办法,如何?”
祝秋微微侧过脸,一双眼斜视着一脸冷笑的秦熠川。
秦熠川脸上的冷笑更盛,言道:“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杀了本世子,带着这东西从此亡命天涯,等有朝一日你问鼎江湖,天下间便没人能够再为难你,到时候你再杀回王府,王府里的那些鹰犬,就算是摘月楼中的那些守阁人出阁,也奈何不了你。”
祝秋双手不经意间握住刀柄,斜视着秦熠川,秦熠川能够感觉到他话语中的冰冷。
“殿下是在此求死吗?”
秦熠川笑而不语。下一刻,祝秋直接转过头,径直朝着院外走去,临走之际留下一句:“邵北王府有些令人失望,东西我会送到!”
等到祝秋走后,秦熠川才长长的舒一口气,后背的衣袍早已被汗水浸湿,一想起方才祝秋握刀之际,此时都还是心有余悸,果然那驭人之术,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天色已经不早,看时辰,二叔也快要醒来,秦熠川起身去厨房煎药做早饭,起身时双腿竟直哆嗦,暗自苦笑自个竟然如此怕死,那又何必去作死。
等服侍二叔吃过早饭喝过药,秦熠川便依二叔的吩咐,从今日起去到嘉宁城中闲逛,秦熠川不知二叔是何用意,但既然是二叔吩咐,那就照办便是。
嘉宁城外的洛水畔离小村不远,出了村口再走上几步就能看到东流而去的洛江水,这里的洛水不比洛城的洛水美,没有粉黛佳人相聚欢声笑语的游船、没有乐器合鸣的声声悦耳、亦没有那独有的沁人心脾的甘甜花酒,就连这洛水畔,与洛城相比都显得万般冷清。
秦熠川坐在洛水畔的一个坡头,席地而坐,映入眼帘的只有出了邵北便滔滔不息一刻都不肯停的洛江水,和坡下一位披着蓑衣戴着蓑笠的钓鱼人。
秦熠川打量着这人。这人赤脚,裤脚挽在膝盖处,脚上全是岸边的污泥,上身只穿一件汗褂,褂子上披着一件蓑衣,身旁是一个用蓑草编织的鱼篓。
在坡上待的无聊,秦熠川走到江边,看一眼钓鱼人身边的鱼篓,里边只有三条手指长短的小黄鱼。钓鱼人见秦熠川过来,转过脸来一笑,露出一嘴的大黄牙来,是个年到六七十的老叟,秦熠川在旁边择一块石头坐下,仔细瞧这人时,才瞧见其怀里揣着一个酒葫芦和一杆旱烟枪。
“花这么长时间就钓这么几只鱼,何不直接撒网呢?”秦熠川问这老叟。
老叟吸一口旱烟,笑道:“这钓鱼,可不是只为了钓鱼,而是钓一种心境,钓这其中的道理。再说这水急,撒了网,网被水冲破,不但没网着鱼,还赔了本,不值当。”
秦熠川看着眼前湍急的江水,笑着问老叟道:“既然水急,那鱼饵岂不被江水冲走?”
老叟咧嘴一笑,拿着手中的烟枪指了指落饵的地方,说:“那儿,水下的河床有一个断层,我们叫做跌水,水流过那儿就会有一个缓冲,看似急实则缓,而水里的习惯鱼儿逆流而上,往往也会在那儿停歇。”
秦熠川看向老叟落饵的地方,果然那儿的江水要流得缓慢些,而在落饵地的前边不远处,江水的水面的确比此地要高出一些,而相反过了这段距离,江水反而比上游更加湍急。
秦熠川曾经看过一部有关于水经的书籍,其中就说到这跌水,专门在河床上挖一个断层,用来沉积水中的流沙。
“这洛水啊,出了邵北就像出了娘家的新媳妇,一路不回头的朝东赶,能钓几条小黄鱼,已经是很不错的收成了。”老叟吸着旱烟,还不忘举起酒葫芦小酌一口。
“那为什么不想想其他的办法,总有比这钓鱼来的快的法子吧?”秦熠川问道。
老叟笑道:“这钓鱼啊,考验的是人的心境,心净则静,万事都想要最大的利益,往往却什么都得不到。”
就在老叟说话之际,水中的浮漂牵着鱼线晃动起来,有鱼儿上钩,老叟不慌不忙的转动线轮,时转时停,看得身旁的秦熠川干着急。终于等把鱼钓上岸来,本想会是一只大鱼,却不想又是一只短小的小黄鱼,好不终于将鱼钓上岸来,老叟看其比篓中鱼还要瘦小,便又将其放回到水中,看得秦熠川既翻白眼又是满脸黑线。
老叟抛竿落饵,坐在江边抿一口小酒,说道:“年轻人性急,可是难成大事的呀!”
秦熠川丝毫不明白这老叟为何要将钓到的鱼又放回去,看着鱼篓里少到可怜的三条小黄鱼,自顾着说道:“可惜啊,放了一条,都不知道今天总共能钓到几条鱼。”
老叟听见秦熠川的自言自语哈哈大笑,对身旁这少年说:“该来的总会来,靠这洛水吃饭自然要懂得感恩,能有这么一条大江从家门口流过,这是天公作美,我之所以放了那条鱼,是因为那鱼小,何不等它在这水底长大了些,再来钓它呢?一张网全部打尽自然好,可等到一天水枯了、鱼没了,不就剩下坐着饿死了吗?”
秦熠川听得专心,当想起这垂钓中的道理时,秦熠川问道:“那这钓鱼,又是再钓哪些道理呢?”
老叟笑道:“这里头的道理,可就多了去了,且要看你怎么去领悟了。”
指了指手中的鱼竿,老叟说:“这做人呐,就要像这鱼竿一样正直且能屈能伸,要有原则也要学会适应变化,刚柔并济。”
“再看这鱼线,做人亦要如这般有韧性,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被扯断,但也要记得顺势而为。”
“对这钓上来的鱼来说,鱼饵的后面藏着的是鱼钩,那要是其他的东西,后面会藏着什么呢?其实对于垂钓者最难忘的不是大鱼装进鱼篓后坐在岸边观赏,而是与之进行搏斗的过程,而人生恰恰如此,最难忘怀的就是成功之前。”
秦熠川与老叟一直闲谈到正午日头高照,这期间老叟钓上来的鱼中不乏肥硕的大鱼,等秦熠川临走时,还不忘送几只小黄鱼,老叟笑着说:“小鱼别嫌弃,今天最大的鱼已经送于你了。”
秦熠川谢过这老叟之后回到二叔家,记得王府里的厨子做过一道油炸小黄鱼,口味甚是鲜美,于是回到家中便依着脑海中的记忆做了一道小黄鱼,虽说品相难看些,但味道还算不错。在与二叔吃饭时,秦熠川说起那位钓鱼的老叟以及从那里听来的道理,二叔甚是欣喜,秦熠川还是第一次见二叔脸上泛起笑容。
听二叔秦韬说,这位老叟早年在京城做官,辞官返乡后便独钟于这垂钓的趣事。那年秦稷孤军入邵北,在邵北抵御辽人,是这位老叟在京城求着朝廷派遣当时义凌府的两万邵北人归返故土,也是这两万邵北人,秦稷才得以起家,有了现如今邵北的五十万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