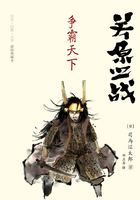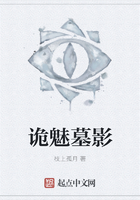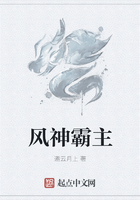欺恨诈惑滔天浪,法司信步若等闲。
解案有道窄且直,断狱无异生死间。
百思千虑岂可撼,寸心一念费猜详。
胸怀王法求正义,孜孜不畏险阻远。
昨夜我独自坐在花园亭子内,享受着清凉的徐徐晚风。夜色已深,我的妻妾们早已各自回房歇息。
整个晚间我都在书房里埋头用功,忙着让书童从书架上取来所需之书,叫他抄录下我需要的段落。
各位看官,我把自己的空余时光都用来撰写一部关于我们大明朝的犯罪及探案的汇编,并为全书增加了一个附录,收录历代名捕名探的传略。此刻我正在写生活于七百年前,赫赫有名的狄仁杰的内容。在其官场生涯的前半期,即就任县令期间,他破解了大量神秘的刑案,被后世尊称为“狄公”。他是我们历史上的神探。
我吩咐哈欠连天的书童去睡觉,然后给远在北地任北州巡抚师爷的兄长写了封长信。两年前他奉调前去任职,走前将此地邻街上的老宅留给我照看。我在信中告诉他,我发现狄公受封去京城任高职前,北州曾是他担任县令的最后任所,故而我请兄长给我找寻一些当地的档案记录,也许能找到一些狄公在那里破案的有趣资料。我知道兄长会尽其所能,我们兄弟俩一直是很亲近的。
写完长信,我顿觉书房内十分闷热,于是起身信步走进花园。清风徐徐从荷塘吹来。休息前我决定在园子偏僻角落里的小亭子内休息片刻,就在芭蕉树旁。我并不是很想回房休息,不瞒各位,自打最近纳了第三房之后,家里颇有些不和。她是个可爱的妇人,教养也很好。我不明白,我的大房和二房为何一开始就不喜欢她,且每每我与她过夜,她们必定要唠唠叨叨。此前我已答应今晚要到大房处过夜。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急着要去她房里。
坐在舒适的竹靠椅里,我轻摇羽扇,凝视着沐浴在银月清冷光芒中的花园。突然间,我看见窄小的后门被人推了开来,我的兄长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我的惊喜真是难以形容!
我跳起身来,沿着花园小径跑上去迎他。
“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我叫道,“怎不预先通知我,您要南下?”
“我也是临时起意。”兄长回复道,“我不得不走。第一个念头便是过来看你。这么晚来,还望你见谅。”
我热切地抓住他的手臂,引着他来到亭子里。我发现他的袖子又湿又冷。
我请他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则在对面椅子坐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消瘦了许多,脸色发灰,双眼微微向外凸。
我担心地问道:“可能是月光的缘故吧,不过我感觉你病了。从北州一路过来,想来旅途劳顿吧?”
“路途的确很艰难。”兄长平静地说道,“我本希望四天前就能赶到这里,可是一路上雾很大。”他拍掉朴素的白袍子上的干泥巴,接着说道:“近来我一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这里有灼痛感。”他小心地摸了摸头顶。“一直痛到眼睛后面。还会一阵阵发抖。”
我安慰他道:“老家这边炎热的天气会对你有好处的!明天请老郎中过来给您诊一诊。现在给我讲讲北州的情形吧!”
他简明扼要地给我讲了他在那边的情况。看来他与上司巡抚大人处得甚好。不过说到他自己私事时,他看上去忧心忡忡。他说他的大房近来举止古怪,对他的态度也变了,而他却不清楚究竟是何缘故。从他的话里,我知道这事跟他的突然离去有关。他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于是我不再要他讲下去。显而易见,这问题的细节令他十分难受。
为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提起了狄公这个话题,跟他讲了我刚写的那封信的内容。
“啊,的确,”我兄长说道,“在北州,人们流传着一个奇异的传说,说的是狄公担任县令期间破解的三件疑案。因为已经传了数代,人们在茶肆酒坊里讲了又讲,这个故事自然已被添油加醋地修饰了许多。”
我兴奋地说:“现在刚过半夜,要是您不太受累,我很想请您给我讲讲这个传说!”
兄长那憔悴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就在我正要为这不情之请道歉时,他抬起手拦住了。
“你听听这个奇异的故事或许有用,”他严肃地说道,“要是我早点留意的话,或许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并用手又一次轻轻地摸了摸头顶,然后接着说道:
“唉,你知道,在狄公那个年代,中土大胜鞑靼人之后,大唐帝国的北疆第一次得以拓展,深入北州以北的平原地区。如今北州乃一人口稠密的富足地区,系北方诸省繁忙的贸易中心。不过,当时的北州仍是个相当偏远的地方,人口稀疏,有许多鞑靼人的混血家族。他们依旧隐秘地施行野蛮而怪异的魔法巫术。再往北去,驻扎着文洛将军的北方大军,保卫大唐帝国免遭鞑靼游牧部落再来侵犯。”
介绍完这些背景,我兄长开始讲述一个不寻常的故事。最后他站起身来,说他得走了。此时,四更已过。
我想要陪他回家,因为他抖得很厉害,粗哑的嗓音变得很微弱,我几乎都听不清他说的话。可他拒绝了。于是我们在花园门口分了手。
我毫无睡意,便回转书房,开始把兄长讲述的奇异故事匆匆记录下来。我放下毛笔,在外面廊内的竹榻上躺下来。其时已经是朝霞满天了。
近午饭时分我才醒来。我吩咐书童把饭菜端至廊内,并吃得津津有味。一想到大房会咋呼着来兴师问罪,我便有些暗暗得意。我会说兄长不期而至,这个理由无可指责,从而可以胜券在握地打断她的唠叨:夜里未去她房里歇宿。如此这般对付完那个不可救药的妇人后,我便会去兄长家中跟他聊聊家常。也许他会告诉我离开北州的确切原因,我也能请他解释一下,他讲给我听的故事中几处不甚明白之处。
不料我刚放下筷子,管家进来禀报,说外面来了位北州的信差。他递给我一封北州巡抚的亲笔信。巡抚在信中遗憾地告诉我,四天前半夜里我兄长突然暴毙。
书斋内,狄公穿着厚厚的毛皮衣,蜷坐在书案后的椅子里。他戴着一顶带耳帽的老皮帽,但仍能感觉到吹进宽敞屋子里的寒气。
他看了看坐在案前凳子上的两名年长的随从,说道:
“这风都从最小的缝隙里吹进来了!”
“大人,这风是从北方的沙漠里直吹过来的。”蓄着稀疏胡子的老者回道,“我叫下人往火盆里多加些炭火。”
他起身快步朝房门走去。狄公皱了皱眉,对另一位说道:
“陶干,这北风似乎对你毫无影响啊。”
那位瘦者把双手往拼接的羊皮袍子的袖子里拢了拢,微笑着说:
“大人,我拖着这副老骨头走南闯北多年,无论天气冷暖干湿,对我都是一回事!况且我有这件鞑靼羊皮袍子,比那些昂贵的毛皮衣服要好得多!”
狄公心想,难得见到有比这更破旧的外套了。不过他清楚,自己这名诡计多端的老随从是十分节俭的。陶干以前是个漂游四方的骗子。九年前狄公任汉源县令时,他帮陶干化解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此后,这骗子便改过自新,要求给狄公当差。自那以后,他对黑道情况的熟谙、对人情世故的洞悉了解,常在追捕狡猾的罪犯时给予狄公很大的帮助。
洪亮从外面进来,身后跟着提一桶装满闪红炭火的衙役。他把炭火倒进书桌边的铜火盆里。洪亮重又坐下,搓了搓瘦削的双手,说道:
“大人,这间书房也太大了!我们以前可从未用过如此大的书房。”
狄公看了看那几根支撑天花板的粗重木柱子,又看了看对面那糊着厚厚油纸的窗户,外面庭院内积雪的白光隐隐透了进来。
“可别忘了,洪亮,”他说,“三年前这个衙门还是我们北军的元帅府。军队将官总喜欢空间宽敞些!”
“元帅他现在待的地方也够大的!”陶干评说道,“再往北三百公里,就是那冰冻三尺的沙漠!”
洪亮道:“我觉得吏部的消息滞后。他们派大人来时,显然认为北州仍是大唐的北疆。”
“也许你是对的。”狄公苦笑道,“尚书大人把委任状递给我时,很客气,但有点心不在焉地说道,他相信我会像在兰坊时那样处理蛮夷事宜。实际上,我们离蛮夷的边境尚有四五百公里,中间还有十万雄兵。”
老参军愤然地扯着胡子,随后起身朝房角的茶炉走去。洪亮是狄家老仆,狄公小的时候起便一直由他照料。十二年前,狄公初任汴州判佐时,洪亮不顾自己年迈,坚持要陪在狄公身边。狄公封了他官职,委任其为衙门里的参军。这位老人家对他和狄家忠心耿耿,是他最值得信赖的谋士,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和他谈论所有的问题。
狄公感激地接过洪亮递给他的一大杯热茶。他双手焐着茶杯取暖,说道:
“不管怎样,我们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里的百姓十分强健,诚实勤劳。我们来此已四月,除日常政务之外,我们只接到几起打架斗殴的案子,而马荣和乔泰便很快将它们处理掉了!再者,我得说,军方处理从北军流窜到本地开小差者等事情时,效率也很高。”他慢慢地捋了捋长胡子。“即便如此,”他继续说道,“十天前还是出了廖姑娘的失踪案。”
陶干接口说:“昨天我见过她父亲,廖老行首。他又问及有无廖莲芳的消息。”
狄公放下茶杯,皱着眉头道:
“我们调查了集市,也向本州府所有的军政衙门发去了关于廖小姐形貌等情况的公函。我想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陶干点点头。
“我觉得廖莲芳失踪的案子不值得大动干戈。”他说,“我依旧认为她是跟秘密情郎私奔了。到时候,她自会抱着胖娃娃,与她难为情的丈夫一起回来,恳求老父亲原谅,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但要知道,”洪亮说道,“可是她已经订了亲要嫁人的!”
陶干只是冷冷一笑。
狄公说道:“我同意,那情形确是很像私奔。她与她的养娘同去集市,站在拥挤的人群中观看鞑靼人耍狗熊。突然,她便失踪了。在人群中是无法绑架一名姑娘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她是自愿‘走’的。”
远处传来低沉的铜锣声。狄公站起身。
“衙门要升早堂了。”他说,“不论如何,今日我要再看一遍廖姑娘的案卷。有人失踪总是令人心烦的!我宁愿干脆查件凶杀案!”
洪亮帮他穿上官袍。狄公又道:“不知马荣和乔泰为何打猎还未归来。”
洪亮回道:
“昨夜他们说了,一清早就要去捉那匹狼,会赶在升早堂前回来。”
狄公叹了口气,脱下暖和的皮帽,戴上黑纱官帽。他正要朝门口走去,班头走了进来,急促地禀报说:
“大人,众百姓群情激动!今晨在城南一名妇人被残杀了!”
狄公停住脚步,转向洪亮,严肃地说:
“洪亮,我刚才所讲的话实在愚蠢之极!人切不可轻言谋杀。”
陶干面露忧色,道:
“希望那被杀的妇人不是廖莲芳姑娘!”
狄公一言不发。在穿过连接内室和公堂后门的走廊时,他问班头:“可曾见到马荣和乔泰?”
“大人,他们刚刚回来。”班头回道,“集市守卫刚才冲进衙门来报告,有人在一家酒馆大打出手。因为他迫切需要增援,他们俩便策马随他去了。”
狄公点了点头。
他推开门,拉开门帘,步入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