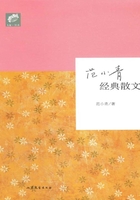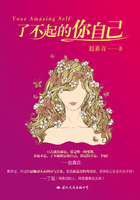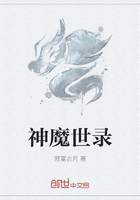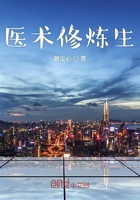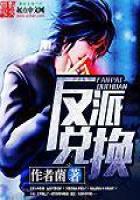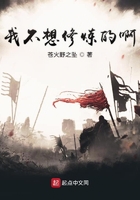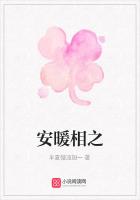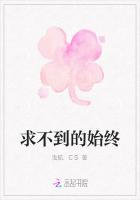第一节 “整理国故”问题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期间,最先出现“国故”一词的是《国故》月刊的刊名。1919年3月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黄侃编辑出版了这份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继承和发扬“文武之道”、“六艺之传”。
这年的5月1日,针对提倡国故的一些人,毛子水作《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卷5号)。文章指出近来提倡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国故可以研究,但“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
胡适于8月作《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就“整理国故”发表了两点意见,其中说“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过分地夸大了“整理国故”的意义,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直到后来的文章,他更把这种意义夸大到了极致。
胡适于这年的12月1日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7卷1号),就“整理国故”的主张系统地陈述了他的意见,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做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把“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这样,“整理国故”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文章就什么是“整理国故”和怎样“整理国故”的问题全面地谈了他的看法:“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就是“整理国故”。因为“国故”而谈到“国粹”,文章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重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在这里,不仅具体地谈了“整理国故”的几个有关问题,并且,把“整理国故”和“保存国粹”区分开来:前者是科学的研究整理,后者是懵懂的接受保存。(《胡适文存》卷4)
胡适于1922年5月7日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一个政治性刊物,从1922年9月3日第18期起,胡适在《努力》上发行增刊的《读书杂志》,每月一期,以研究和整理国故为其宗旨,他在第1期《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中鼓吹了清代学者王念孙父子“校注那许多的古书”的“不老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鲁迅对于“国学”的抬头,于1922年10月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所谓“国学”》,说:“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那些出版物,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鲁迅对于“国学”的最初批评了。
郑振铎署西谛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载1922年10月《文学旬刊》51期)。汪馥泉发表《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及其它》(1922年10月21日)。
《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于1923年1月10日出版,从这一期起,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任主编,这一期上,他就发动、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在他写的《发端》一文中说:组织这次讨论,其目的想弄清“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有什么影响”,“到底是反动不是”。发表文章的有: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的《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沈雁冰的《心理上的障碍》。
从发表的文章看,都认为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是有益的,必要的。具体意见留待后面论述。
1923年1月,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并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阐述了明代以来三百年国故学研究、整理的成绩和问题后,指出:当今研究国故学的方针,应是: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提出“国故学”既应研究“国粹”,又应研究“国渣”。我们应“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上至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有这样,国学才不致沦亡,它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意见是:对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弄清哪些是“国粹”和哪些是“国渣”,以达到真正发扬国故的目的。
胡适于3月4日在《读书杂志》第7期又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个书目是应《清华周刊》编者胡敦元、梁实秋等人的约请而拟的,“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知道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个方法,就体现在这个目录之内,即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的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而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开列183种,读了这些书,可引起初学的人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
由毛子水倡导在先,胡适继之于后,又经《小说月报》发起讨论,再经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鼓动和表态,“整理国故”的完整的意见就出现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但是,自“整理国故”提出后,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二节 “整理国故”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因为,“第一,我觉得新文学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地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破,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通过整理国故)把他们中心论点打破了,他们的旧观念自然会冰消瓦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造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而这种工作,都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我们现在的整理国故的呼声,所要说的,便是这事”。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的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王伯祥:《国故的地位》。“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都是不可偏废的”,“历史的观念非但不会损害现代精神,而且可以明了现代精神所由来,确定他在今日的价值”。
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新文学的基础,不当单建在外国旧文学上面,也不当单建在国故上面,须当建在外国文学和国故的混合物上面。这种的新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学”。
沈雁冰:《心理上的障碍》。“四五年前突兴的新文学运动,显然含有深湛的社会的意义,说他仅仅是旧有文艺思想的反动,尚嫌失之肤浅。然而社会上一般人却充分地应用他们的误谬的‘循环论’,以为新文学——在他们看来只是白话文学——的突兴,由于文言文的太盛,由于文言文的太多,被人看厌。一件对于学术思想史上极有关系的革新运动却被他们看作喜新厌旧的心理的表现。”“旧文学的忠臣”早就料到“白话文的‘气运’是不会长久的”,“这个‘新’过后接着的,定是从前的‘旧’。而最近一二年来的整理国故的声浪,就被他们硬认作自己的先见的实证了”。“凡一种新运动的发生,不怕顽强的反抗论。却怕这种既不反抗又不研究而惟从游戏态度相对待的阿谀曲解者。”文章希望“努力创造新文学和整理国故的人们除低头用功外,还要多用些消毒功夫,先打破一般人心理上的障碍——误谬的循环论”。
第三节 “整理国故”的几种不同意见争论
“整理国故”的问题提出后,反响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是三种意见:
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是一种意见,如上文摘引所表述的,总的看法是这项工作是一种适时的做法,对新文学运动无害而有益,有它“今日的价值”。
以成仿吾为代表的是一种否定意见,他在《国学运动的我见》(载1923年11月18日《创造周刊》第28号)一文中,批判“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希望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不要再去“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成氏的意见很明确:数千年的东西已成“枯骨”,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不相干,研究是无益的。
茅盾的意见前后有所变化,在《小说月报》征求关于“整理国故”的意见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只是希望新文学运动者和整理国故都能低头用功,做好整理国故中的消毒工作。一年多之后,即1924年5月12日,他在《文学》第121期上发表了《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把“整理国故”同“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相并论,视为“反动运动”,称他们是“中国向后的努力”的势力。一周之后,他在《文学》第122期上,又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的文章,说新文学界在这两三年里,大家提倡了白话文,进了一步。随后就退了两步,一是一些做白话文的朋友自己先怀疑起白话文来,二是“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必然丧失一些白话文已夺取的阵地,而且守旧派也会借用“整理国故”的旗号,为旧文化旧文学找到护身符,这就助长了复古势力的气焰,造成文学界“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
对“整理国故”持否定意见的还有陈西滢。他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反对把许多人带着“钻到烂纸堆里去,‘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弄得乌烟瘴气,迷蒙大地”。他认为我们还不到“整理国故”的时候。旧文化好比“一座旧房子里的破烂家具”,再“整理”,“还是那些破旧东西”。现在要的是“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载《现代评论》5卷119期)他的比喻有一定的意思,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郭沫若和鲁迅则反对“整理国故”的做法。
1924年1月13日,郭沫若在《创造周刊》36号上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批评胡适等人以“整理相号召”向学生讲国故,把这作为“人生中唯一的要事”,这就“侵犯了他人的良心”,必然“招人厌弃”。认为吴稚晖“以为科学切用于现在的中国,国学不切用,所以应该去此取彼”,这“最难使人心服”。认为成仿吾的意见也“失之偏激”,“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无须去反对他。文章认为:国学研究,“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而且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国学研究“只要研究者先有真实的内在的要求,那他的研究至少他自己便是至善。我们不能因为有不真挚的研究者,遂因而否认国学研究的全部,更不能于自我的要求以外求出别项的势力来禁止别人”。
鲁迅应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之邀,于1924年1月17日作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围绕天才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批评了“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的种种错误做法: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就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载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1期,12月27日《京报副刊》第21号转载)这就从本质上揭露了“整理国故”的荒谬和所带来的恶果——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
第四节 “国学书目”的出台引起青年读什么书的争论
“国学书目”的出台,是“整理国故”的提倡者们“拿了这面旗子”向青年号召的必然行动,开具书目的第一人就是胡适。1923年3月4日,他应《清华周刊》的编者胡敦元和梁实秋等的约请,在《读书杂志》第7期上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并说明开具这个书目的目的和对象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只为普通青年人想知道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个书目,计183种,其中文学史方面的书有千册之多。
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作《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的国学书目〉》,批评他开出这么多的书目,“叫青年从何读起”?他在批评胡适的同时,也应《清华周刊》的约请,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载5月《清华周刊》),到这年的6月23、24日《晨报副刊》将他的“评”文和“要目”一并刊载。他在批评胡适开了那么多的书目的时候,自己也开了127种,可谓旗鼓相当。
这样的两套书目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反响、批评接踵而至。
吴稚晖:在当今的世界上,“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它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梁先生开了一笔古董账,让学生“挟之而渡重洋,岂非大逆不道?”其结果,这些留学生就“成了一个废物而归”。(《箴洋八股化之学理》,载1923年7月23日《晨报副刊》)
梁实秋:对于吴稚晖的文章不能同意,他反驳说:假定国学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人生观,我觉得就很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对于国学,“自夸”或“自卑”都是不对的,“而以为国学便是古董遂‘相约不看中国书’的思想,却也与狗屁差不多”。至于出洋学生带线装书,“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但除此外,留学生还是“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许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灰色的书目”》,载1923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
吴稚晖作《答梁实秋先生》,他认为:许多祸国殃民的老国故,那些“灰色的陈腐书目,终究要不得”。我用了三年瞪开眼看,“方觉悟圣经贤传的祸国殃民,比未开海禁以前,还要厉害。若真正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载1923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
应不应该给学生开线装书的争论是在梁和吴之间展开的。而其他一些人直接地批评了他们拿了整理国故的旗子向学生去号召的做法。
李茂生:他在《国故大家应负的责任》一文中,从教育的视角来反对“整理国故”,指责国故家侵占了教育的权利,把学生的课程也“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对于学生们演讲,开书目”,使得无数青年学生中了毒,“你们的祸等于洪水猛兽了”。(载1924年3月30日《文学》周报115期)
严既澄:他在《国故与人生》一文中指出:“国故,是过去的时代的人生的产品,和今日的人生没有多大的关系,实不应该再捧出来占据少年人的有限的脑力和精神。”(载1924年4月14日《文学》周报117、119期)
第五节 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意见及其他
“青年必读书”是《京报副刊》征集青年读什么书引发的。1925年1月4日,该刊主编孙伏园开辟《青年必读书》栏,请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为青年推荐必读书,胡适、梁启超等人也参与了,他们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推荐给青年作“必读书”。这实际上是这之前他们应《清华周刊》向青年开列“书目”的一个继续。
针对这种情况,鲁迅也就青年读什么书的问题,用刊表的形式,发表了《青年必读书》(载2月21日《京报副刊》)以答,原文很短,仅二百来字,摘要如下: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寥寥数语,振聋发聩。有人对这篇极为深刻的短文,不能解其真意,以为不过是一些玩笑或是愤激之词,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这样回答:“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全集》第1卷)鲁迅坚持青年要有活学问,反对青年埋头故纸堆,读死书。如果不将青年引导去“行”,那后果,中国将真要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鲁迅的真意,为青年们所赞同,接受。当时的年轻诗人汪静之于1925年5月1日写信给周作人说:“《京报》附刊上《青年必读书》里面鲁迅说的‘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一见就拍案叫绝,这真是至理名言,是中国学界的警钟的针砭,意见极高明,话语极痛快,我看了高兴得很。”
鲁迅的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攻击。
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攻击鲁迅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是“卖国”,指责鲁迅“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鲁迅作《聊答“……”》,痛斥攻击者:“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而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外国的书“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你的大作,“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载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柯文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熊以谦作《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攻击说:“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他的话“糟蹋了中国书”,“贻误青年”,“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变成一个外国人”等。
鲁迅逐条予以批驳:熊的攻击的文章,不是用“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他是用的篡改原意,故意“推演”,甚至是些“不省人事之谈”。文章说:“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来达到侵略的目的的做法,从而有力地批驳了熊的言论。(载1925年3月8日《京报副刊》,熊文也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赵雪阳给孙伏园先生写信,谈到有位学者说到“青年必读书”时,说鲁迅“读得中国书非常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作《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以答,说:我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没有不让人家读。现在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先前喝酒,从小喝继而大喝,酒精“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载1925年4月3日《京报副刊》,赵文也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因为“青年必读书”,引出许多的反对声,其本质的问题还是把青年引向哪里:引向故纸堆,脱离现实的斗争,还是学习活学问,参与现实的斗争?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鲁迅都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曾说:“你只要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们篇篇答复他们,总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为止。”(荆有麟《鲁迅回忆·鲁迅的对事与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