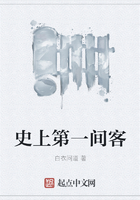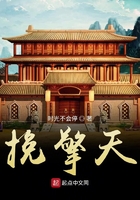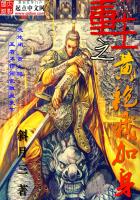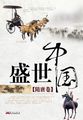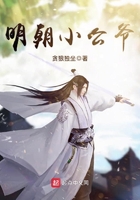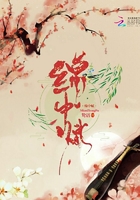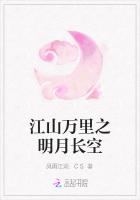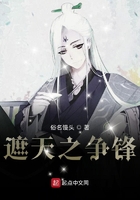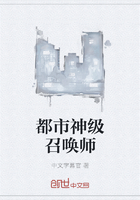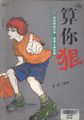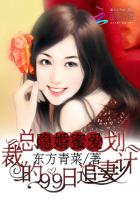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草创迄清终结,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阶段的层层选拔,有案可查的,大约产生了十一万余名进士。这些人构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政治精英,协助帝王治国理民,又在文、史、哲、艺等诸多领域有所建树。记录这些精英们的史料,历代《登科录》、《题名录》仅仅简略地录入他们的姓名(明清两代字号阙如)、籍贯、榜次、科次、甲次、名次等内容,更详细的背景资料,如字号、生卒年、家族、仕历、事迹等,除诸史列传、人物总集外,大都零落散漫于方志、朱卷、档案、碑传、笔记杂著等文献中。
裒集残丛,献征乡里,参集证史,前代学者在进士传略的纂辑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但形成的著作依旧寥寥无几,并且也不够完善,仍然解决不了了解故实或查证有些相关人物时的难题。正因如此缺憾,当代史学界人士纷纷予以关注,一时间,考证性文章、总录类著作竞相呈现,渐渐几成显学之势。在这些著作中,由浙江大学龚学明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最为突出。该选题1995年立项,2003年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他2008年11月发文介绍该书时,编写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多个年头,并且预计到2011年“书稿可望全部完成”,但我们至今未见其书出版,可想工程之大、耗时之长、工作之繁。
不为生人立传,盖棺方可论定,是古代史家为史、志的编写确立的原则。编志者在志书中为贤达人士作传多冠以耆旧、先贤、士林、乡宦等类名。那些登科入仕,无至高官,历迹不彰,艺术不显,著作又不见于后世的人,正史无载,往往杂入“人物门”之中。
作者编著这部通览,大概缘起于对进士墨迹的兴趣。在考镜过程中,求诸史传,或为史传所未载;求诸志乘,或为志乘所未及;求诸碑记,或为碑记所未考;遍寻群籍,有的唾手可拾,有的竟日无功,东鳞西爪,或有或无,一部十七史竟不知从何说起。遂发宏愿,积沙集腋,冀成一部展卷即得之书,以绝同病疾苦。
作者构建此书的脉络非常清晰:举明清两朝进士《题名碑记》为纲目,系山东府州县志人物述记为内容,然后质之于史。其中在利用前代旧志上最费功力。旧志未经校勘裁正,有很多陋劣之处,诸如:逞臆而言、守凿支离、不知裁剪、言之无文、自相矛盾、弗参互考、崇尚异端、大乖志例、胪列己文、过于夸饰、考核不精、予夺不当、体例不善、叙述不详、去取不严、关系不载、版刻漶漫、字迹不清、错讹漏倒、出典晦奥、指类泥古、用语艰涩、古今干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弊病大大加深了承旧治新的难度。清人张瑛在《兴义府志序》中针对性地指出,修志“征引必著书名,稽溯必详原委,采摭必求关郡,条目必求分明,访册必求信凭,引书稍加裁节;俚言必去,晦语必芟;矛盾必无,论断必有;一事必至互考,各说必求并存;至间载己文,仅数篇见意,而扬政德,则一字不登;列传核实必严,诸志夸词必削;考核必求一是,予夺必餍众心;体例悉本前人,叙述折衷聚讼;去取俱有深意,关系尽为大书”。这些要求作者大都做到了,而且更有所发凡。
“修郡志,郡守责也”,作者夫妇无借众手,以二人之力,行郡守之责,成就百万言之著,亦贤达人也。观是书,庶可叹止。
罗燕生
201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