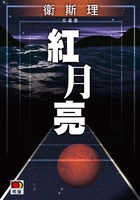(一)接手《晨报副刊》
其实,徐志摩早想要办份报纸。想他回国之初,老师梁启超有意推荐他当《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虽然有梁任公推荐,但徐志摩毕竟刚刚回国,一无名气,二无根基,所以《学灯》主编一事未能如愿。不久以后,张君劢的“理想会”要办一份月刊,名为《理想》。他向徐志摩要稿子,当然,也拉了徐志摩入伙。因《学灯》一事抱负未展的徐志摩欣然同意,挥笔写就《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投了过去。结果,徐志摩发现,那《理想》月刊永远只是“理想”,一直出不了娘胎,他失望致极。
再后来,《晨报》负责人黄子美听说徐志摩有意办报,就想让他为《晨报》办个副刊。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然没有先前的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为着陆小曼的事情心神不定,所以对黄子美的提议一直没有上心。
徐志摩自己不上心,可是他的朋友们却替他上心。当他说要去欧洲散心时,陈博生和黄子美都不放他走。情急之下,他只得应承,说从欧洲回来后,一定接办《晨报副刊》。等他从欧洲回来了,陈博生他们便讨债似地逼他赶紧兑现办报的承诺。可是,那会儿的徐志摩还在为着陆小曼的事情伤情呢,哪里顾得上办什么报纸。这下陈博生急了,无奈之下,他联合众人演了出戏来激徐志摩。
这天,陈博生在《晨报》报馆里摆开宴席,约了徐志摩,陈西滢,张若奚等几个朋友吃饭。徐志摩知道,这是要让几个人当说客了,可他想不到,席间居然有人对他接办《晨报副刊》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徐志摩不配办报纸。他这样的人,只配东游西荡,偶尔写点小诗解闷。甚至还有人说,副刊这种东西是“该死”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陈西滢干脆说:“我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因为我最厌恶副刊。我主张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如果是冲着这目的,我倒是支持志摩办副刊的。志摩,我给你两条建议:第一步,你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大家听了陈西滢这话,都笑得停不住。陈博生趁机开始利诱,说徐志摩啊,如果你要办报,另起炉灶的话总得要自己贴钱,现在晨报副刊现成给你了,还有薪水可以领,多好的一件事。
一通激将,威逼加利诱,徐志摩总算动了心。想他原来一直“心不定”,遇到感情的事情,又把一切抛在脑后,只活在自己的情绪里,或许浪漫的诗人,注定感性大过于理性。所以,虽然他对理想总是执著,但却也总是脚跟无线,无目的地忙碌着。现在,朋友们对他还是信任,愿意把一份报纸交给他来办。自己的理想总算有人愿意帮他实现,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接手就是,但是他又一想,晨报副刊是日刊,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出一张报纸,多难啊。这一下脑子又胀起来了,于是便开条件道:“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
陈博生一听,手一拍:“好!你就管三天副刊!”就这样,徐志摩有点半推半就地接编了《晨报副刊》。
接手了晨报副刊,徐志摩的理想有了崭露棱角的平台。他的“棱角”是什么?是他的态度,主张与思想。
“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这就是徐志摩,只对自己负责,不迎合,不谀附,不取媚。正是这份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个性的提倡,让徐志摩的形像看上去,不仅限于浪漫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份子看上去感性与浪漫永远大于理性与现实。
(二)自己人的文艺圈
如今,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已有三五年。三五年,给一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一场真心实意的恋爱也便满了。但徐志摩在这三五年里,不但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更打造了一场惊世骇俗,毁誉参半的热恋;他写了诗文若干,惊艳了暮气沉沉的中国;还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社团,开一代文学流派之先声。现在,他不过也才28岁,就接手了《晨报副刊》,当了主编。上天眷顾徐志摩,就是这份被“逼”接手的报纸,在他的主持下,竟成了日后与《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齐名的,五四时期中国四大报纸副刊之一。
徐志摩“入主”《晨报副刊》, 无疑开启了《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这么说总有道理,先看徐志摩为《晨报副刊》找的撰稿人:
梁启超、赵元任、张奚若、金岳霖、刘海粟、闻一多、任叔永、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这些的名字眼熟?哪能不眼熟,都是平日里走动的朋友,大多也是新月社的友人。单看这些名字,也就怪不得其他人说,《晨报副刊》是徐志摩的,更是新月社的。的确也是新月社的,徐志摩正是要借着这份报纸好露一露他的棱角;原本松散新月社能在因这份报纸的联结得以团结,何乐而不为呢?
说是《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还因徐志摩一来,晨报的风格便整个地照着徐志摩走。他早先接办的时候便对陈博生他们说了:“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徐志摩说办法由着他,这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纸的刊头先换了。原来的刊头只是几个楷体字外加年月日期数,太不符合徐志摩的艺术审美要求。先是那几个字太平常,于是徐志摩找来前清举人书法家蒲殿俊,重新提了刊名,写的是隶书。还不够,单是字有些单调,于是,找来凌叔华照着琵亚词侣的一张扬手女郎图放在刊头。
结果,这画因徐志摩的一时疏忽,让外界误以为是凌叔华“剽窃”了琵亚词侣的作品。虽然后来徐志摩写文章解释清楚了,但凌叔华后来总被人拿这事说项。一直到来年五月,凌叔华还气哼哼地为这事抱怨徐志摩。所以,后来的晨副刊头画,换成了闻一多的画——一个裸体男子站在山崖上,瘦骨嶙峋,绝望呐喊。
“办法由着他”的第二件事,便是要对《晨报副刊》的编排做了调整。先是版式,由原来的八开八版,改成了四开四版;然后是出刊的日期。原来《晨报副刊》是日刊,到了徐志摩这里,便是周一、三、四、****天出刊,且偏重于文艺。比如,有罗志希,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邓以蛰来谈西洋艺术;有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谈文学,而西洋音乐则有萧友梅、赵元任;中国音乐,自然是李济之谈。
看起来,《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真正来临了。为它撰稿的人,在它那里所发表的文章,都符合徐志摩的趣味。很明显,他就是要借着这个大平台团结他的新月同仁,而不为发行量迎合读者,不为党派依附上层言论。《晨报副刊》成了徐志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这里激荡着徐志摩的思想主张,同样也激荡着新月社价值观念。有了它,徐志摩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发声的地方。
虽说《晨报副刊》多多少少成了徐志摩自家人的地盘,但它并不封闭。但凡优美忠实的文字,也总是能被他发现,比如沈从文的《市集》;有时,哪怕是反对意见,只要写得漂亮,徐志摩也一样照刊不误,后来的两次文坛大讨论,也亏了徐志摩的不分正反的刊文。但这里,先说沈从文的《市集》。
沈从文原来潦倒。在刘勉己还是《晨报副刊》主编时,沈从文曾给他投过三四篇文章,换稿费交二十块房租。其中有一篇便是《市集》。徐志摩接了报纸后,发现了这些文章,而且一眼便看上了《市集》。他折服于沈从文白描式的笔触,欣喜之余便将它发表了。徐志摩掩饰不住对这文章的欣赏,在全文发表了沈从文的文章后,还在后面加了一段附注: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鳒鳒里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却不料,这样赞美的文字,沈从文见了,却背脊发凉。因为这文章,是在《燕大周刊》发表过的,《民众文艺》也曾转载。原来报纸刊发的时候,用的只是他的笔名,而现在,徐志摩把“沈从文”三字写上了。或许是凌叔华刊首图事件让沈从文心有余悸,亦或许是沈从文学得一稿多投的事情总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连忙写了声明到《晨报副刊》解释。徐志摩当然把沈从文的申明全文发表了,完了还不过瘾,他在沈从文的声明后,又加了自己的附注: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这便是徐志摩的风格,有点义气,有点潇洒。
从沈从文的事情上,也透露了徐志摩办报纸的另一个风格:总喜欢在别人的文章后面,加上一段附记,按语之类。这到底是得谁真传?恐怕是梁启超。话说当年蒋百里写了篇《欧洲文艺复兴史》,洋洋洒洒五万字,交给梁启超作序。结果梁先生这序一作,也是五万字。五万言的文章作序怕是不妥,于是梁先生重新为蒋百里的书写了一短序,把自己的五万言长序改作著作给出版了。
徐志摩在当主编时,竟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张若奚投来一篇《副刊殃》,不过一千字。结果,徐志摩在后面加了附注,竟有两千字之多;比如刘海粟投来一篇《特拉克洛洼与浪漫主义》短文,也不过一千来字,结果徐志摩给它的附注竟有三千字之多。所以,他的附注被“扶正”,独立成文发表了。
徐志摩喜欢写附注,也是因为有话想说,便借着作者的话一并说了。太长的按语到最后喧宾守主,这分理直气壮也着实可爱。徐志摩自认这是一种“毛病”,但他这“毛病”却便宜了读者。除了评介作者,徐志摩也总喜欢在附注里谈谈他选文章的想法,谈谈报纸的稿件都是如何来的。他的附注,有时就像电影花絮一样给了观众以得见幕后制作的乐趣。
(三)著名的闲话事件
徐志摩在接办《晨报副刊》以后,新月社众人有了自己的发声管道。徐志摩领着他的撰稿团队几番驰骋,文名渐盛,当然,麻烦也不少,最麻烦的一件,要数“闲话事件”。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件意外。
新月社成员陈西滢不但给《晨报副刊》撰稿,同时也在《现代评论》上主持专栏,名曰“闲话”。陈西滢在专栏里,或写文化批评,或论时事,所有文章的题目一律定为《闲话》。
1926年1月9日,陈西滢写了一篇关于法郎士的文章,登在他的专栏上。后来,它被收进著名的《西滢闲话》中,定名为《法郎士先生的真相》。这是一篇文化评论,陈西滢在其中对法郎士的文字风格发表了看法,兼谈了他的一些趣闻轶事。文章干净利落,正是陈西滢的一贯风格。
两天后,1月11日,徐志摩正发愁,他的晨报副刊缺稿了。徐志摩正当无计可施之时,看到了陈西滢的那篇法郎士的文章。真是不错,妩媚可羡,徐志摩当下喜欢得不得了,又想起自己早先也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法郎士先生的牙慧》,于是提笔写了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徐志摩下笔时也只是想再谈一些关于法郎士的话。后来可能是因为他太喜欢陈西滢,也实在佩服西滢那篇文章写得干净灵巧,于是,他着了魔似地笔下一滑,把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写成了“西滢颂”。其中的对陈西滢的夸赞,颇的“吹捧”的嫌疑:
“……西滢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澄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
这闲话说多了,麻烦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