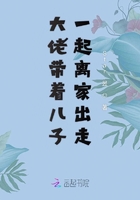傍晚,上海福熙路49号,繁树掩映着一栋洁净的两层花园别墅。
洁净整洁的客厅传来电话铃,清扫走廊小丫头急匆匆的进来接电话。
鸳儿瞧见她奔忙的样子,叫住了,“站住,浮蓉,你干什么去!”
被叫住的小丫头乖巧站直,低垂着眼,“鸳儿姐姐,我听着有电话打过来。”
鸳儿看着她的鞋,粉色绣鞋缀荷花,鞋底子旁腻了一圈泥,想是从后院鼓捣花草粘上的。
浮蓉也顺着她的目光看,把一双小脚往后藏了藏。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进了屋去,蹭的那地毯上脏污,”鸳儿使了三分力气将扫把往浮蓉怀里一掷,“让小姐看见这脏东西犯恶心。”
浮蓉应了一声,去后院的台阶处仔细把鞋上的泥刮干净。
旁边有人看见她被鸳儿斥责,替她抱不平,“鸳姐姐不过比我们早进张公馆几年,小姐抬眼看她一眼,她还真拿自己当半个主子了。”
“平常咱们做错什么事,小姐是个好性子,尚不开口,她便来献殷勤。”她看浮蓉不顺她的话,“你怎么不说她,要是她这么说我,我必要和她理论个清楚。”
“鸳儿姐姐说的也没错,”浮蓉眼看着脚底,细细的刮下土,“小姐爱干净,我不该穿脏鞋进屋。”
那人看浮蓉不和她搭腔,走了,边走还嘀咕一些活该之类的话。
鸳儿接了电话去楼上汇报,先在最靠里的一间屋子外站住,当当当敲了门,听见里面传出让她进来的声音,鸳儿才敢进屋。
“小姐,刚才天津那边打来电话,说是梁少爷的飞机下午五点到。”
小姐正在镜前画眉,她头微微向前,脖颈和薄背成一条微有弧度的好看的曲线。
今天尚未出门,她穿的家常的一套睡裙,外面的阳光透过细纱窗帘打进来,显出程蓁不施粉黛的美丽。
“告诉二爷了吗?”程蓁在描另一只眉毛,外面罩的一只宽大披肩滑下来,露出一节白皙的玉腕。
“想来天津那边,应该早得给二爷发电报了,”鸳儿斟酌着回复。
程蓁应了一声,“还是给二爷通个电话,万一他不知道,梁博宇从天津回来没人接,又该话多。”
鸳儿轻笑,“梁少爷话一贯比旁人多些。”
“是吧,”程蓁把眉笔撂在一旁,起身换衣服。
程蓁第二天穿的衣服,在前一天晚上就要收拾好放在沙发上的。今天要穿的是一件松叶色的两经罗,有淡金色蝴蝶花纹作点缀。
鸳儿忙过去,把旗袍扣子一个个解开,替她更衣。
程蓁穿好后,在梳妆镜前细细打量,“看,”程蓁捏着旗袍腰身多余的布料,“今年又肥出这么多。”
“不注意瞧到也看不出,”鸳儿替她缕平了褶,又笑,“人家过冬都是胖点圆润些,小姐您倒好,反而瘦了。”
“去年没还怎么穿过这条,真是可惜。”程蓁拿两条开司米的披肩在身上比量,“鸳儿,你看这两条哪个好些?”
“米色的不显人局气,”鸳儿说,“等明天我把洋裁缝师傅叫到公馆来,替小姐略改一改腰身。”
程蓁的卧房很大,进门先是一件小的会客厅,会客厅带着一间大阳台,往里去是卧室,衣帽间,还有一间浴室。
一间衣帽间抵得过普通人家的整间房子,豪华的有些夸张。各样舞会的晚礼服,参加酒会的宴会服,骑马场的衣服,喝下午茶的茶歇裙,家常的织锦袍子,浩浩汤汤的摆满了一整面墙的大衣柜,外面用珍珠罗幕帘罩着,怕落灰。
地上也铺着白绒长地毯,把一间屋子造的像一只柔软的巢。鸳儿想,那程蓁就是巢中的凤凰蛋,平常的蛋绝配不上程蓁。
程蓁有洁癖,不让人动她东西,鸳儿一直服侍她,也很注意分寸。程蓁不在房里的时候,她万万不敢随便进来。
现在程蓁走进来,把几件藕粉色的家常衣服挑出来,鸳儿还以为她要让人改一改,没想到她把衣服掼到地上,衣服哀怨的落到长地毯上,虽然没有声响,鸳儿好像也听到了他们的哀鸣。
“眼看夏天了,这颜色太旧,显的人老气。”程蓁出了衣帽间,从饰品架子上挑耳坠,选了一对缠丝珍珠的,对着镜子带上。
“你把衣服带下去扔了,”程蓁对着镜子补口红,“一会我给二爷打电话。”
鸳儿抱着衣服下楼,衣服上还留着程蓁常用的那款香水的味道。真可惜,鸳儿想,旧了,就要被扔掉。
鸳儿把衣服整整好,放在一个大袋子里丢到后门。进来的时候被大司务叫住了。
“大司务,怎么了?”鸳儿问。
“怎么少爷小姐还不下来吃早点?”
“少爷一早出去了,”鸳儿说,“小姐在楼上呢,我端上去给她。”
张钧东喜欢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所以他在家的时候,程蓁就会下楼吃早点,要是张钧东一早出门,程蓁也就不下楼了,让鸳儿就把早点送到卧房去。
今日的早点是梗米粥,桂花粉糕,可可麻薯欧包,用一个银制缠花的大木盘子端上去。
“你早知道少爷不在家吃早饭?”鸳儿问,“要不今日怎么有欧包?”
“我还纳闷呢,”大司务说,“昨天小姐吩咐要的,我还想着少爷不是厌吃西式早点?怎么又要做欧包吃?原来小姐早知道他不在家吃。”
“那可真是奇怪,”鸳儿摇摇头,没再说话,颤巍巍的端着盘子上楼了。
卧房门口,隐隐听见小姐打电话的声音,鸳儿怕打扰,略在门口停一下。
听小姐的语气,恐怕不是二爷,或许是新近认识的那位小宋先生。
说起这位小宋先生和小姐,倒真是有缘分,怎么这么巧,小姐的车子恰好坏在宋府门口,参加舞会两个人又恰巧碰到。
鸳儿有意要听听里面说话,头靠的近了些,听见小姐说,“剑湖的莲花开的倒好,只是我不得空去。”
不知道那头说了些什么,逗的小姐在这边笑,“你又哄着我,谁要陪你去,你难道会少人陪?”
两个人又聊了三四句话,应该约好了一起去赏花。
待电话挂了,鸳儿觉得差不多时候,故意在门口脚步放的重了一些,敲了敲门,听见程蓁应声才进去。
今日上海天气不算好,早起出太阳了,现在又有些阴,微微起了点风。
程蓁卧房里有一个大阳台,放了一张圆桌,两把精致椅子,平常早饭,约熟人聊天,程蓁就坐右边那把椅子上。
眼下她正坐在那个地方发呆,曼丽的白色纱帘被风吹的一卷一卷,直往人身上刮。
鸳儿把早点放桌上,将窗帘束起来。
“早上天气还好,现在风倒起来了,”鸳儿说,“小姐是在这吃还是端下去在一楼?”
“就在这吃吧,省的麻烦。”程蓁说,“我只吃粥,其余的端去你吃。”
“那旗袍犯不上明天着急忙慌的改了,等着夏天过去,你还要瘦许多。”鸳儿笑着说,“您快吃了吧,大司务特地还做了欧包。”
“哈哈哈,我不过那么一说,还真做了,”程蓁揪了一块面包,“对了,把给二爷打电话了这事忘了。”
程蓁揪了张纸巾擦手,电话放在床头,她坐在床头旁的沙发上,把电话抱在怀里拨号。
张钧东的号码倒着也能背熟,
“喂,张钧东,梁博宇下午五点飞机到上海。”
电话那头传过来的声音带着些许疲惫,“好,我知道了,我下午忙完过去接他。”
“还顺利吗?”
“差不多,事情很多,”张钧东吸了一口烟,“三爷为了往我这插人真是费劲了心思,可惜了,他死的早,儿子又太蠢。”
程蓁似乎能闻到从张钧东口里呼出的烟草气。
“下午去接他小心点。”
“放心吧,小匡跟着呢。”
“要下雨,别忘了带伞!”程蓁觉得他要挂电话,急忙跟了一句,说完了自己也觉得好玩好笑。
张钧东在那头也轻轻浅浅的笑了一下,淡淡的说了声,“知道啦。”
没人接。
程云迟疑了一会,正考虑挂不挂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程云?”
“张钧东,梁少爷下午五点的飞机,你去接他。”
“…现在几点了。”
程云抬手看看自己腕上的手表,“额,四点半。”
程云听见电话那头吵杂的声音,随即电话被挂断了。
张钧东急匆匆的从“金域”走出来,门口早已备好了车。张钧东坐在汽车后座,一上车先拉上了车帘。
汽车一路向东,租界通畅。到了码头附近,熙熙攘攘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只得以一步一晃悠的速度前进。
从后视镜里看张钧东,老袁不禁感叹了一下少爷的相貌。
他的眼睛狭长的微微往上吊,一笑有个好看的弧度,剑眉入鬓,鼻子有相当的高度,五官都是男相,却有一张狐狸脸。
老袁平时爱听戏,他私心觉得少爷若是扮上了,得是绝好的一个大花旦,还哪有现在这几个角什么事啊。
张钧东觉出这不正常的车速,睁开眼睛,拉开车帘,远眺窗外。
远处,上百个年轻力壮的码头苦力正像工蚁一样忙忙碌碌的搬运东西,大宗的货物从诺大的货轮上被小人分解开,运到陆地上,然后送走一艘,又来许多一艘。仿佛船队永远也没有尽头。
他把车帘拉上,目光收回来。问老袁,“外面是宋家的码头?”
老袁:“是宋家的,咱们在这还一直租了几个仓库。”
张钧东点点头,没再说话。
外面的人一直只增不减,车在这样的路上走比步行还要缓慢。张钧东看着着急,修长的食指有节奏的敲击大腿。
“得快点,梁博宇的飞机五点半到上海,要是晚了他又得絮叨。”
老袁笑了:“是了,梁少爷性子可够急的。”
梁博宇是张钧东没有血缘的表弟,张钧东的父亲张广牧,和梁博宇的父亲梁远是拜把兄弟。张广牧有十个兄弟,他排第三,梁远是小十。
这十个兄弟年轻的时候,从码头扛包的干起,坑蒙拐骗几大宗,张广牧机缘巧合的摸着门道,带着几个兄弟逐渐攒起了上海最大的赌场“金域”。打天下的先些年里,几个兄弟先后逝世,近些年金域势力逐渐壮大,张广牧在两年前被人暗杀。
两年前,张广牧身亡,张钧东还在英国留学。刚一回来,父亲逝世,八爷内讧,外面风波四起,内忧外患,张钧东处境艰难。
幸而有梁文出手帮衬,所以张钧东一直对梁家七分敬重,三分感恩。梁博宇又梁文独子,在家里宝贝的不得了,梁文有心放他出来搏一搏,又舍不得,所以安排在张钧东身旁照看。
这边,老袁一路连按喇叭,总算从人潮里挤出来。半个小时赶到了机场,刚刚好碰上梁少爷下机,梁少爷远远的就看到张钧东了,一个健步冲上来送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任着行李箱在一旁打转悠。
张钧东对着这个突如其来扑过来的东西很是抵触,眼疾手快的拿手挡住,用一根食指戳着胸骨板顶回去,然后不轻不重的扫了扫衣服上压根看不见的褶皱。
…您用得着把嫌弃表现的这么明显吗?
被嫌弃的梁少爷从脚趾头到头顶仔仔细细的把量了一番他哥哥,酸了一句:“至于吗,来接我一趟还穿的这么隆重,不知道还以为你和市长开大会呢。”
“也不是没可能,”他看着梁博宇一脸,我去两年不见你都这么出息的眼光看着张钧东,张钧东脸不红心不跳的拖着长央:“不过今天不是。”
“害,我以为你回来这两年真像我爸说的一样,那么厉害了呢。那你今天穿的和个花蝴蝶似的,什么意思?”
“你忘了,程云今天过生日。”
梁博宇吃惊,一拍脑门:“啊,程云是今天生日?”
张钧东回头催他,“快点吧,七点钟宴会都开始了。”
梁博宇上车先和老袁热情的打了个招呼,然后跑后座和张钧东挤一块,问他:“就带了老袁一个?上海这么不太平,你出门都不多带点人。”
“我几辆车换着开的,再说还从法租界住着,不安全能不安全到哪去。”张钧东揉眉,微叹一口气,“我不喜欢出门一堆人跟着。”
路走了一半,梁博宇让老袁绕绕路,绕到金广大厦,拽着张钧东到一层的珠宝铺子。
店员未必认得这两人的身份,但看模样装扮也知道不是平常人。热情的招呼:“您二位想要什么样式的,看中了我拿出来给您看。”
店堂不大,在金广大厦的一个角,但装修的十分华丽,堂中央几只白炽灯照着,高爽敞亮,几只玻璃柜台,陈列着各样的宝石,梁博宇倚在玻璃柜台上,拿手点了其中的几个,叫拿出来看看。
店员取出他选的几个黑丝绒板,一一摆到他眼前看,说道:“先生眼光真好,这几个钻石的成色都是顶好的。”小店员看见客人对摆着的几个好像不太满意,拿出来的几个坠子还在盒子里,没取下一只来看看,又说:“先生买来送女朋友,送女朋友最合适了,您要不再来看看这几个。”
小店员话还没说完,梁博宇给打断了,觉得没什么必要,但还是得要解释解释,“当然不是送女朋友,送女朋友舍得来你们家买么,送一个姐姐,算了,不看啦。”
他直起身子,回头对张钧东说:“以后再补给程云吧,我在香港看过几个钻,托朋友给她挑好的带来。”
张钧东原来在后面漫不经心的坐着,听见梁博宇的话,说:“她还巴望一阵你过来呢,先买给她吧,省一顿唠叨,这东西买了多少又不嫌多。”
然后漫不经心的对着小店员说:“拿好的出来,别拿这样糊弄的成色。”
小店员先开始听到梁博宇的话,本来以为这生意黄了,没想到出现了转机,喜出望外,兴冲冲的从结账的柜台底下开了保险箱,取出一只大的深蓝丝绒盒子。
梁博宇打开盒子看,是上好的红钻石,比豌豆还要大一圈,主钻的周围镶了一圈碎钻,众星拱月似的,在灯光底下只觉得闪眼睛。
梁博宇拿着钻石看了看,在灯光底下仔细把量,轻声道:“哎,这只好像好点。”
张钧东也看了一会:“蛮好,就这只吧。”
小店员高兴坏了:“那两位是现在带走还是我给您包装好送到府上去?”
梁博宇多聪明呀,听话听音儿,这话的意思就是,两位是现在付钱还是先交订金。
他退后了一步,贴着张钧东的耳朵悄悄的说:“你来付。”
“嗯?”
梁博宇勾肩搭背的把张钧东拉到后面去:“我没带钱,你知道的,我刚刚才想起程云的生日嘛。”
张钧东一脸正气,“我也没带,你也知道我,我出门从来不带钱的。”
“嘿,您倒是给我早说,您早说我还费心扒拉的绕这一趟的什么劲啊。哥哥,您没带钱刚才我要走,您还装…现在买不买的多尴尬。”
张钧东看着面前犯难的梁博宇,然后潇洒的回头对着那店员说:“开个单子吧,明天把货送到张公馆去。”
店员闻声哎了一声,俯身在后面开单子。
梁博宇在后头跟着张钧东说:“现在上海也能这样了?开单子送货,我还以为和从前似的。啧啧啧,连个订金也不交吗?上海人民真信任。”
“也不全是。”
“嗯?”
“主要也得看东西是往哪送的。”
“哦。”梁博宇一脸的了然:“那看来和香港也都差不太多。”
车子刚刚驶进公馆,梁博宇大叫困死,行李一丢,自己跑去一楼客房补觉。
张钧东坐在沙发上歇一歇,把手里的油纸果子搁茶几上,立刻有小丫鬟送上来茶。
张钧东唤人:“阿香,二小姐去哪了?”
阿香小跑过来回他话:“小姐去凭览了。少爷,二小姐让煮的枣粥煮好了,我给您盛过来?”
张钧东说不要,又问阿香:“二小姐说回来吃饭了?”
阿香:“没有,她让我给您煮的,她说你处理完平阳路赌档的事,又得接梁博宇少爷,肯定来不及吃饭。”
张钧东听完,略坐了一下,揉揉眉心,起身拿了大衣准备出门,临走前交代阿香:“把枣粥并着这份点心给川川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