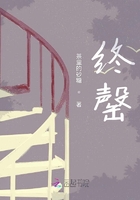“我很不高兴……我要是回顾过去的一生,就会完全心灰意懒;如此多半途而废的努力,如此多的失败!而这一切一切,原因都在帝国里没有哪个诸侯不妄自尊大,以为可以把他的怪念头看得比我的想法更加重要。”(见第三幕《奥格斯堡》一场;引文系笔者所译,下同)——这是软弱的皇帝在抱怨跋扈的诸侯。
诸侯呢,也自有其不满,他们的代表巴姆贝尔格的主教说:
“国内尽管签订了四十个和平条约仍然是个杀人坑。弗朗肯、史瓦本、上莱因邦和邻近地区一再受到目空一切的亡命骑士蹂躏。”(第一幕《巴贝姆尔格的主教宫廷》一场)
统治阶级尚且如此,下层民众的痛苦和怨恨就更深、更重了:失去了生存基础的骑士一个个铤而走险,沦落为盗;手无寸铁的商人们常常成为劫掠的对象,到处求告却得不到保护;广大农民在残酷压榨下无以为生,只好用剑与火发泄仇恨和愤怒,结果当然是遭到血腥镇压……
总之,歌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危机四伏的德国,一个充满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和奋不顾身的个人抗争的德国。
时代特色的成功描写,使剧本的内容大大地生动起来,为主要剧情和冲突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真实感人的背景。歌德晚年曾对艾克曼说:
“我写《葛慈·封·伯利欣根》时才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十年之后,我对自己描绘的生动真实还感到惊讶。”[21]
可是,我们认为,《葛慈》对于时代背景的出色描写,意义还不仅仅限于再现历史的真实,加强了剧本的感染力而已,它对于歌德创作此剧的狂飙突进时期来说,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从发生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16世纪初到掀起狂飙突进运动的18世纪七十年代,其间整整经过了两个半世纪;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德国社会的发展却异常缓慢。三十年战争(1618-1648)加剧了分裂割据局面,普鲁土发动的七年战争(1756-1762)更使得民不聊生,把德国变面了强邻的角逐场,民族危机相当严重。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描绘十八世纪的德国,说在那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22]
这样一个德国,与《葛慈》中的那个十六世纪的德国,又何其相似乃尔!不论在书本或在舞台上,德国民众看见对于后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不免会想到前者,进而抚今思昔,激发起反对封建小邦专制,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情感和愿望。也就是说,在恰当地选择时代背景和题材的基础上,《葛慈》通过鲜明的、成功的、现实主义的时代色彩的描绘,发挥了以古喻今、干予现实的巨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葛慈》这部历史剧可以说整个都洋溢着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此外,剧中还有以下一些具体内容,也是狂飙突进精神的生动体现:
一、同情农民。在1832年发现的《葛慈》初稿即《原葛慈》(Urgoetz)中,歌德以较大的篇幅揭示出农民起义原因,在于不堪忍受封建贵族的残酷压迫,形容贵族对农民剥削残害就像“水蛭”、“毒龙”一般凶狠。1773年的定稿这方面的内容虽有所削弱,但通观全剧,农民对封建主的仇恨甚至起义中的过激行动仍然事出有因,贵族平日飞扬跋扈和把农民不当人的情况剧中仍多有提及。如第五幕一开头,一位农军领袖就愤怒地回忆了贵族欺压农民的暴行。尤其是在起义失败后,歌德对农民的惨遭镇压更表示了深刻的同情,通过葛慈手下的一名骑士描写当时的惨状说:
“他们——指封建统治者——采用了种种闻所未闻的行刑方法。梅茨勒尔——一位农民领袖——给活活烧死了。成百上千的人被车碾死,被刺死,被砍头,被分尸。整个国家已变成一座出卖人肉的屠宰场。”(第五幕《海尔布隆·牢狱之前》一场)。
二、推崇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例如,自由不羁的吉卜赛人在狂信基督教的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被视为不可接近的下贱种族,歌德在《葛慈》中却大胆表现他们的生活,让观众看到这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多么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忠诚勇敢。受伤的葛慈前往求助,他们的头人立刻回答:“对迎您!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供您支配。”“为了您,我们可以付出生命和鲜血。”且言而有信,真为救护葛慈、抵抗官兵牺牲了生命。(第五幕《头人的帐篷》一场)
三、主张人性自由发展。在第一幕《林中旅舍》一场,穷修士马丁对葛慈抱怨说: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受的哟!可对于我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不能做一个人。贫穷、贞节,顺从——这三个誓约中每一个都够难受的,全加在一起更忍无可忍……呵,老爷,你们生活中的艰辛与我们这种人的可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人借以发展、生长、繁衍的最好欲望,统统被扼杀在想更加靠近上帝的虚妄贪求中了。”——这样的话出自一位教会中人之口,应该说是对违反自然人性的基督教信条的大胆讽刺和有力批判。
四,粗犷自然的语言。歌德一反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语言的矫柔造作,也克服了德国启蒙运动舞台用语的说教气,在《葛慈》中使用了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的地道德语,使德国舞台上第一次响起了粗犷、自然、有力的声音,令观众感到新鲜,感到振奋。而且,《葛慈》的语言还做到了个性化,切合剧中不同人物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份。在语言运用方面,《葛慈》也体现着狂飙突进的刚强有力的精神,堪作当时德国文学的典范。
(三)
可是,与上述各端比较起来,歌德在剧中塑造的葛慈这位主人公的形象更加成功,更加集中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加强烈地表达了一代先进青年的社会理想。
如前所述,历史上的葛慈·封·伯利欣根(1480-1562)只是个没落骑士,只是个以拦路抢劫为生的“可怜的人物”;那种称他为“中世纪革命家”和“人民运动的天才领导人”,把他与杰出宗教改革家和起义农民领袖相提并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23]
歌德天才地抓住此人英勇强悍、独立不羁、敢作敢当、不畏强权的基本个性特征,经过艺术加工,把他塑造成了一个“骑士的典范”(剧中人对葛慈的赞语),一个他所谓的“最高贵的德国人”,使他身上有了许多狂飙突进运动希望于人的理想性格——
他强壮骠悍,英勇善战,虽只有一条胳膊仍令敌人胆寒,是狂飙突进的参加者们崇奉的所谓“力的天才”(Kraftgenie)。葛慈身边的许多骑士,如出身下层的雷尔塞和仅有一条腿的塞尔比茨——我们姑且名之为“木脚骑士”吧,都是这样的人物。
他坚信骑士只能听命于“上帝、皇上和他自己”(见第一幕《雅克特豪森》一场),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坚持战斗,宁折不弯,至死不当诸侯的附庸,是个狂飙突进思想家向往的所谓“独立不羁的个性”(Selbstaendige Persoenlichkeit)。
他忠于皇上,痛恨拥兵自重的诸侯,认为骑士的职责是“驻守边境,抵御豺狼似的土耳其人和狐狸似的法国人……保卫帝国的安宁”(第三幕《大厅》一场),道出了狂飙突进运动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理想。
他生为自由而浴血苦战,死时仍高呼“自由!自由!”是个狂飙突进运动参加者一样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斗士……
总之,青年歌德非常喜爱这个葛慈,在他身上集中了狂飙突进时代的种种理想性格特征,集中了德国民族的种种优秀品质,希望借他的形象重新唤起德国民众心中的英雄主义豪情,用他的铁手击碎德国民众铅一般沉重的睡眠,使民族精神为之振奋。
葛慈那一只有力的铁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乃是奋发向上的狂飙突进精神的绝妙象征!
不过,歌德尽管喜爱葛慈这个人物,却并未违背本历史真实,无度地把他理想化,忽视他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代表的本质,像拉萨尔之于济金根似的把他美化为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而是在剧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他的局限、矛盾以及注定失败的命运——
他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代表,作为一名强盗骑士,在与处于合法地位的诸侯的斗争中,始终居于被动、受审的地位。
他立脚已实行罗马法的德国封建专制社会(关于罗马法的传入见第二幕《巴姆贝尔格的主教宫廷》一场),脑袋却留在骑士时代,仍死抱“骑士的价值”,“骑士的荣誊”、“骑士的誓言”等等陈腐观念不放,因而一再碰壁,一再上当受骗:受主教骗,受范斯林根骗,受代表皇上征讨他的官兵骗,战斗中总是失败。
他忠于皇帝,皇帝却主张派兵讨伐他;他寄望于皇帝,皇帝也自身难保。
他同情农民,但不理解农民;他不愿违背誓言与农民起义军“同流合污”,又被迫不得不当他们的领袖。
他渴望自由,为自由而战;但这自由只是骑士的那种争胜斗勇、拦路抢劫的自由,只是不依附于比他们更强大的封建主的自由,为社会的发展和法律所不容。
他向往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安宁(第三幕《大厅》一场),但又主张这一切都应像中世纪那样由皇帝在骑士支持下取得;这在已经前进的时代里,只能是无从实现的幻想而已。
总之,作为个人,葛慈忠诚、善良、坚毅、勇敢、机智——如两次拒绝济金根帮助他抗拒官兵,为自己留下后路;但是,他的阶级地位和所处时代却束缚住他的手脚,使他一直陷于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最终遭到了毁灭。这就使葛慈这个人物身上同时存在着英雄性和悲剧性,成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典型。
为了塑造这个典型,歌德除了让他在风云多变的历史大舞台上充分表演,以自己的言行为自己画象以外,还采用了反衬、烘托等等手法,让他与众多人物发生关系,通过不同人物对他的态度和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他,使他的形象变得丰富而富于立体感,真实生动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那么,对于歌德塑造的这个人物,又该如何评价才算恰如其分呢?
首先可以肯定,葛慈不是革命者;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逆历史潮流的。但是,他也并非农民起义的叛徒,或如有的书上讲的,“背弃了起义的农民”——历史上的葛慈确实如此;因为他并未“和农民一起革命”[24],而是迫不得已才参加了起义农民的行列,且目的在于约束农民的过激行动;再说,他在起义军被击溃后负伤被俘,至死并无任何变节行为。
笔者认为,葛慈只是如恩格斯说的一个叛逆者;他的确拿起了武器与社会进行抗争。但是他抗争的目的,仅在于谋取自身的生存和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所以,讲得更确切一点,他就仅是作者歌德所谓的那么个“在野蛮、混乱的时代里强悍而善良的自助者”,本质上与历史上的葛慈没有两样。
(四)
《葛慈》这部历史剧在描绘时代色彩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歌德早年努力学习莎士比亚的结果。读它,我们不仅可以获得艺术上的有益借鉴,而且能加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莎士比亚化”这样一些问题的认识。因为在写此剧初稿时,歌德的的确确正处于对莎士比亚的狂热崇拜中。他在1771年发表的题名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讲话里说:
“我初次看了一页他的著作之后,就使我终身折服;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25]
所以,他自己提起笔来也极力仿效莎士比亚的风格,彻底摒弃法国古典主义戏剧遵循的“三一律”,“觉得地点的一致好像牢狱般地狭隘,行动和时间的一致是我们的想象力的讨厌的枷锁。”
这些固然是青年歌德不受成法定则约束的狂飙突进精神的表现,只可惜矫枉过正,产生了副作用,“在企图摒弃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时,也损害了那个更高的一致”,[26]致使剧本结构松散,场面转换过于频繁,难怪赫尔德尔读过初稿后批评说:“莎士比亚把您给全毁啦。”[27]
两年后,歌德根据赫尔德尔的意见进行修改,但并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结构方面的缺点。
然而瑕不掩瑜,《葛慈》在当时的德国剧坛上仍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力作,在柏林、汉堡、维也纳等大城市演出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守旧派讥笑它的演出全靠华丽的古代服装取得成功;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更咒骂它是“那些蹩足的英国剧本——指莎士比亚的剧作——的可耻摹仿。”[28]但另一方面,它却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热诚欢迎,狂飙突进的重要代表毕尔格尔自称在读完它以[29]后竞“高兴得几乎发起狂来”。
对于歌德本人,《葛慈》则是早年仅次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最成功杰作,按其意义和影响,应当算作他漫长文学生涯的真正起点。歌德因此十分珍惜它,晚年在与艾克曼谈话时称它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对于整个狂飙突进运动,《葛慈》也不愧为第一个成熟的果实,在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以及语言运用诸方面,都起到了决定运动方向的作用,因此被誉为狂飙突进的“军旗”(Panier)。在它问世的一些年,摹仿之作大量涌现,德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写历史剧或“骑士剧”的热潮;从同时代的克莱斯特,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多数自然主义剧作家以至于英国的小说家司各特,都或多或少受过它的影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