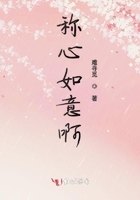“舒,晴。”他小小身躯抱紧了舒晴,舒晴有些不敢相信刚才那些有胆量的作为是自己所为,她的双腿也微微颤抖着。
在这个落后的村里,他们彼此是两个鲜明的存在,她为他斗胆面对了一家子人,现在心里边虚的一个慌。
看他光着两脚,个子较高的舒晴只好背了他一段路,中途遇上打着手电筒的姥姥,她看着嘴巴翘着和她赌气不说话的孙女淡淡地笑了一下。
“来!让姥姥背他吧,姥姥力气大,我的晴儿这还生姥姥的气呢!”
默许了别人带走巴特儿姥姥终究心里不舒坦,惹到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女生气她很在乎。
巴特儿是有些不信任舒晴的姥姥了,他一直不看舒晴姥姥,舒晴捏了捏巴特儿的小手。
“巴特儿,地上很凉的,让我姥姥背你吧!”舒晴的眼睛也不看姥姥,这话倒是让姥姥听了倍感舒适。
姥姥背着巴特儿,舒晴心里想着该怎么保护这个小她一岁多的小男孩,她知道他家人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本来,她把他安排在西厢房的一个小套间,这一晚她干脆把他安排在她和姥姥住的东边正房大套间里,进屋大炕是姥姥和舒晴睡,内里小套间的床是巴特儿睡的。
连续几个白天和黑夜,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以外,舒晴总是拉住巴特儿的小手怕他从她手里消失。
似乎想到了一个重要的,舒晴用舅舅画画的碳笔在白纸上写了满满一页的‘舒晴’。
“巴特儿,你,不光要记得我的名字,也要会写我的名字,以后假如你走在村里再又哪个坏人要把你带走,你就把我的名字说给他们,写出来更好。”
“好!我学,我写!”巴特儿在院子里用槐树枝条开始写舒晴的名字。
舒晴知道,村里人好歹都怕舒晴爸爸,他们会怕她爸爸让他们惹上麻烦,所以她才对招弟家的人说巴特儿已经被她认作弟弟了。
汉语没有学会多少的小巴特儿知道舒晴姥姥爱干净,所以,他里屋的夜壶他从来没有用过一次,每晚他都自己跑到院子南边的厕所方便。
姥姥家的老宅是经历了三百年风雨的宅子,墙高两米三,墙头有电网。
让舒晴感到可怕憎恨的荒唐事情还是在一个晚上发生了,巴特儿半夜上厕所就凭空消失不见了。
舒晴睡到半夜感觉院子里有‘腾腾腾’的声音,可她还是不愿意起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她才爬起来的时候天都大亮了。
夏日清晨五点的太阳照上大格子窗,里屋静悄悄地。
舒晴推开半掩的门,小床上被子被掀开的,巴特儿的外套和帽子还在。
“姥姥,巴特儿不见了!你说他会去了哪里?”
“这中院大门是我早上才打开的呢!他是长了翅膀自己飞出去了吗?”姥姥说。
这突如其来的事儿让舒晴着急的顾不上吃饭。
舒晴马上打电话给村校的老师,老师想了想,心情凝重地对她说:“什么原因先不要想了,先找人吧!我这里有一张我那天为巴特儿画的素描,也许用得上。”
“老师,那我今天不上学了,我向您请个假,我要求助我爸爸了!”
“好的!”老师答应了她的请假。
老师组织全班同学挨家挨户带着巴特儿的画像询问,那是他亲手当着巴特儿的面为他画的肖像,就如他本人的照片打印素描版。
舒晴爸爸的单位最近在执行航天保密任务根本联系不上,妈妈让舒晴直接打电话给省城的市局报案,因为她正忙着给弟弟们做吃的。
幸亏这半年在姥姥这里凡事主动得到了锻炼,她拨通了市省局的电话。
“喂,你是哪里?什么事儿?”那端是极具威严的成年人的声音,让人一听见就会两腿被这威严的声音震到发抖。
“叔叔您好,我这里是广武县野狐城镇狐狸坡村,我叫舒晴,我今年上小学三年级。”
舒晴还想要说下去的,那端声音立刻猛虎出山般提高。
“小朋友,我这里是省局刑侦办的,请你说具体情况啊!”
舒晴被这声音吓得想哭没有哭,抖动着双腿薄唇抿了一下快快地说:“我家里一个亲戚的男孩失踪了,他八岁呀他昨晚出来院子里上厕所,我们今天早上就没有看见他。”
姥姥看着她腿抖着有些不忍心,她接过电话给干员把小巴特儿怎么从车站遇上没赶上火车,然后被她外孙女执意收留回来家里一五一十的说了个清楚。
祖孙两人的电话报警成功了,村校的老师和同学相继来到舒晴家,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因为他们徒劳了一场根本就没有获得那小男孩巴特儿的消息。
这该死的农村!
舒晴心里着急到闷在离间不走出去,如果在一个人口稍微集中一点的县城里这事情就好办多了,那里通常会有礼拜寺接纳巴特儿这样的孩子,也有充足的警察力量很快将坏人抓获。
舒晴完全不想吃饭了,羊肉泡馍一碗就放在桌子上冒着热气,小碟的腌芹菜,芫荽猪蹄花包的馄钝她连动都没有动。
趁着姥姥不注意,她搭上梯子爬到老屋顶上手遮眉毛眺望远处的大路和铁道。
“巴特儿,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也许是没有吃饭,舒晴从木头长梯子上下来时候还摔倒在紫槐树旁,膝盖磨破了皮。
人在着急的时候倒霉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她很想站在村口把所有想打那男孩巴特儿主意的人都痛骂一遍。
“姥姥,我现在出门再去村里彻底地找一遍,你在家里等我就好!”
“你,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强呢?省城的干员说了,他们同志县里的同仁尽快赶来。”
姥姥抓住她的手,她认为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比不上孙女舒晴重要。
4当天下午,一辆白色警车带来三男一女四位干员。
这些干员仔细地在舒晴姥姥家三进的前中后院看了看,他们发现墙上的电网已经被毁坏,他们搭上梯子,最后在姥姥和舒晴住的中院西墙上找到了铁钩痕迹。
一名老干警对舒晴姥姥说:“这是属于作案手法老练的犯罪分子所为,这些年在我们县已经很少见。”
“叔叔,那么巴特儿会被坏人带到那里去呢?他连汉语都不是很会。”舒晴问。
早上电话报警遇上很严厉的声音,舒晴对干员开始有种本能的讨厌,一方面她巴不得他们早点走,另一方面她着急地想多问他们一些问题但又没有想好。
那位老干员眉头深锁,笑着看了一眼舒晴之后就对姥姥说:“老人家,我们会留下两人在村里进行暗访,希望您老人家全力配合我们!”
“一定的!只要能把那小男孩找到,可别等他家里人找来的时候我交不出来人啊!”姥姥今天最感到焦急。
舒晴姥姥已经认定巴特儿的妈妈会找到这里的,昨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她开始觉得住在这里不安全了,正好干员又这样说。
老干员的警车开走了,留下一男一女两名干员住在姥姥家的前院。
这两名同志建议姥姥和舒晴正常地生活,于是姥姥白天去村里剧院看戏,舒晴骑车去村校上学。
心里焦急的舒晴三天后发高烧病了,吃了药从前一天的傍晚躺到第二天早上,感觉到家里似乎又来了什么人,因为姥姥在厨房外的水槽边洗了很多蔬菜和牛肉。
一个熟悉而印象模糊的年轻女人也在姥姥身旁,舒晴想起来了。
“阿姨,您是巴特儿的妈妈?对不对?”
这个年轻女人的眼睛和巴特儿是同样的深蓝色,脸庞很好看,她一下子上来就抱住了舒晴,她用她好看的唇亲了舒晴的脸,那是她们民族的礼节。
“是,我就是巴特儿的妈妈呀!我很感谢你把他带回家,你们是好人。”
巴特儿都让我弄丢了还感谢呢!
舒晴一下子觉得愧疚难过就哭了。
“您别谢我,我没有把他看好,现在他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
舒晴擦着眼泪,心里难过到哽咽。
“真主保佑!我可爱的小姑娘,因为你的真心帮助,我相信今天他就能回来啦!”
巴特儿妈妈说着就掏出一块彩色的棉布手帕为舒晴擦眼泪。
她穿的七彩长裙,两条长辫子盘成两圈绕在后脑勺,前额发丝自然卷曲而有弧度,这精致的盘发多少年之后仍然是一种复古的流行风格占据潮流行列。
是啊,三天了,干员住在家里应该让巴特儿有消息的,她心里这样想着。
吃饭时候,姥姥一直笑着看舒晴。
“我的傻晴儿,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报警的,你不知道这三天省城的同志找巴特儿妈妈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呢。”
“对呀,就是你们那天报警之后,省城的同志才从火车站的旅馆找到了我,还帮我找到了这里。”
舒晴感冒好了,心里几度难过又自责不想说话。
姥姥竟然还笑着对巴特儿妈妈说:“这呀,也都是缘份。我一个住在村子里的老太太长居在这深宅大院也能认识你这么好看的和田姑娘,你看,我家晴儿和你们巴特儿也是。”
姥姥干吗说这些奇怪又有些害羞的话呀?关于‘缘分’这个词儿舒晴当时的理解是模糊的,总觉得那是一个小孩不会明白的词儿。
“那么现在巴特儿会在哪里呢?”她插开话题直接问姥姥。
“前院的县局警察说就是在你们村子里,但他们暂时不能公开的。”巴特儿妈妈说。
姥姥吃完饭,喝了一口瓷碗里的酥油茶叹气。
“要说,我从城市下乡到这个村子居住了快三十年了,我都还不知道这里有个老人贩子哩,他藏的好深呐!”
原来,巴特儿被村里的老人贩子铁钩上墙,瞄准了半夜出来上厕所的巴特儿用麻袋装了藏进他家的菜窖里了。
巴特儿在人贩子家的菜窖里待了三个白天,晚上怕他待菜窖会生病就带到屋里睡的。
干员用公务车公开抓了人贩子,舒晴非要看看巴特儿待过的地窖什么样的,她跳下去了。
那里气味略有潮湿,干土堆上有很多新收的洋芋和萝卜,菜窖墙壁上刻了很多个‘舒晴’,感觉字体很拙似乎是用萝卜尖写出来的。
当天下午省城来的同志来接巴特儿母子,他妈妈把一个黄金镶边的羊脂玉如意项链捧着送给舒晴。
“舒晴,这是我们送你的,希望你将来一切如意!”
姥姥推辞了几句之后就为舒晴戴上了,舒晴有些呆住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临上车时候,巴特儿那小男孩从车上跳下来,他站在舒晴的面前就是比她矮了些,仰望住舒晴的细长眼睛握住她手。
“我,还回来找你!”
舒晴还是呆着:“……”因为她想不出来合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