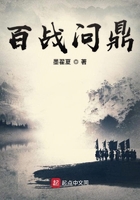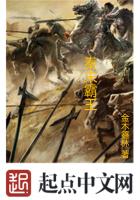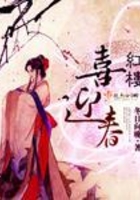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虽然把人们通过礼制分为上下等级,可它的终极追求却是大同之世。
所谓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权力禅让,人人平等,选贤举能使社会不用管理就能安定。
只是因为大同之世在可见的未来,并不能一蹴而就的实现,所以才退而求其次,有了小康之世。
小康之世是在天下为家的条件下,制定礼法的等级规范,也就是儒家制度,使社会在管理中安定。
但是,若统治阶层习惯了等级规范,并认为这就是天理,王侯将相就是有种,那就很容易忽视中国人对相互之间对等关系的需求。
儒家是不像墨家一样要求人人必须平等,但却坚持对等,而且绝不让步。
对等,也就是孔子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无礼,则臣不忠,甚至还要推翻这个‘暴君’的话,孔子虽然没说,但孟子却讲的露骨: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你对我无情,我也肯定对你无义。
相比起墨家形而上学的平等,儒家的对等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平等概念在华夏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对等原则却在中国人心中真正的扎下了根,成为了民族核心价值观里的重要一条。
所以刘宗周主张的治心、操守、仁义……确实是恢复信任的办法,因为只有统治阶层先这样做了,被统治者才能不把他们当做剥削自己的寇仇看待,才能同舟共济,才能众志成城。
只是姜洛知道,这套方法太慢了,而且统治阶层又不止皇帝一个人,其他那些权贵都心术不正,皇帝自己再讲道德,再克己复礼又有什么用。
困难重重,现实阻碍太大,最重要的是,没有时间了。
同样的,刘宗周虽然百折不挠,但也深感时不我待。
皇帝不采纳他的主张,他就去各地讲学,教学子们学会正心诚意,克己复礼。
可是,等这些学子经由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大量进入官场,并自下而上的改良整个统治阶层的不正之风,乐观估计至少也要二三十年才能收到成效。
他自己虽是六十有三的高龄,但一直清心寡欲,再活二三十年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大明皇朝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还能再存在那么的长时间吗?
刘宗周因此而深感忧虑。
他宣扬孔孟思想,目地也跟孔孟一样是为了在现实中使天下重归太平。但最终结果的成败却是一种悬念,在答案没有揭晓之前,他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姜洛在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继而说孔子堂堂正理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些失望的。
这种大道理,是个圣教弟子就会讲,而他想听到的则是一套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
是的,刘宗周最开始所看中的就是姜洛的术。
那些从道之外,以独立并客观的角度,分析各种问题起因和制定解决方法的术,才是让他对姜洛眼前一亮并青睐有加的真正原因。
好在姜洛之前的才气纵横,让他认为此子应该不至于徒有空论,而对方若真有救时之术,那再加上自己的治世之道,说不定就真能快速的把国家从危局中解救出来?
这样一想,刘宗周对未来的希望就大了些,于是强打起已经有些疲惫的精神,笑着问道:“临渊你说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老夫的所作所为才是最能救当今天下之危局的,那么临渊,你可有更好的方法?”
姜洛摇了摇头,干脆利落的回答道:“没有。”
“没有?”刘宗周一愣,然后露出一副明显不相信的表情,耐心开导道:“你既能开出导致本朝危局的病因,那就肯定是想过解决方法的。或许你的方法还没有完善,但也不应该闭门造车,说出来大家探讨一番,焉知不会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嗯…就是话中有悖谬之处,在这里说说也是不打紧的。”
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规范所悖谬之处,姜洛在之前的话中已说过不少了,甚至有些话都超越了悖谬,而开始否定皇权,非议皇帝了。
因此这一顾忌对姜洛是没有限制的,他不会不敢说,只是不想说。
不想说的原因,则是他认为的救国之术难免也要涉及到在场众人的利益,而他对这些人是抱有好感的,所以不想言语中伤。
反正他想出的方法不可能实现,大明皇朝也终究要亡,既然伤人的话说与不说都不可能对现实产生什么有益的效果,那又何必说呢。
但是他的一番长篇大论已经到了最关键处,只差临门一脚就可登堂入室,若戛然而止,就此打住,对众人和对自己而言都难免是一种遗憾。
因此刘宗周一劝,姜洛也就不打算再装傻充愣。
只是若真的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所展现出来的庐山面目,未免会让众人觉得太过残酷。他也就不得不再想一番避重就轻的言论,以尽量不使这些人因他救国方法中的细节而胆寒。
“切莫藏私啊,临渊。”
“是啊,临渊尽管知无不言,我们洗耳恭听。”
此刻,又有几个声音同时敦促道。
姜洛抿着嘴巴想了想,然后对众人拱了拱手,“承蒙诸位错爱,那晚辈就斗胆妄言一番。
晚辈觉得,问题既然是儒表法里所造成的,那要解决问题,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干脆就把儒表法里政治架构颠倒过来,也就是用儒家思想,行法家制度,有菩萨心肠,使霹雳手段。
儒家思想的道德大中至正,法家制度的效率独步天下,把两者真正好的一面结合到一起,晚辈相信是能救国的。”
华夏作为世上唯一一个没有湮灭与中断过的古老文明,自有国情在此,也自有制度在此。因而,治此时的国,平此时的乱,还是得用老方子。
儒法这两个老方子虽然都有问题,但其问题毕竟也要分个主要次要。
儒家的主要问题不在思想,在制度。法家则反过来,主要问题不在制度,在思想。
儒法两家不是闲着没事被人们瞎想出来的,也不是无缘无故被凭空创造出来的。
它们都诞生于乱世,因此被创立出来的第一目标都是为了治乱,治国则要排到第二位。至于会沦为维护等级专制的行政工具,起码是儒家所始料未及的。
人世间为何有乱?是因为人性有贪。
只要贪婪在人身上存在一天,那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因为对利益的争夺而产生战争。
贪为恶之源,因此止战治乱,首在治贪。
儒法治贪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儒家认为人性有恶,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
有恶,就还有救,所以儒家温和的像医生,它要治病救人,它要人们发扬心中的善来压制心中的恶。
本恶,就没救了,所以法家残暴的像屠夫,它就是杀,不杀就无以立威,无威就不足以称其为法,就不足以制恶。
……
使人剔除本性中的贪婪,是儒家思想在做的事。
君子不夺人所爱、怒不过夺,喜不过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思想使人脱离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兽性,而往人性上塑造的这一方面,是极为高尚伟大的。
因为它就是在与整个人类的人性之恶做斗争。
仅凭这一立志,就足以使人折服,虽然它在已往的历史中从未胜出。
但也因为这种立志,儒家思想就只能是追求,是理想,是人性道德的上限。
它不设下限,君子之外就是小人,小人等同于禽兽,两者之间也没有缓冲。
为什么后来的新儒家变的不再包容人性,甚至有些丧心病狂,喊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新儒家浑身上下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们都不是人了,而成了神,自然而然的他们的调子也就越喊越高,高到了人都做不到的地步。
尤其是这些神眼里还揉不得沙子,他们自己成了神还不够,还致力于也让你不再当‘小人’,不再当‘禽兽’。
真小人真禽兽也就罢了,改就是了。可把想在饮食上吃好点都算作小人心思,在有了孩子之后偶尔过过夫妻生活也算作禽兽行径,那新儒家岂非混账透顶?
水至清则无鱼,这么高尚的思想,不适合治理一个人群杂乱的现实国家。而它希望的人人都是君子的神圣国度,在人间也是不存在的。
……
而儒家制度治贪的方式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爱,大家都你爱我,我爱你,即使贪婪依旧存在,那也会因为有了爱,而从互相争利转变为互相让利。
爱能救世的观念有些人深信不疑,但它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谁都知道处处都充满爱的社会是好社会,可偏偏人不是理性动物,而是感性动物,并且感性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地步。
有太多时刻,你跟别人完全没有利益之争,但别人却能够因为你的长相,你的性格,你的出身,你的肤色,你的民族,你的国家……而讨厌你,鄙视你,甚至恨你恨的咬牙切齿。
听说你遭了灾遇了难,因你的悲惨遭遇,有人能同情心大发而落泪,也有人能笑的肚子疼,但这两种人却可能都不认识你,也跟你没利益牵扯。
无缘无故的恨,与无缘无故的爱,都是广泛存在的。
所以亲亲不行就还要有尊尊,尊尊就是尊重和服从上级的处理意见。
在家尊父母,在朝尊君主。
你和你的兄弟,你的同事同僚之间有了利益之争,不能自己解决,而是要去找父母和君主裁定。
父母说,你是长兄你要让着弟弟,你跟他抢这个抢那个太不像话,听话,都给弟弟。
君主说,你是下官他是上官,以下犯上岂非狂妄?听我的,这事就按你上官的诉求办了……还不给你的上官磕头认错?
尊尊就是这样,至于尊尊所产生的分配意见合不合理则不必考虑,因为它的目地就不是为了合理,而是为了让你不争。
一个巴掌拍不响,争端中只要有一方收手,那自然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像周礼规定,天子娶十二女,诸侯九,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普通人……普通人能找到媳妇延续香火就不错了,还妄想什么?
它不合理,因为谁都想要更多的女人,凭什么你们都左拥右抱,而我就一个?要一个就都一个,要十二个就都十二个,行吗?
不行,女人数量是有限的。
你不要看普通人想要十二个,天子还想要一百二十个呢,够分吗?不够分就又要抢,一抢就打,打起来命都可能丢掉,还要什么女人。
所以大家为了保命就都要认同尊尊,哪怕它的分配不合理。
在这种分配中,占了实利的自然高兴,没得到好处或受到损失的,它也会用吃亏是福的理论进行自我安抚。不这样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礼制就是这样规定的,你又改变不了,难道还得自己把自己给气死?
那么尊尊管用了吗?没有管用。
人主不公,人臣不忠。
人臣觉得自己总是吃亏,自己总是分的比别人少,那干脆就不听你的分配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想要什么就抢什么,既顺心又划算,怎么也比听你的强。
他这种不忠,不单单是不忠于人主,而是背离了整个亲亲尊尊的礼制。
这样的人多了,就又回到了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时代。
这是尊尊难以避免的结果。
什么是公平?你说不公平就不公平?这世上有公平吗?
种同样大的地,收同样多的粮食,而你要养十口人,别人却只养三口人,因此你说你的负担大,你得多分地,多收粮食,这样才公平。
凭什么?谁让你多生孩子了?
上级哪怕不同意,你也不能听,只能抢,再不抢你家人就饿死了,关键是你人口多你还真的能抢过来。
人到了绝处,就不会再想自己的绝处是不是自己所造成的了,更不会再管亲亲尊尊。
除非他想饿死。
不想饿死,他必须连儒家思想的道德都弃之不顾,还能再受儒家制度的管?
法家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法家思想治贪的大前提是富国强兵。
富国,就是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
自己有,才能不抢,哪怕有的少点差点。如果没有,如果他就要饿死了,他就只能去抢,还是必须去抢。
所以法家要干实事而让大家都有,有没有的问题也才最重要,亲亲之爱则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在没有的情况下,你爱他,他也要去抢。你不爱他,他也要去抢。那你爱他干什么?儒家有病吧……
富国之后,其次就是强兵。
如果富国是基础,强兵就是保障。
因为人性贪婪,因为人在有了之后还想有更多,如果没有强兵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震慑住,那还是要回到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时代。
没有强兵震慑,谁说话也不管用。
像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周天子的话谁听了?
为什么不听?还不是因为周天子打不过诸侯,没有让诸侯听话的实力。
有实力,才可以跟诸侯们讲道理。没实力,就只能听诸侯跟自己讲他们的道理。哪怕周天子在名义上是所有诸侯的总父亲。
……
法家制度实现富国强兵的方式多不胜举,而思想上,则把中心放到了君主一人身上。
君主要做到两点。
第一是集权。
君主通过法、术、势,包括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严刑峻法等方式,掌握所有权力,拥有打败所有诸侯的实力,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存在。
这样一来,君主之外的其他人都没有权力没有实力,等于是把他们的破坏力减到最弱,使他们再贪婪也有心无力,再能抢也抢不了多少。而君主却轻轻松松的就能清除掉他们。
第二是以法治国。
君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不靠尊尊分配利益,靠法分。
通过法,来公平公正的给予其他人利益。守法的给,不守法的不给,除此之外,不因为任何因素而多给或者少给。
这看着很好,但是过度依赖君主的能力与品德。
君主也是人,也有贪婪的劣根性存在。
他无敌于天下,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他恨不得把所有的利益都捞到自己手里,他第一个就不守法,又怎么能够做到为天下人定分止争?
再立一个跟他一样实力的副君主来监督他?那君主与副君主之间有了争端怎么化解?还是会产生战争,并且由于两人实力一样,打起来就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次性的使人口折损过半,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更大。
法家思想在源头上就埋下了隐患,因此对后续产生的问题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