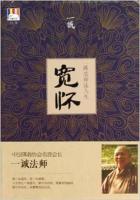李思勉夫妇两个夜话。
李思勉:“明日我去找柳县令问案情,你也来罢。”
芊芊:“不去。我尝个鲜,试个趣儿就够了,怎好成天跟着你?叫人笑你惧内……”
李思勉演起来了:“哼!我李省身生平固然不敢违拗夫人,但却也不叫惧内!”
芊芊噗嗤笑出来:“与你正经说话,你油什么呢!”
李思勉知她一惯口是心非,就安慰道:“你勿多想了,我权势大,人不敢当面笑我的。”
芊芊怒道:“我讨厌的就是背地里的!看那知县和快手的脸色就知道!”
李思勉劝她:“皇帝也禁不了人背后非议他。你我问心无愧,管他说什么。再者,这两日你笑脸多了,我见了开心。”
芊芊晕了脸:“你近来嘴也颇乖了吧……”
李思勉笑:“这事耍一两天,人要笑我惧内;做一两年,人道我夫妻情深,密不可分;若我坚持十年二十年,人就敬我是圣人了!那时我敢叫人都学我,也和妻子携手出门,这岂不妙?”
芊芊乐了:“哈哈!你却是做梦了,大字都写错,还做圣人。”
……
次日,李思勉先去找柳县令,夸他为民父母,解民于水火,只一日就将恶人缉拿归案,实有包龙图之风。
柳县令也有些得意,但还是自谦:“此全乃省身弟功劳!我已听闻,省身弟甚有急智!仿佛孔明在世!”
他们一个当代包公,一个孔明在世,越发商业互吹起来,叫侯芊芊在一旁看得好笑。
柳县令想:“原以为老师公子是个痴顽蠢物,不意此人竟颇识趣!只是他将女子带在身边,还叫她着男装,此糊涂事若叫老师知道,恐要责我不察之罪……我只假装没看出来罢!”
随后李思勉问起案情经过,柳县令便慢慢说来:
捕快们从庙里搜出一千两赃银,私下分了八百两,剩下的上交县衙,继而拷问那假和尚钱如何得来。
这假和尚见南京县衙里没有他的海捕文书,无人认得他这张脸,就只认诱尖妇女的罪,不肯认他有什么前案,好谋一个轻判。
且此人甚是嘴硬,重刑拷问亦不开口,咬死不说来南京前犯了什么案
后来一个经年老吏出马,掏出一包硬猪鬃,扯开贼秃裤子,拿猪鬃捅他马口眼。
这强盗不是铁铸的,如何禁得起这种刑罚?死去活来地,实在痛苦忍不得,方才供出他是江西鄱阳湖的大盗,做过两起大案,劫了数千银两,手上少说有六条性命。
他在江西狱中逃出,先到上江(安徽)做了一起案,继而流窜到南京,因恐人认出,就剃了发,借出家避难,躲到那土地庙里。
那日他收斋饭,因见到吴峦妇人独自午睡,就动了歹心,强与之淫。更奇那妇人惊醒却不叫喊,居然也甚乐之!
这和尚尝到甜头,得陇望蜀,图谋长久,就骗妇人说:“不好了!被人看见了!若传到你男人耳中,叫拿去官府,我被刺配,你则发卖,全部完蛋矣!”
那妇人无主见,被这一吓,慌得直哭,和尚就说:“事已至此,你不如与我逃了。我实小富家庭出身,还有千金家资,愿还俗与你做长久夫妻。”
吴峦妇人起初是受害者,后来她自己有心,也成了罪人,因此无法与丈夫解释,只好同那和尚私奔了。
这和尚奸计得逞,转瞬露了强盗本性,他将那妇人拘住,禁在庙中,日夜凌虐,毫不怜香惜玉,吴峦妇人痛苦不堪,此刻才醒悟是被骗了,方想起吴峦的好来,却是悔之晚矣。
好在昨日吴峦求李思勉出面,县衙便差捕快来找,否则这妇人早迟死在那强盗手里。
……
“这帮狗才!竟敢在我眼底贪赃!若不是犯人在堂上大呼‘我有千金’,我至今不知叫他们落去了赃银!这下好了,有这一千两,倒可以给魏上公再建一座生祠!那时我将这生祠来历禀与魏上公知晓,魏上公必然嘉奖年弟与我,此真幸事也!”柳知县眉飞色舞地说。
原来那强盗自知必死,因痛恨被狱卒拷打,故将赃银数目喊出与县官知道,叫那些捕快狗咬猪尿泡——得了一场空。
“这笔钱回不到失主手上也就罢了……居然要拿来给魏忠贤造祠堂!?”李思勉震惊,“那我这阉党之名岂不大大坐实!?”
他便开口道:“年兄抬爱,弟实感激。但弟一来年幼,二来并无功名,外人知道,或说我无心进学,却与贱卒皂吏厮混,那反叫家父与魏上公难堪了。故弟以为,年兄大可说此案是你一手包办,弟绝无意见!”
柳知县一听,内心叫好,外表却捻须思忖:“此言亦是有理……”
后来就这样定了,柳县令多少不好意思,便说:“将来省身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李思勉就说:“弟或要多雇一些人耕作土地,先与年兄知会一声。”
。
出得衙门,芊芊鄙夷道:“原想你那篾片不是好东西!谁知他妇人更不是个东西!早知如此,该让她到衙门挨一顿拶!”
李思勉道:“近来此事甚多,故刑已不严了。再者强盗之言也不可全信……”
话虽如此,他也觉得“好他娘奇葩啊!这么乱的吗?”
……
回到家中,门子报说吴峦已到了。
李思勉有些无语,不知怎么面对这个绿帽侠。
“还是叫人不快,别叫他来家里了。”侯芊芊说了就回内宅了。
李思勉来会客厅,对那躬身道谢的吴峦说:“住了,你我交情就到今日,你去寻别的人家帮闲罢。”
吴峦脸色大变,慌忙告罪,却又不知错在哪里。
李思勉不能说“我老婆看到你夫妇就心烦”,而是说:“并非针对你,所有清客我都辞了。”
吴峦知道没戏唱了,就躬身说:“贱内之事小的还是感激不尽!不过恩情只有来日再报了,大老爷,那小的走了。”
李思勉想起昨日吴峦表现,此人确实疼爱妻子,那掉泪也不是假的。
那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明朝人,思维方式都太怪了,理解不了……
但是李思勉又想要理解这个年代的人。
他还是忍不住问:“你妻子那样,你怎能容她?”
吴峦一愣,转身鞠躬:“大老爷,小的本不该与您说这些凹糟事,但您待我至诚,昨日之事与您毫无瓜葛,但大老爷却亲力亲为,为小的以身犯险,小的无以为报,实感惭愧!既然大老爷有话,小的这就坦白:小的……是天阉。”
李思勉惊了一跳,细想过去,果然从不见吴峦留胡子!
“贱内或有不对,但她现在也悔了,如今小的还是体谅她。”吴峦卑微地说,深深低头。
这“体谅”倒比“原谅”的级别更高了,真是愈发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