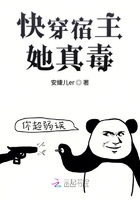抬头仰望时,晴天里总有片云像是从某年飘来,让我油然想起某些人和事。
但记忆又如云苍白,如天空湛蓝,不见底的深邃。
珠海拱北口岸的那片海,在记忆里与我间隔了大概十五年。
十五年前,第一次去。
那时有父亲和继母,还有和我同一屋檐下长大的堂哥。那张合影里,我和堂哥稚嫩青涩。我们四人第一次像这样合影。也是我和父亲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合影。
十五年后的今天,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我孤身第二次来到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找工作碰壁后停留的港湾。
一次次的面试失败,将我的信心击得破碎。已经放弃了努力的我,听叔叔的劝慰,打算回到这里的原公司,他朋友所在的公司。为了等待入职消息,我租了房子,一等就是两个月,毫无音讯。为了省钱,吃了近两个月的面食,用烧水壶烫熟,偶尔买几颗青菜一起烫进去。手上资金不足,与母亲持续的矛盾,让我不敢开口要钱。更没脸没资格再以学生的身份要钱。而叔叔体弱多病,这几年来也没有工作,根本无法资助我。省吃俭用,每天有气无力。叔叔不断打电话安慰和鼓励我。
此前,我在深圳同学的租房里睡了半个月的沙发,夏夜格外闷热。我已经把自己放得很低贱。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除了感恩,别无多求,哪怕在不花钱的别人的租房里给我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板就知足了。住得太久,实在过意不去,自行选择离开来了珠海。
等,是最难熬的一件事。每天焦虑等待入职消息。
心情郁闷,熬夜失眠,趁着放晴,打算出门走走。
我一个人来了,又见那片海静静躺在那里。她眸眼浑浊,大概是看多了如我这样来来去去,匆匆一遇无声一别的过客。她的表情,比起十五年前还要幽秘深远。要望向更远更深处才辨得出她的纯净幽美。
她大概在十五年前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往后所有的念想都被心里的她泛起。为了遇见类似于她的她们,我总会梦寐以求,心驰神往。
我选读了近海的大学。青春在翻腾的海浪里和赤热的沙滩上游荡过无数次。我做着她深蓝的梦,触着她无垠的风。脚丫踩着银沙和海贝流连忘返。就连我身上附带的尘土,也要在沙土里雀跃,在海浪上起舞。
她给予我无垠的壮阔,也深埋我年华的蹉跎。
十五年前,照片里的她心潮澎湃,那时候看不出她任何的悲哀。
如今我已长大成年,再看她,潮来潮去也浪不费她的岁月。时间都已经沉淀或封锁在她的沙粒和乱石里。她截留了过客的年华,将之潮起潮落,只等有一天过客再回首与她重逢,她定不吝惜把曾经的画面一幅幅抛给他们。她已经将画卷在我记忆里灼烧,我却已不记得合影的地方具体是哪里了。蓝天不是那日的蓝天,海树已不是那时的海树,海岛尽管还在,而山石草木也已经萎靡过了十几个春秋。海水被河流和云雨灌新。也许我家乡的河流也汇集进来了,也许我年幼时的呼吸,父亲以及所有我见过的熟悉的陌生的人的气息,也都融在了这海里。它们在四季里循环游荡,又窜入更多人的鼻腔直至心底,让他们有了关联。
春去秋来泯灭了从前。只有被她定格的许许多多不知名状的东西在海风里呼啸而过。
海未枯,石未烂,天如昨日青蓝。只是父亲已经随着海风一阵阵从我的发丝剧烈拂过,偶有几条被刮得灰白。
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曾以为风无起始之地,未有终结之处。没想到它们也起于这片海,终于发丝苍白。
风游走大河荒漠,穿越人山人海,从世界的这头去往另一头。风寄身于海鸟,轻扶它们到别的天涯海角,鸟儿与鸟儿互通。鸿雁传书,古往今来,不绝于世。风还会拽走海空上的云朵,在世界各处幻化成雨,代替了人心底许许多多次的晴天。
人的多情善感都被这些与自己同生共存的异类触动。
那片海很多情,连同沙土石块和海岛。她自己本就能凭借着蒸腾变化上天入地。她还感染了风,风感化着海鸟和云朵。毋庸置疑,鱼儿也会是装满故事的漂流瓶。鱼鳞烙满了文字,鱼骨也刻上了甲骨文。只待有心人消化它们,融入躯体。如今她又有了长长的跨桥和隧道,想要连通隔海相望的人。她一早就有了船,让相隔遥望的人漂洋过海去找寻彼此。去爱恋,去祭奠。
我也被她的多情感染了。情愿做一支洋流随她奔向每个港口。在那里我会是别人心中那片海的一部分。多年后,那些过客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顾我。如果他们望向我的更远更深处,我也会毫不吝惜地把昨天还给他们。纯净而幽美。
而我,却更像她浩瀚里的孤帆。需要她的风和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