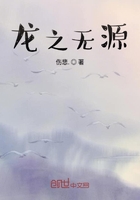家,很简单。一张床,一个奶奶,一个我。当然,还有这个瓦房,一个土砖和木头构成的两层楼房。
瓦房背后几百米是青山,前面是一排悬空的竹林,竹林落差几十米处,细水长流。
风雨扫过的瓦房,竹叶和杂物飘落在木楼上,衣服上、床上又是一遍脏乱。雨水渗在楼板里,衣柜里,一股霉味。霉味,是童年的记忆。
每次离开家,尤其是离开的时间长,总要把湿气的被子和棉垫卷起来,用尼龙盖住。
蜈蚣趴在散落了灰白的墙壁上,又钻到床底,不见踪影;
大黄蜂在屋顶扎窝,小黄蜂在布满灰尘和蛛网的褪色衣服里安家;
老鼠翻箱倒柜,撕咬衣服和书本,没日没夜地折腾,死老鼠的味道常年在二楼蔓延;
怪蛇经常从竹林偷溜进暗屋,蜷缩在角落和床底。
还有,和奶奶同睡的床边窗户下住着一群蚂蚁,它们经常搬走我掉在床上的甜点。
门前的竹林上,清晨里有群鸟的欢叫,夜幕里有猫头鹰的怪叫,那怪叫,时常钻进我童年的梦境。当我开始一个人睡二楼时,对怪叫的猫头鹰怕透了,奶奶不在家的一个暗夜里,灯泡爆炸后我跑到阳台,怕猫头鹰会来就渐渐停息了寻找安全感的哭喊。
这些土生土长的生灵,或可恶,或可怕,也都肆无忌惮地活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却又和谐安宁。除了猫头鹰。
清晨和傍晚的炊烟是我的最爱,有着不同山柴的味道。它们也穿过瓦房的缝隙,袅袅升起,洋溢暖气。这种感觉在雷雨天和冬天会更深刻。
炊烟,是奶奶在准备着一顿饱餐。辣椒煮鱼、辣椒炒西红柿、辣椒炒红薯叶、辣椒清汤……离开辣椒不算美味,无辣不欢,不是奶奶的味道。
竹林里脱落的干枯笋叶和竹子是生火煮饭的好材料。
干竹经常爆裂,炸飞了灶里的灰,或透过虫洞喷出浓浓白烟。呛鼻,却感到竹香四溢。
奶奶静静靠在老旧的木椅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房子旁的空地上烤红薯。她得意于自己的成果能带给我美味和欢乐。
房屋旁的小空地上也有奶奶的小菜园,有青菜、萝卜、辣椒、茄子、四季豆、黄豆、黄瓜、冬瓜、南瓜。
一年四季,就在这被开发的小空地里,瓜果飘香。
屋旁的枇杷树桃树和桂花树,花果年年如期;领居家黄菊花和牡丹花的芳香,让人沉醉。那好像是我出生后接触的第一道香。
同一个小山头的人家共用的山泉池可以洗出干净的菜,可以品出浓郁的山味。
山泉汇聚的小河,就是家门前那条。在它怀抱里的小鱼是融进我童年血液里的营养,是我的最爱。
家里有个特别的趣事。经常有小狗自己送上门,然后被我和奶奶善养。别人说,小狗自己上门,那是福。
小狗为这暗淡的房子增添了生气,给我们欢乐和安全感。它们灵性、忠诚、善解人意。
同一屋檐下,它们生儿育女,和我们同甘共苦,共历风雨,平等关爱。
然而,每一条狗都曾痛苦离我们而去。被夹断腿、被贩卖、被活活打死。谁会为一条狗的命运悲泣呢?心地善良的奶奶会,我也会。它们是我家的一员,那是我懂事后体会别离之痛的启蒙。
家和我的世界,曾经,就这么大。无须开疆扩土,无须缤纷繁华,自得其乐,得天独厚。